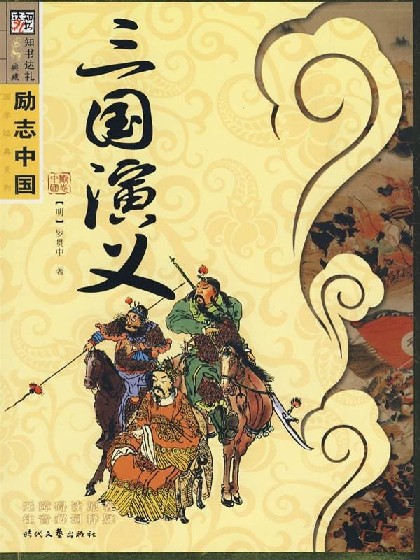第八十章煮酒醉论道
秦晋对北衙禁军的规矩了解并不多,听陈千里如此说,立时也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大好机会。心想,等接掌了神武军中郎将之职以后,再将陈千里调到神武军中来,此人心思细腻,又向来有大局观,用此人做臂膀,也省却了很多不及考虑而造成的麻烦。
陈千里有着契苾贺与郑显礼所部具备的一个优点,那就是此人大事临头,仍旧十分的冷静谨慎,甚少会以情绪左右行事,这也是秦晋很看重陈千里的原因之一。
现在秦晋要到神武军中去任职,再不把近在咫尺的陈千里调过来,从哪一方面都说不过去,再者,调动区区一介参军,芝麻粒大小的事情,他这个神武军中郎将难道还办不到吗?
只是,此刻的秦晋没想到,一旦经办此事时,将会为他带来无尽的麻烦,
陈千里的酒似乎也醒了,斟酌一阵后问道:
“不知天子如何就改了主意?一日间连升两次官,长史君这可是古今独一份啊!”
继而又拍拍脑门笑道:“错了错了,是中郎将!”
说起这个,秦晋的目光忽尔一阵暗淡,便将天子如何将新安军做了交易,送给哥舒翰,杨国忠又如何保举自己做了神武军的中郎将说了一遍。
听罢讲述陈千里一阵疑惑的啧啧连声。
“奇哉怪也!”
秦晋被他沉吟不决所吸引,便问道:“何处奇怪?”
“长史君从未与杨国忠打过交道,此人因何甘冒如此风险,为长史君夺下关键的职官。”他端起酒碗咕咚一声,又灌了一口,才恍然一般道:“难不成这是天子的本意,杨国忠只是挡箭牌?”
思来想去,他又摇摇头,“不会如此,一定还有深意!”
“是了!”
终于,陈千里双掌交击,兴奋的喊了一声,就像发现了宝贝的孩童一般。秦晋看在眼里心道,陈千里平日看着不苟言笑,喝多了酒却也有原形毕露的时候。
“杨国忠最近与哥舒翰争的厉害,凡是哥舒翰同意的,他就反对。凡是哥舒翰反对的,他就同意。”
秦晋点点头,以他所指,杨国忠与哥舒翰的关系的确几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长史君想想,哥舒翰一直试图打压你,暂且不说其中因由。加上天子十分看重于长史君,借由这两点,杨国忠除了要以长史君为筹码打击哥舒翰以外,怕是还有拉拢之意。”
陈千里更断言,相信用不了多久,杨国忠将会有进一步的动作对秦晋进行拉拢。
“长史君切不可与杨国忠过从甚密,以陈某判断,此人并非什么长寿之人,没准还要突遭横死,过从近了,反会受其拖累。若远了,又唯恐杨国忠因此生了戒心,总之,长安城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咱们兄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小心再小心。”
秦晋自问可以做到戒急用忍,但他可不敢保证契苾贺与乌护怀忠都能戒急用忍,尤其是契苾贺,勇武有余而狠辣过甚,任何事只要不对脾气,便是天王老子都敢大干一场。
这种脾气秉性在长安城这种遍地皇亲权贵的地面上,恐怕秦晋的双手都要时时护在契苾贺的脖子上。
秦晋就势端起酒碗喝了一大碗,大呼一声痛快,然后将酒碗重重在桌子上一顿,说起了他心中的担忧。
“杨国忠与哥舒翰的明争暗斗,秦某倒不怕,怕只怕因为争斗而害了国事,将刚刚有所好转的局面给败坏了个干净!”
一说起国事,陈千里则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而道:“长史君一直担心的高大夫,只怕时日无多了!”
这句话听的秦晋心头立时就是一紧,他知道陈千里在长安城中,听到的消息一定很多,而长安城中遍布朝臣权贵,不论从哪一坊传出来的消息,都未必是空穴来风。
“是兴庆宫里传出来的消息,据说天子有一次在提及高大夫与封大夫的名字时面色很难看,直到议事完毕宰相们退了出去,天子提起笔来写下了一个字。宦官收拾桌案,才发现,那个字是一个极为潦草的死字!”
陈千里描绘的似模似样,甚至连细节都有声有色,秦晋却不相信。
“这等宫闱隐秘能传出来个大概轮廓就已经十分难得了,加工的如此精致细微,定然是有人故意如此造谣!”
宫闱里有嫌疑造这种谣言的,第一个嫌疑人就是边令诚,此人上一次几乎就要成功的杀掉了高仙芝与封常清,但偏偏不巧在路上遇到了秦晋,又偏偏不巧,秦晋搞了个岘山大火,乃至引燃了整个崤山上的密林,彻底断绝了潼关通往陕郡的道路。
边令诚其时已经丢了天子旌节,手中空有一封夺命敕书却不敢送出去,于是灰溜溜的逃回了长安。若非皇帝念着旧情,仅仅因为丢失天子旌节一事,就会获罪流放,严重者就算处死也是常有的。
“长史君偏激了!”陈千里在边令诚和天子对高仙芝的态度上产生了不小的分歧。秦晋认为,天子诛杀高仙芝封常清,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边令诚的谗言,而陈千里却认为,边令诚不过是天子的应声虫,如果天子没有杀机,就算边令诚造出一百个谣言,进一千个谗言,高仙芝和封常清都死不了。
“所以,症结所在还是于天子身上,天子要臣死,臣如何能不死?”
高仙芝和封常此前很幸运,只可惜高仙芝的运气太差了,竟然带着人马烧了太原仓后一头扎回潼关,这不是伸头等着挨天子那一刀吗?试问如今满朝文武有哪个还不知道天子要杀高仙芝与封常清?高仙芝他自己难道不知道吗?封常清运气好,带着兵马到河东与河北区平乱……
陈千里说了啰哩啰唆一堆话,秦晋听的云山雾绕。
“以陈某所见,高大夫的事长史君已经竭尽所能了,不若就此罢手,否则牵扯进去,惹怒了天子,唯恐自身难保!”
秦晋定睛细看陈千里以确定他说的是不是醉话,两个人酒酣正浓,说这些话难保隔墙有耳,他又陡得警觉了起来。看到秦晋的这一番好似做贼心虚的表情,陈千里嗤笑了一声:“长史君怕甚来?大唐又不会因言获罪,似这等酒肆中,说话比你我兄弟骇人千百倍的都有,没人会当真的!”
“是吗?”
在秦晋的印象里,封建王朝因言获罪的例子不胜枚举,怎么这里的酒肆就随便说呢?
陈千里就像发现了新鲜宝贝一样呵呵笑着:“因言获罪那是汉朝,幸亏你我兄弟没生在武帝之时……”说着,他打了个酒嗝,然后伸出右手指了指自己肥硕的肚子,“否则这里随便响动一阵,都要被捉了去过廷尉府的大狱!”
陈千里所指的肚子秦晋是知道的,武帝时甚至有腹诽之罪,只要当权者认为某人有过不臣想法,便会抓起来下狱,可以说罗织罪名无所不用其极。
至于大唐,虽然唐律依旧严苛,但执行起来却远不如两汉那般严谨,到了开元天宝年间,朝野上下一派开放散漫气息,谁又有功夫整日里揪着律条过日子呢?
就算朝中的宰相们相互间拆台斗法之时,也没人再提起大唐的律法作为是由,去打击各自的政治对手。
陈千里的醉意更浓了,话也越来越离谱。
“前汉藩王造反,有七国之乱,藩王兵力不可谓不强,为何朝廷盛而藩王败?无他,皆因法度完备,上下其一!我大唐又因何有逆胡安贼坐反?无他,皆因法度废弛,天子政令朝行夕改,墨敕斜封屡见不鲜,时间日久,从上到下都只重私恩,而忘公法,安贼焉能不反?就算安禄山在两个月前死了,造反不成,也会冒出来**山,张禄山……”
秦晋沉默不语,陈千里说的没错,唐朝到天宝年间,中央朝廷与地方之间的羁绊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身为皇帝的李隆基不想着如何完善制度,而仅以私恩笼络边将,往往节度使掌管数十郡的军政财权。地方财税,节度使可有权提调,地方官的任命可有权干预,到了近几年郡太守的权力几乎已经被节度使所掏空。
试想想,军政财权无一掌握在朝廷手中,就算安禄山被打压下去,只怕做了四十多年天子的李隆基一死,边将造反者也一定不止一人。
朝廷边患日甚,需要边将节度使为它打胜仗,便竭尽所能的扩充其权力,但日久之后又觉得难以制衡,再想收权却难上加难,于是只能哄着,给更多的好处和权力,如此饮鸩止渴,国事焉能不败坏?
秦晋忽然有一种想法,也许李隆基并非没意识到边将节度使的尾大不掉,也并非不知道墨敕斜封的害处,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他才有些恍然,李隆基今日所说天子当的苦,并非全然是在演戏,也许有几分真意在里面也未可知。
乱唐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退役
- 简介:兵王退役,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当从退役那一天开始,兵王李彬就知道,这也是自己该选择的,十年前自己因为受不了村长的压迫,所以才不得不得以离开从养育自己的家乡,十年后回来了,一切的辛苦揭竿而起。
- 1.2万字5年前
- 穿越成救世主
- 简介:没有摘要
- 2.0万字5年前
- 三国演义(白话版)
- 简介:《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原著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三国演义》原著内容是用古代文言文写成的,而且每个章节内容篇幅太长,今天读者阅读起来极不习惯,并且在原著中的迷信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的污蔑称呼,也与今天的时代的不符合。在我努力遵守《三国演义》主体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特色基础上,对原著内容进行全面翻译和改编,这样希望各位读者喜欢。
- 81.0万字5年前
- 绝世双剑录
-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君可曾梦回三国?漫天的烽火,山壁染成赤色。周郎举兵西向,复拔南郡。千古功名拓,然而,在一年之后,年仅三十六岁的周瑜病逝巴丘。美人断肠,小乔泪洒长江。君可曾叹息?叹息英才天妒?君可知,在十年之前,还有一位英雄,在二十六岁的英年,万丈光芒骤然消逝。在他的身边,也有一位美人落下了伤痛欲绝的泪水,她叫大乔。
- 8.2万字4年前
- 大明头上长了草
- 什么!早起刚睁眼睡得满脸胎记?历史的车轮正滚滚而来?Cao!(一段舞蹈)什么!东北奴儿铠甲已经+13?西北快递李哥即将被裁员?Cao!(一代奸雄)什么!3岁小孩明末搞工业革命?只因为爱发电回到未来?Cao!(一种植物)
- 1.5万字4年前
- 龙战于野之北宋末年
- 这是北宋末年的水浒世界,天下风云变幻,华夏内有四大寇(宋江、田虎、王庆、方腊)作乱,外有金夏辽进逼。身为汉家男儿的夏华在来到这个时代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捍卫汉家山河、保护汉家同胞的铁血征途,为华夏苍生奋斗前进不息,谱写一曲轰轰烈烈的英雄战歌。
- 24.6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