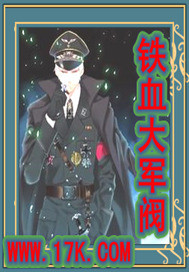第四十一章阿宝入朝一
沉默了一会儿,朱厚熜看看严嵩那花白的头发和凄迷的泪眼,叹道:“夫孝悌者,乃君子立身之本,我大明更以孝治国,严世蕃纵有那样的想法,虽非人臣事君之正道,却也是人子事亲之常理。自古忠臣多出于孝门,他若能移孝做忠,倒是国朝可用之材。你起来吧!”
吕芳扶起了严嵩,说:“严阁老,皇上仁厚,已不追究令郎严大人之罪了。镇抚司那边奴才会去打招呼,不让他们为难严大人,只要你悉心给皇上办差,没准皇上过些时日就让你们父子二人团聚了。”
朱厚熜听得出来,吕芳的话字字句句都是在安慰严嵩,却更是在婉转地规劝和提醒自己不要因一时心软而贻误了大事,便轻咳了一声,板着脸说:“方才朕问及鞑靼求贡一事内阁有何意见,你附议翟阁老,建议朕发六部九卿公议,你觉得如此处置可妥当否?”
严嵩显得十分为难的样子,嗫嚅了半天才说:“论说军情如火,也容不得拖延,但此等大事关乎兵凶国危,一定要慎重,翟阁老建议发六部九卿公议也是稳妥之举。”
刚刚对他有点好感,他竟然又开始耍滑头,朱厚熜不禁又生气了:“内阁不敢酌处,把事情推给朕,现在又想把责任推给六部九卿,这便是你所说的稳妥之举?”
见严嵩低头不语,朱厚熜追问道:“可朕看了你上的那道密疏,翻来覆去说的都是既不可战,又不能和的实情,你到底是何用意?”
严嵩说:“回皇上,圣天子明见万里,臣等智慧不及万一,惟有将实情奏报皇上,恭请圣裁。”
“什么事都要朕来裁夺,朝廷养你们这帮大臣何用!”
严嵩赶紧又跪了下来:“回皇上,恭请圣裁是内阁合议的结果,臣身为新进阁员,不敢另有他论。”
“内阁五位阁员,徐阶有伤在身未能与闻,剩下四位有说可以商量的;有说坚决不能的;有说惟圣天子自裁的;更有你这样跟朕耍滑头的,摆出一大堆实情让朕来猜你的心思!”朱厚熜怒气冲冲地说:“就这样,你们还要跟朕说什么内阁合议!当真以为朕不晓得你们这些个阁老心里都打得是什么主意?!”
看见严嵩战战兢兢地俯在地上不敢回话,朱厚熜仍是怒气未消,冷哼一声,又说:“个个都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又混迹官场几十年,哪个不晓得明哲保身之理?平日都自诩家国之臣,张口社稷闭口苍生,眼下寇犯国门,北直隶数省陷落虏贼之手,数百万百姓流离失所,正需要你们这些阁老赶紧拿出一个保全社稷安定黎民的法子,你们却只顾着打自己的小算盘,怕被人抓住把柄危及自家荣华富贵和身家性命,哼哼哈哈扯上半天,谁都不肯说一句准话,最后就弄出这么个‘原件呈进恭请圣裁’的合议结果来糊弄朕!被朕逼问到头上,又说该发六部九卿公议,惟独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在这样的大事上帮朕想个妥善的法子!这就是你们的事君之道!”
尽管皇上斥骂的话越来越尖刻,严嵩却暗自松了口气:果不出他所料,夏言不但上了密疏,而且还提出了同意议和,有条件地接受鞑靼封贡的意见,此举固然是尽到了人臣的本分,但他虽仍是内阁首辅,毕竟已奏请停职休养,眼下皇上左支右拙,焦头烂额之时觉得他语焉不详,不能尽心谋国;焉知日后不会认为他擅操权柄,暗中仍在保持朝政?看来夏言虽也知道韬光养晦明哲保身之理,毕竟柄国多年养成的勇于任事、独断专行的脾性一时要改也难,这样的首辅,如何能伺候得了刚愎自用且雄猜多疑的皇上!
想到这样,严嵩摆出一副为难的表情,叩头说:“皇上这样责微臣,微臣无言以对,更不敢应对。”
“什么无言以对、不敢应对?”朱厚熜冷笑道:“不外乎就是觉得自己刚刚复列台阁,势单力薄,生怕出什么差错就没了下场罢了!当此国难,若是满朝文武都象你这样做事畏首畏尾,不敢担一点责任,我大明也就亡国有日了!”
一席奏对,等得就是皇上这句话,严嵩心中大喜,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赶紧俯身在地请罪不迭。
朱厚熜突然又说:“朕听说翟銮把调整增补十八衙门部院大臣之事交由你去办,如今过了好些日子,怎还不见你具文报来?”
严嵩说:“回皇上,微臣已将与吏部会商酌定的初步议案呈报夏阁老,待夏阁老看过之后即能呈送御前恭请圣裁。”
朱厚熜的脸又沉了下来:“十八衙门部院大臣大都因伤不能理事,还有好几个衙门的大印空悬,此事刻不容缓,报了翟銮还不够,还非得要报夏言吗?”
“回皇上,内阁上承圣意,下领百官,督率六部九司等各大衙门处理朝政,各部院使司大臣人选素来需经首辅首肯,方能呈送御前由皇上裁夺任用。微臣不敢越俎代庖……”
朱厚熜看看一脸无辜表情的严嵩,突然笑了,却是那种令严嵩不寒而栗的冷笑:“看来朕把你冷藏了两年,你也长本事了啊!朕问你,你是不是也想学翟銮那样做个甘草?”
严嵩赶紧将头又俯在地上:“微臣有苦衷,请皇上明察。”象是犹豫了一会儿,他才说:“夏阁老素来与臣有隙,两年前微臣失爱于君父,退出内阁,夏阁老奉诏回朝理事之后,将微臣在内阁之时票拟擢升的官员尽数罢黜斥退。微臣虽德行有亏,一些奸佞之人为求加官,不得不走微臣的门路,但微臣辅佐皇上掌枢国政不过数月,并没有那么多私党,许多人其实都是卓有劳绩的能吏干员,理应晋升,却被夏阁老一概目之‘严党’予以贬谪罢黜,难免伤及无辜。这两年来微臣每每思之,仍觉于心有愧,更觉于国不利。故此次翟阁老将调整增补十八衙门部院大臣之事交由微臣去办,微臣不得不谨慎从事,此固是微臣一己之私念,更是不愿有人再受微臣池鱼之殃,请皇上明鉴。”
严嵩这么说之后,朱厚熜才想起来嘉靖二十一年末夏言被起复之后,确实曾罢免了一大批被认为是“严党”的官员,当时也有一些大臣和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等言官上疏抗辩谏诤,可自己只想着严嵩是个奸臣,他起用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八成是向他行贿才得以加官进爵,因此对于夏言的奏疏是奏一本准一本,也没有认真调查核实,大概确实有严嵩所说的“伤及无辜”的情况,但严嵩既然与夏言有私怨,他这么说肯定有借机攻讦夏言的意思……
想到这里,他冷静了下来,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只要你一心为公,惟才是用,谁能说你广结私党?”
严嵩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献媚的好机会:“皇上圣明……”
可是,没等他说出更多的颂圣的话来,就听到司礼监首席秉笔黄锦在外奏报:“启奏皇上,高拱求见。”
话音未落,就听到高拱在门外奏报:“臣,巡城御史、监营团军高拱恭请圣安。”
得了皇上的恩准,高拱和黄锦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七八个小太监,抬着两只装得鼓鼓囊囊的麻袋,那两只麻袋里似乎装着两个人。那些小太监将麻袋放在地上之后,立刻就被黄锦赶了出去。
朱厚熜、吕芳和严嵩都是一愣,不约而同地想:营团军又抓到了鞑靼虏贼的重要人物,高拱亲自给皇上送来邀功请赏来了!
哪有这样的规矩!吕芳不禁恼怒道:“高大人这是何意?”
高拱并不理他,冲着皇上跪了下来,说:“皇上,微臣有事要单独奏报皇上。”
朱厚熜知道吕芳因当日兵杖局一事已对高拱心生芥蒂,更知道高拱恩师夏言与严嵩积怨颇深,有心要帮他与两人缓和关系,便说:“你们三人都是朕最信任之人,你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高拱有些犹豫,但也不敢违抗圣命,只好站起身来打开了一只麻袋,一个三十多岁,肥头大耳的人自麻袋里钻了出来。
朱厚熜又是一愣,这分明是个汉人啊!而且,看他一身粗衣短打的装束,也不见得是什么重要的货色,高拱为何这样故弄玄虚地将他装入麻袋用小轿子直送到宫里来?
那个人一钻出麻袋,四下里看看,发现了朱厚熜,便扑到了他的脚下大哭起来:“皇帝哥哥,阿宝终于见到你了!”
“阿宝?”朱厚熜怔怔地说,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这么一个“阿宝”,竟然把自己叫做“皇帝哥哥”。即便他真的是藩王宗室,有外臣在场,也该按着君臣之礼叫一声“皇上”才是,怎么连这个礼数都不懂!
吕芳突然失声叫道:“你……你是宝王爷……”话刚出口,就意识到自己失言,忙改口道:“哦,荣王爷!”
刚见那人钻出麻袋,严嵩眯着眼睛站在一边,也在寻思他究竟是何人,忽然听到吕芳失口叫了一声“宝王爷”,忍不住眉毛一跳,心中暗道一声:“原来是他!”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铁血大军阀
- 简介:这是一个穿越者的奋斗历程这是一个古老民族浴火重生的荣光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凡是从我华夏得到割地赔款的列强们我李默涵不光要收复国土,还要你们赔上利息本人已有三部完本《重生之傲视三国》《明朝第一驸马》《新中华1903》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86.0万字6年前
- 绝品太监
- 简介:黑车夜幕往返皇宫,秽乱后宫。乡下少年刘安一觉梦到二十一世纪。以为仙境,家中贫困不得已准备净身进宫。净身时,其天赋异禀,惊呆了小刀刘和他的徒弟们。老太监三德有了新的想法,带着还没净身的刘安直接进京。书友群:361936780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87.0万字5年前
- 狼牙特战队
- 简介:狼牙刀锋,丛林战神,铁血柔情,谁与争锋。败,也要对手肢残体裂。胜,就要傲气冲天!看一个新兵蛋子的兵王传奇,为战友报仇,为知己义无反顾,为国家抛洒热血,一把飞刀,一把钢枪,一身好功夫,一腔热血,一段奇遇,看新兵蛋子王峰怎样从一个新兵一步一步的成长为众人仰慕的兵王,如何成为站在世界最高峰的兵王。新兵连的遭遇,集训队的苦练,任务中的磨练,知己的患难与共,真挚的战友之情,他们是热血的战友兄弟,他们更是敌人眼中冷血而令人恐怖的狼牙特战队。王峰经过一个一个的磨练,终于成长成为狼牙特战队成员,对手在他的眼中颤抖,在他的脚下惨叫。狼牙特战队令国人骄傲,另对手恐怖,最终王峰带领狼牙特战队站在了世界的最顶峰。成就了一代兵王传奇。新书发布《官道巅峰》喜欢的可以欣赏了,作者号1970489198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05.0万字5年前
- 忆过往,一缕青烟
- 简介:“战勋爵,你放过我吧”男人用着邪魅的语气说“你能逃得掉吗?”
- 11.4万字5年前
- 穿越之争霸在三国
- 简介:特种兵王孙战完成任务回国途中,被系统砸中,将他带到了一个和历史三国极其相似的世界里。这里不但有文臣猛将,还有武侠高手和宗门!孙战他想要争霸天下很有压力!不过他更有动力,因为他有系统的帮助,还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兄弟们的帮助,还有那红颜知己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统一三国不是他的终极目标!。
- 118.8万字4年前
- 盛世先忧
- 盛世之忧,忧盛之长短,忧国之兴衰,忧民之多寡,忧心之聚散,忧法纪之明暗,忧纲常之正乱。忧贫富之不均,忧闲劳之过甚,忧善恶之倒行,忧内外之逆施。
- 13.0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