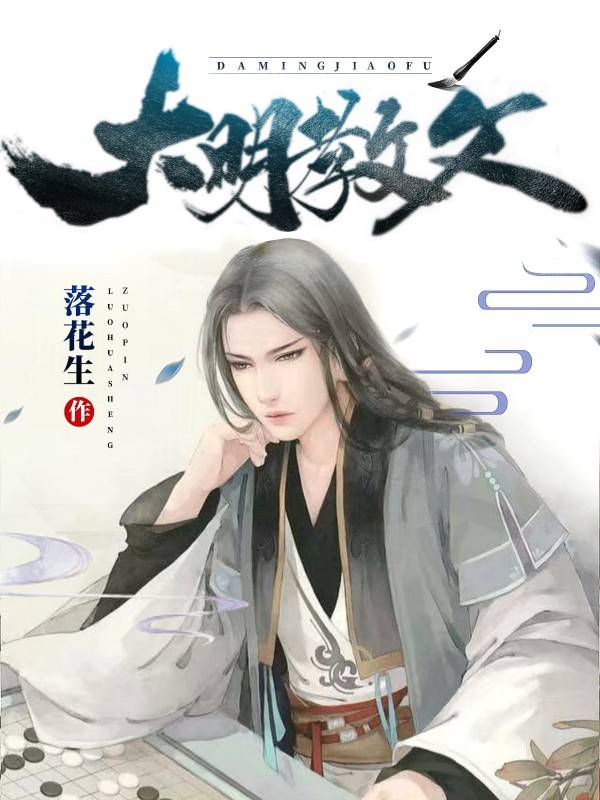第三十二章心乱如麻
好不容易压抑住内心的惊恐,初幼嘉结结巴巴地说:“怎会……怎会这样?且不论辽王德才能否膺九州万方之托,以他辽藩之疏,怎能生出窥测天位之心?”
何心隐冷笑着说:“这又何奇怪的?不正是太岳方才说的那样‘礼乐崩坏之时,什么样的牛鬼蛇神不能冒出来?’吗?说来真是好笑,若以太祖高皇帝血脉之亲疏而论,排一百个也论不到他辽藩,但总有那么一些人,真以为自己是天潢贵胄,自打一落地起,就想问问奉天殿外的那只铜鼎有多重了!”
“可是……可是顾公乃是圣人门徒、海内人望,他怎会……怎会……”
“这就更不奇怪了!”何心隐说:“愚兄知道两位贤弟昔日曾受他颇多恩惠,但愚兄还是要说,眼下南都靖难之事还八字没有一撇呢,那些所谓的士林泰斗、清流领袖就一心要谋夺拥立之功了!”
“不,不会……不会这样……”初幼嘉喃喃地说:“顾公情致高远,视功名利禄如粪土,不会为了什么‘从龙之功’而悖背礼教违逆祖制的……”
“愚兄也不怕两位贤弟着恼,就索性都说与你们吧!”何心隐冷笑着说:“你们的那位情致高远的顾公只怕压根就没把什么礼教什么祖制放在眼里!就以今日之事而论,辽王不经请旨便离开藩邸,已是违背祖宗家法,更僭越动用了亲王甚或太子的仪制,何论礼教何论祖制?更为可恨的是,他们公然带兵入城,欲以武力强行胁迫,监国千岁派出亲卫及南都守备之兵阻拦,他们竟刀兵相向,杀伤诸多军校,若非魏国徐公、诚意刘伯及时赶到,约束部众不与之计较,只恐堂堂南都、太祖陵寝之地,又要遭逢一场兵祸!如斯所为,置圣贤教诲于何地?又置祖宗家法于何地?”
何心隐越说越激动,到了最后,竟大声喊了起来:“当此国事多厄、名教剧变之秋,我辈当戮力同心,克己复礼,使礼仪教化、祖宗成法复行于九州万方,他们这个样子兴兵胁迫,成何体统!倘若众人不服,闹将起来,朝廷大军乘虚南下,致使靖难大业功败垂成,这一份罪责,有谁承担得起!胡闹!胡闹!!简直是胡闹!!!”
张居正心里慨叹一声:辽王不经请旨便离开藩邸、僭越动用了亲王仪制诸事的确是违背了祖宗家法、朝廷规制,但那些起兵靖难的藩王宗室移驾南都,哪个不是如此?在他们的眼里,又何尝有过什么礼教什么祖制?但是,听何心隐的话里,已将原本不屑一顾的那些勋臣改以“魏国徐公、诚意刘伯”这样的尊称,大概是因突如其来的辽王带兵南下之事太过严重,太不得人心。不过,或许对于何心隐这样的江西人氏来说,支持拥戴就藩于江西的益王是理所当然之事,就如同尽管他与辽王有家仇,但若要他从益王、辽王之中选择一人的话,他大概也会更倾向于辽王一点……
但是,撇开乡土观念不论,也不论益王、辽王到底谁更有能力做一位治国安邦、抚民化外的皇帝,何心隐方才所说的亲疏之论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也就是说,按照“少不越长,疏不间亲”的伦常准则和“立君以亲”的祖宗家法而言,作为太祖二十五子的辽藩,无论如何也无法身与宪宗第五子嫡孙的益藩相提并论——一个是已经出了五服,不过因是太祖嫡传血脉,勉强还被认定是宗亲藩篱的旁系子孙;一个是当今皇上的堂兄弟,即便撇开当今失德乱政,已被天下人决意放弃的嘉靖皇帝,他也还是先帝武宗正德皇帝的堂兄弟,兄终弟及,天经地义,辽藩怎能有越益藩而代之之理!圣人出,黄河清,经过几千年来长期的灌输、施行,又经过大明开国一百七十多年的礼仪教化,纲常伦理已成为人们心中凛然不可违犯的“天条”,否则当今皇上也不会因推行有悖于春秋大义、祖宗成法的新政而遭到官场士林的坚决抵制,更不会引发靖难之乱。如此简单的道理,身为士林泰斗、清流领袖的顾公怎么会不知道?他又怎会不顾官场士林,乃至天下苍生的悠悠之口,行此大不韪之事?
想到这里,张居正又回想起了他与初幼嘉当日面谒顾璘之事:他们虚心求教,再三恳请顾璘赐以明示,顾璘却三缄其口,最终也没有对他们说出个所以然来。即便不说是当他们是黄口小儿,“竖子不足与谋”,不能将拥戴辽王之事透露给他们,但至少也应稍加暗示,免得他们在波诿云诡的动荡时局中走错了路啊!难道是听说他们与何心隐厮混在一起,担心他们走漏了消息?如此行事,难谓“正大光明”四字之评……
一时间,张居正的心里纷乱如麻,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加之什么情况都不明了,他也不想多说什么,便收敛了心神,继续听何心隐和初幼嘉的谈话。
初幼嘉因与顾璘感情很深,此刻还在争辩:“不会的!旁人怎么想,愚弟不敢断言。但顾公绝非如你所说的那样。柱乾兄须知国朝自有规制,非有军功,文臣不得封爵,入阁拜相已是人臣之极。顾公当日既能谢绝益王召其入阁的令旨,足见他非是那等贪恋栈位之人,拥立辽藩于他又有什么好处?”
这个话问得好,总不成顾璘还有当王莽曹操之心,期待着辽王日后将皇位禅让给他吧!何心隐也不禁语塞,过了一会儿,才气哼哼地说:“愚兄也不晓得他究竟意欲何为。但凭他能周谋多时,不但说服治下湖广一省各军镇影从造逆,还派人千里远行,不惜重金收买西南安、杨、奢三大家土司,借得数万苗、瑶、侗、壮等南蛮异族之兵之举,所图者必大也!”
初幼嘉梗着脖子还想再说什么,张居正忙阻止他说:“子美兄,事变肘腋,我等什么情势尚不明了,孰是孰非更不甚了了,在此空说无益,还是静观其变,不必再行口舌之争为好。”
何心隐和初幼嘉想想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便停止了争论,其时长随已将酒菜置办齐备,三人移席就坐,何心隐遵从前诺,亲自持壶把盏给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奉酒赔罪。三位年轻人虽则血气方刚,但都是熟读孔孟的大才,也一向崇敬政争不伤朋友之谊的前宋新旧两党领袖王安石、欧阳修那样的名士风范,三杯酒一过,方才的不愉快就全搁开了。
席间,何心隐将今日所发生的事情向两人娓娓道来,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才知道,原来自己今日竟遭遇了一场怎样紧张而又凶险的兵乱……
辽王移驾进京一事之前全无征兆,概因南直隶锦衣卫哗变之后,以各位勋臣家兵重建的锦衣卫不堪其用,又将监控的重点放在了南都官民百姓身上,对于前湖广巡抚顾璘说服旧部拥戴辽王,集结湖广一省各军镇兵士,以及从与湖广毗邻的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借蛮族土司家兵之事一概不知,以致辽王车驾抵达仪征之后才被侦知。
南都主事的那些勋贵大臣都知道来者不善,有心调集军队将他们挡在留都之外,可是又因南都原有的军队绝大部分都调到前方,屯兵于徐州准备再举兵北上靖难,余下的不足五万之众,无力抵抗号称有十万大军的辽王部属,只好一面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南都人心惶惶,再生变乱;一面派出与顾璘有同乡之谊,并称“金陵三杰”之一的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元前往仪征,劝说辽王车驾暂时驻留,容新明朝廷召集文武百官依礼迎驾。
可是,不晓得是顾璘等人瞧破了新明朝廷的用心,还是与顾璘等人早有勾结,陈元竟被顾璘三言两语轻松说动,跟着辽王车驾就直奔南都而来。不但如此,陈元还凭借自己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喝令受都察院下属职官巡城御史节制的五城兵马司守城军卒打开城门迎接王驾,遂使辽王车驾及麾下数万大军顺利进入南京。
监国益王闻说辽藩违背祖制,以僭越亲王仪制的仪仗进京,大发雷霆,传令亲随护卫及南京守备军士阻挡,双方对峙于朝阳门内,一言不合,便相互攻杀起来。眼见着局势即将恶化,几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魏国公徐弘君、诚意伯刘计成匆匆赶来,好言抚慰辽王部属,又喝令本军儿郎率先放下兵器,这才平息了一场几乎又将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拖入万劫不复境地的兵祸!
其后,就在大街上,魏国公徐弘君、诚意伯刘计成在以臣子之礼叩见了辽王之后,代表监国益王及新明朝廷,与代表辽王的前湖广巡抚顾璘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判,开出了种种优厚的条件,意图说服顾璘带兵离京:许诺发府库钱粮犒赏辽王部属,并准许其在号称“富甲天下”的南直隶治下扬州或浙江治下的苏杭二州等三地,任择一地“就食”,可由辽王自行委任官吏开征赋税,新明朝廷一概不予干涉;对辽王部属也“只宣不调”等等。
令人气愤不已的是,对于这样优厚、几乎已经侮辱了新明朝廷威严的诸多条件,顾璘一概不理,问他意欲何为也不说。后经随后赶到的朝廷众位大臣们苦苦劝说,他才勉强答应移师出城,但仍要保留两万兵马驻扎北校场的军营之中拱卫辽王车驾,自己却只带着十来个随从住进了东城的官驿之中……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乱世情缘漫黄沙
- 简介: 他是个亡命孤儿,被东家收留长大。东家突遭兵家提亲逼婚,情急之下,打小与他青梅竹马的东家小姐,便于他私定终身。 大祸临头,九死一生,避难小县。 滚滚黄沙,弥漫了西北边陲鲜为人知的兵匪相争。 情感交错,在小县绚烂多彩的历史画卷中徐徐展开...... 厚重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细腻贴切的描述。形成作品鲜明的叙述特色和令人震撼的真实感。 本书已完稿,绝不太监,质量保证,敬请放心阅读收藏。相信它会像一抹美丽的风景,让您赏心悦目,回味无穷。细读会上瘾。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30.5万字6年前
- 陆战兵王
- 简介:跆拳道少年周力庆贺18岁生日,去酒吧庆生之时,不想遇到了恶霸调戏美女王雅婷,因为看不惯这些流氓之徒的所为,选择出手相助,因为招来了杀身之祸,少年避祸入伍,成长为利刃毒蛇特种部队陆战兵王。我的书友交流群:241911158,我的QQ:807457338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316.7万字6年前
- 梦醒三国
- 简介: 稀里糊涂的穿越到了三国时代,是顺应天命还是开天辟地。在人如草芥的乱世,且看主角如何求生。梦醒时刻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命还是梦。面对众人赵飞得意洋洋的说:“想当年长坂坡七进七出的赵云,是我磕头拜把的大哥。勇冠三军古之恶来典韦是我保镖。”“切!”众人纷纷竖起中指。新书,异界之逍遥圣尊已经发布,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群号211540841喜欢三国的朋友可以来坐坐大家一起探讨探讨0.0.特别强调一句,群里有美女哦!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238.1万字5年前
- 打服为止
- 简介:不服?那就接着打下去,直到你跪服。我军特种兵前身与越军特工的惨烈战斗。
- 28.7万字4年前
- 大明教父
- 理学工学双料博士陈恪穿越到明朝崇祯年间,成为一名寒门士子。由贩私盐白手起家,纵横在黑白两道,一步一步成为大明的教父。
- 1.9万字4年前
- 明朝不值得
- 我从现代来,将往大海去!小富翁李固意外来到明朝,自认没什么大能力、野心的他在明朝有着自己的生存计划。搞一艘船,拉一伙人,在东南亚寻一座岛,当女真人来了就驾船出海,不受那“我大清”的气……
- 14.5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