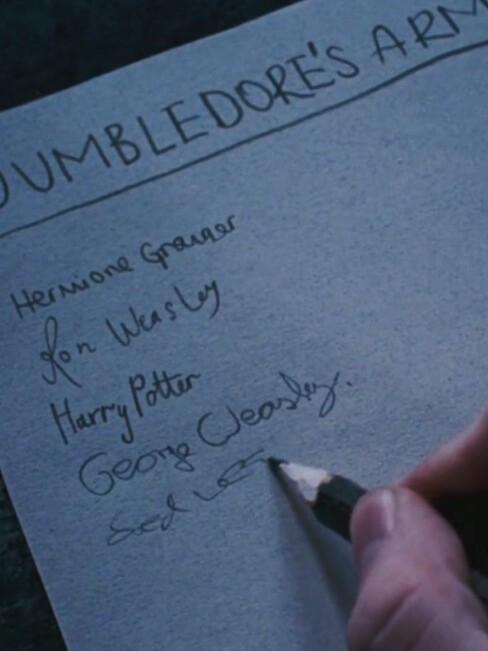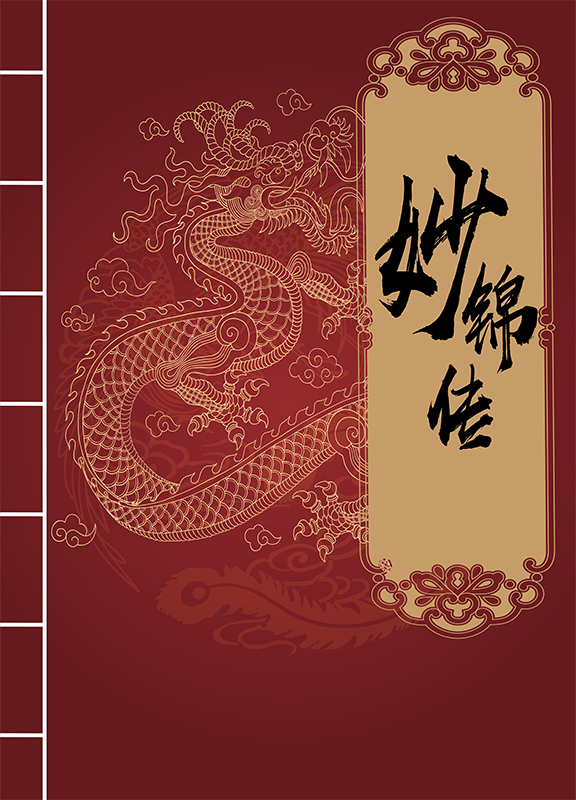第六十一章无心插柳
眼下离中秋节只有两天了。随着暮色渐沉,一轮略见清减,却依然皎洁明净的皓月从遥远的地平面上跃出,开始将柔和的银辉洒向滚滚东流的大江,洒向变得空朦起来的辽阔郊野。皎洁的月光之下,初升的雾气象一层白色的轻纱,缓缓地在江面上起伏飘泄着,使这条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长江,竟也有了几分如诗如画的江南烟水之色。
自古江山美如画,只与英雄做战场。如斯美境当前,江边沙滩上却大煞风景地架着一堆堆的刀枪矛戈和盔甲箭衣。河南卫所军统领钱文义光着膀子,赤着双脚,对面前同样只有一条短裤遮身,密密麻麻排成方阵的兵士喊道:“你们这些龟孙,哪个会水给老子站出来!”
一个个兵士越众而出,在方队前排成一排。看着人数比自己预计的要多出不少,钱文义乐不可支:“你们这些龟孙当教官,一人教一哨。教得好,大头兵升哨长;哨长升队官;队官以上,老子说了不算,给你个龟孙记一大功,报朝廷叙功恩赏。”他看着面前那些喜形于色的兵士说:“够便宜你们这些龟孙了吧!不过老子把丑话也说在前头,要是教不会,老子军棍可不是吃素的!”
接着,钱文义又面向了全军兵士:“告诉你们这些龟孙,这回首攻任务是老子豁出脸面向戚军门争来的!徐州城下我们靠人家营团军的神炮立了头功,已是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强渡长江要是再落到人家的后面,河南人的脸都让我们丢尽了!俺带头,都他娘的给老子下水。十天之内,还学不会的,自个把自个给抹了,省得淹死在江里给老子丢人现眼!”说完之后,他转身就往水里走。
时近中秋,江水已凉,刚踏上去,一股凉意就从脚底板窜了上来,钱文义不禁打了一个哆嗦。身边的亲兵忙说:“军门,水凉,要不您老就别下水了。”
钱文义把眼睛一瞪:“放你娘的屁!让老子在岸上看着,亏你小子想得出来!哪次打仗老子躲在弟兄们的后头?”
有人看着那轻拍堤坝,缓缓东流的大江,犹豫着问道:“军门,这宽的江面,真要游过去?”
“他娘的,营团军那边已练了三天了,再不赶紧些个,吃屎都抢不到热乎的!废什么话!老子这是为着你们这些个龟孙好,对面那些龟孙的阵势你们也都看见了,真打起来,船被打破了,要是不会水,你小子就等着掉到江里喂王八吧!”说着,钱文义索性一屁股坐在了水里,喊道:“都给老子下来!”
主将带头,性命攸关,谁也不敢再有怨言,也不敢再犹豫,“扑嗵”、“扑嗵”跳入水中,跟着那些会水的弟兄,试着在水里扑腾起来。
正练得热火朝天之时,有人眼尖,突然指着远处的江面说:“军门,那边象是有动静……”
此刻已到了二更时分,升上中天的圆月也开始显出疲态,越来越向西天倾斜,而且变得越来越朦胧昏暗。钱文义努力睁大了眼睛,顺着兵士所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迷离的月色下,一个黑影正从远处朝着这边靠近。渐渐地,黑影越来越近了,能隐约看见是一条带篷的木船正拼命朝着北岸驶来。
叛军撤回江南之后,与江防水军会合沿江布防,并在南岸诸多关津渡口都立了水寨,严禁官民船只下水,并派出战船日夜巡防不休。河南卫所军为了不打草惊蛇,专门挑了一片偏僻的河段练兵,却不曾想到还有船从南岸驶来,而且,深夜行船却不点灯,不难猜测,这绝不是一条寻常的船只。
钱文义压低了声音:“八成是对面那些龟孙派来的探子。会水的悄悄靠过去,给老子抓活的,其他人都他娘的别声张,休要吓跑了他们!”
说完之后,他自己都哑然失笑:几千名兵士都在水里扑腾,搞出的动静对岸都能听到,更不用说那条船已经驶过了江心,想要抓活的,谈何容易啊!
说话间,那条船已接近了北岸,或许是突然发现江边漂浮着黑压压的一片脑袋,吓了一跳,停撸踌躇了一下。钱文义正要喝令手下精通水性的兵士赶紧游过去,却见那条船又“呀扎、呀扎”地摇了过来。同时,一个人影从篷里钻了出来,拢着双手低声喊道:“对面是哪家的军爷?”
钱文义立刻猜到这是来投诚的官民或军将,这倒是最近时有之事,便喊道:“是你爷爷我,河南的!快靠过来,爷爷算你起事投诚!”
兴许是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那条船更是摇得飞快,不一刻便冲到了岸前。河南卫所军的兵士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将船直接推上了岸边浅滩,就算要逃,也逃不掉了。
十几个兵士冲到岸上抄起了兵器,围住了那条船,喝道:“滚出来!”
几个摇撸的船丁吓得哆哆嗦嗦不敢应声,都将眼睛盯着厚厚的蓝布遮蔽着的船篷,那里却没有任何动静。
兵士不耐烦了,又喝道:“滚出来!再不出来,小心爷爷手里的家伙不认人!”
这个时候,钱文义也已上了岸,一边披着衣服,一边走了过来,见着他们如此兴师动众,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弄啥哩弄啥哩!船都搁浅在这里了,还怕他们跑了不成?你们这些龟孙怕是又忘了皇上‘不许虐待俘虏’的圣谕了吗?”说着,他冲那条船喊道:“出来吧!说了算你起事投诚,老子说话算数!”
船篷里传出一个人的声音:“敢问将军贵驾、官职。”
“操!老子还未盘问你,你倒问起老子来了!”钱文义正要发火,随即想到堂堂王师该有王师的气度风范,通名报姓也不算什么,便强压下了火气,说:“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河南信阳卫正千户、河南卫所勤王军统领钱文义便是老子我!哎,我说,你架子摆够了,也该出来了吧!,未必还要老子下拜帖请你,你才肯出来?”
遮蔽船篷的蓝布掀开了,两个人从里面低头钻了出来,其中一人身穿官服,一人身着长衫,都是二十多岁的样子。
钱文义冲那位青年官员一抱拳,钱文义阴阳怪气地说:“末将有礼了,敢问大人贵驾、官职。”
兵士哄堂大笑起来,那位青年官员尽管知道他其实是在嘲讽自己,但也不好过于拿腔作势,便说:“在下何心隐,南京兵科给事中。”
“难怪架子这么大,原来是兵科给谏。不知给谏大人大驾光降鄙部,可是纠察军纪,抑或督军催战?职等有失远迎,不胜惶恐……”正在说笑,钱文义突然想起了什么,忙问道:“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何心隐见他如此肆意嘲讽,分明是在故意轻慢辱没自己,心中大怒,但重任在肩,也不敢随便得罪眼前这些粗鲁不文的军汉,便强压着怒火,说:“在下何心隐。”
“何、心、隐……”钱文义追问道:“你真是何心隐?江西的那个何心隐?”
“不才正是何心隐,请问将军可认识在下?”
“何大人可是在说笑话?”钱文义摇头晃脑地说:“去年年初带领举子大闹科场,大人之名便震动朝野,普天之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及至江南叛乱之后,大人姓字更是时时见诸朝廷民报之上,我等军汉再孤陋寡闻,又安敢不闻大人之名?”
咬文嚼字地冒了一阵酸气,钱文义突然勃然变色,喝道:“给俺把这个逆贼抓起来!”
身旁那位青年文士忙拱手说:“这位将军且慢动手,在下与何大人今次前来,是有要事在身……”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可有官职?”
“在下初幼嘉,湖广人氏,区区一名举人,尚未出仕。”
“哈哈!何心隐,初幼嘉!何心隐,初幼嘉!”钱文义激动地搓着手:“乖乖俺的娘哎,搂草打兔子就够让老子美气的很了,没想到竟抓了两条大鱼!哈哈,去年大闹科场的三大要犯,竟然全都让我河南军给抓到了!”
初幼嘉心中一凛,忙说:“这位将军,你的意思说张居正也落入贵军……被贵军拿了?”
钱文义得意地点头道:“不错!”
初幼嘉急切地问:“不是民报上说,皇上已赦免他的罪责,还恩准他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吗?莫非……”
“莫非什么?民报是朝廷喉舌,要明发天下晓谕百姓的,它说的自是真的。”钱文义说:“要说那个张居正,他当初逃出徐州,就被当地官府拿获,若不是俺派人一路护送他到京师,他哪有那样的好运气,能得睹天颜,幸蒙圣恩?”
初幼嘉这才明白是自己误会了,冲钱文义拱手道:“谢将军。”
钱文义说:“你们都是钦案上有名有姓的逆党要犯,谢俺也没有用!抓起来!直送中军帅营!”
原来,自平叛军进抵长江之后,朝野上下都认为平定江南叛乱已是指日可待,内阁便迫不及待地指示吏部和都察院根据投诚官员的供词,将所有被伪明政权封授官职的文武官员拉出了详细的名单,以便平叛军按图索骥,将逆党分子一网打尽。这份名单呈送御览得到朱厚熜的同意之后,便成了钦定逆案。初幼嘉虽未受任伪职,却是“辽逆”余孽,因而也被列为钦案要犯。
何心隐怒道:“休要侮辱斯文,我自己会走!”
“哦?也好!”钱文义一拱手,又阴阳怪气地说:“何大人,请吧!”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重建北宋
- 简介:战略侦察兵李宪穿越到北宋末年,发现大辽国已经完蛋,大宋危在旦夕。可惜没有时间给他折腾,就算三头六臂也来不及,北宋覆灭已经无法挽回。李宪很气愤:完颜阿骨打死太早,老子没赶上。完颜宗望(翰离不)、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弼(兀术)之类的混蛋,如果不搅得你们彻夜不安,那就不算穿越者。李宪究竟想干什么,最终又干了什么,请看本书。本书数字版权由“当当”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320.8万字6年前
- 红色家族
- 简介:以主人公史大鹏家三代人为主线,描写近一个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风云变幻。
- 新书6年前
- 打服为止
- 简介:不服?那就接着打下去,直到你跪服。我军特种兵前身与越军特工的惨烈战斗。
- 28.7万字4年前
- 南宋迷雾
- 一个在现代社会的废材中年男,被一团迷雾带到南宋初年,当然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改变不了他草根,风流的个性。不学无术的他努力在南宋挣扎并享受权利给予的多彩生活。起初他以为是让他回到南宋改变天下人的命运,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 5.2万字4年前
- 作文素材大全
- 简介:在小说APP的一股清流作品,希望你们不要沉迷小说,也能收获积累,本文材料源于本人所积累或书上新闻等渠道,可以摘抄,记得留名,让我知道你们的存在!感谢配合
- 1.1万字4年前
- 妙锦传
- 中国明朝,这个国祚近二百七十余年的大一统王朝,在历史上因其辉煌与黑暗并存的特殊性,一直以来为众人所津津乐道。至千禧之年而下的二十余年里,这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朝代总是被掩盖着一层朦胧,有人唾弃其厂卫的阴狠恶毒,亦有人颂扬其威震八方的天朝国威。但无论怎么说,象征这个朝代的符号总是让人屡屡惊叹。《永乐大典》,《本草纲目》,《纪效新书》亦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难以磨灭的光辉星辰。扫荡安南,南驱倭寇,北攘蒙古,壬辰战争,铿锵铁马之声至今仍旧回旋于耳。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七下西洋,宣仁之治,火枪,紫禁城,内阁等等诸如此类,频频成为历史大家们热烈讨论之对象。三次盛世,两次中兴,一次革新。在古典王朝中,这是极其少见的。而明朝自开国以后,平均五十年就出现一次极度繁荣的社会现象,亦不可不为之惊奇。诚然,脱离洪武之治来浅谈永乐盛世无异于空中楼阁。那么,这个开国仅仅以半个甲子的时间,就快速步入巅峰的王朝,它的背后,究竟又隐藏了什么?又是谁铸就了宏伟的永乐盛世?在这盛世中,又隐藏了多少悲欢离合?请让我们慢慢走进明朝,去细细感受它给我们带来的别样美感。
- 12.1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