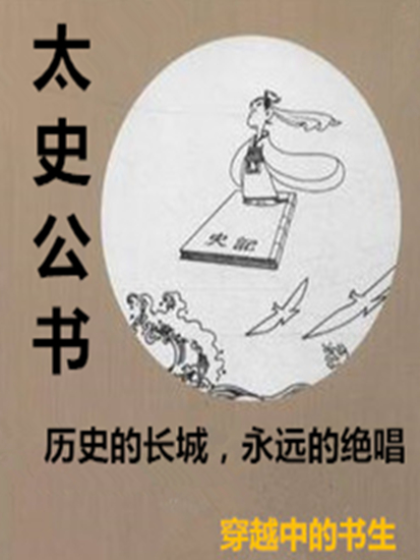第九十一章逼君入瓮
严嵩回到内阁,正在自己的值房枯坐发呆,他的儿子、大理寺丞严世蕃匆匆闯了进来,叫了一声:“爹!”
那份御笺揣着怀里,就如同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严嵩的心情正不好,当即怒道:“这里是内阁,没有什么爹,只有我大明的臣子!未经传唤,你跑来做甚?”
严世蕃吓了一跳,凝神看去,只见父亲面色铁青,额头微微肿起,心中大惊,却不敢问,乖乖地躬身行礼:“回阁老的话,下官是奉我衙堂官刘大人之命,来向阁老回禀三法司会审逆案一事。”
严嵩知道此事,王师南下平叛,一路势如破竹,受此激励,无论礼部还是司礼监,早就迫不及待地将午门献俘大典一应礼仪规范都安排妥当,如今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徐、汤、刘三位谋逆首犯逃匿之后,总要从其他那些乱臣贼子中选出几个罪大恶极且够分量的人来把的场面应付过去。若不从速审结,导致午门献俘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典一拖再拖,朝廷颜面大概也就难保了。因此,江南伪明朝廷的那些达官显贵还在槛送京师的路上,内阁便行文三法司做好准备,一俟逆贼押解至京师,就赶紧会审定谳。大概大理寺定下了儿子参与会审,让他来内阁复命并领受训示的吧!
但是,严嵩却见儿子飞快地使了个眼色给他,便明知故问道:“刘大人可曾定下你大理寺何人参与逆案审理?”说着,将一叠笺纸推到了大案的那头。
严世蕃趋前一步,拈起了案上的一支湖笔,飞快地在纸上写了一个“陈”字,一边说:“回阁老,刘大人的意思是要下官参与此事,故此才委派下官前来回禀内阁。”
严嵩猜到儿子是说司礼监掌印陈洪去找过他,不由得一愣:依照国朝律法,内侍不得随意结交外臣,司礼监凭什么绕过内阁找外臣问话?吕芳走了,那些阉寺越发没有规矩了!再者,自从去年为了追查薛陈逆党一事,在都察院的大堂上公开闹翻直至闹到御前之后,那个陈洪便把严家父子恨之入骨,他找儿子,想必不是什么好事……
正在琢磨,却见儿子将眼皮向上一挑,又写了两个字,一个是“益”字,一个是“鄢”字。严嵩心里“咯噔”一下,原来,陈洪那个阉寺找儿子是奉了皇上的口谕。不过,他当年多次收受益逆贿赂一事,皇上刚才便已当面点明;而鄢茂卿在扬州巡盐御史任上贪墨之事,皇上更是了如指掌,要治他们的罪也不至于拖到今日。如今陈洪专程找儿子重提这两件旧事,到底是何用意?
这个疑问刚刚浮出脑海,立刻便与今日云台奏对之事联系在了一起,严嵩心中哀叹一声:这个皇上越发不好伺候了,恩威并施,双管齐下,一边许下了晋位“三公”的甜枣;一边却又磨刀霍霍,若办不好那件要命的差使,这一刀砍下来,别说是继续位列台阁,掌枢朝政,大概罢官戍边、抄家灭族都有可能啊!
想到这里,他从袍袖之中掏出那份御笺,轻轻推给了严世蕃。
父子同心,严世蕃也跟他方才一样,只看了一眼,脸就“刷”地一下变得惨白,将惊诧的目光投向了父亲,随即恍然大悟,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严嵩面无表情地说:“既是钦定逆案,照例三法司都该出个堂官参与会审。你年资尚浅,本不足以担此大任,但你衙门刘大人既已确定,本辅也不好再加干涉。但你且要好生用心办差,莫要贻误皇命才是。”
严世蕃心领神会地将那份御笺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入袍袖之中,躬身施礼:“是。下官告退!”
严世蕃走后,严嵩将他刚才写的那两张笺纸轻轻地撕成碎片,揣在袍袖之中,然后扬声叫道:“来人。”
一个中书舍人赶紧进来:“阁老有何吩咐?”
“几位阁老可在?”
“回阁老的话,大约一个时辰前,李阁老说要去往兵部议事;马阁老说回户部处理部务,便都出去了,如今阁里只有徐阁老在。”
李春芳、马宪成两个混帐东西竟怯懦至斯,脚底板抹油--溜了!严嵩不免有些恼怒,但想想换做是自己,只怕也要如他们一般早觅脱身之计,便又释然,起身踱到了隔壁徐阶的值房,告诉徐阶他有事也回家,请徐阶代他值宿。
内阁向来是阁员轮班值宿,处理星夜送来的急报。可是,皇上如今宵衣旰食,批阅奏章常至深夜,少不得遇到疑问之处要召见阁臣奏对,还时常三更半夜移驾内阁亲至垂询。因此,自从正位首揆之后,严嵩为了表现自己忠心王事勤勉理政;更为了独承顾问尽揽朝政,就经常在内阁值宿,十天半月也不回家。但是,适才奏对之时被皇上委派了那样重大且要命的差事,即便没有严世蕃报告的这件意外之事,也需要回家静心思量,仔细斟酌。
徐阶见他额头微微肿起,十分诧异,但又不好问,忙应承了下来,并说若有要紧公务,定派人送至严府请他定夺。
回到家中,刚在书房坐定,严世蕃眨巴着那只独眼,笑着说:“儿子恭喜爹爹独承圣意,尽得天心;更恭喜爹晋位三公,位极人臣!”
尽管早就知道自己的儿子机敏通达,远非常人可比,但听他这么一语中的,如同亲历一般,仍让严嵩十分震惊,故意问道:“哦?此话怎讲?”
严世蕃笑道:“爹又在考儿子了。照例这么大的事情,非皇上至信重臣不足以托之。皇上不找他人,而是单单找了爹,足见爹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可是独一无二啊!而且,帮皇上了却了心腹大患,皇上定会论功行赏,爹晋位三公便是指日可待了!”
严嵩自得地一笑,却又摇摇头:“你们这些年轻人从来都是如此急功近利,却不知道‘福兮祸所倚’的道理。在我大明朝为官,功过向来结伴而行。尤其是为父这样的辅弼之臣,今日之幸,又焉知不是他日之祸?尤其是‘位极人臣’四字,断非我严家之福啊!”
“儿子不这么看!”严世蕃热烈地反驳道:“论及阁臣之功过,因议礼得幸的前首辅张璁张孚敬曾有言说的好:‘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是故身在台阁,原本就该甘当替罪羔羊,为皇上的过失担当责难。如遇昏聩柔弱之君,或许真是欲求一善终也难,可当今皇上睿智天纵,明断万里,柄国大臣谁中用谁不中用,心里自然有数。夏言那个老东西缘何能再度受宠而把持朝政,薛陈二逆夺宫之变那样的奇惨祸变也未能伤他分毫,不就是替皇上顶下了新政的黑锅吗?儿子看来,他推行新政,再有劳绩,终归只是朝廷的事;爹变革《宗人法》,断绝了外藩窥测天位的念想,可真真是给皇上去除了心腹大患啊!两者相权,孰轻孰重,皇上心中自然有数。他尚且如此,放眼大明,还有谁人能与爹相提并论?”
听了儿子这番宏论,严嵩心中也暗自称许,但嘴上却还是矜持地说:“是这个理,可话却不能这么说。夏言辅佐皇上推行新政,富国强兵;为父辅佐皇上限制宗室,巩固国本,都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哪有什么高下之分?这种话在家说说也就罢了,切不可为外人道也,免得旁人嘲讽你我父子二人挟功骄矜,非人臣事君之道。”
见儿子似乎还不以为然,严嵩又说:“平叛军张、陈二位勋帅和吕公公呈上的请罪疏已明发邸报,想必你也看到了。半载辛劳,历经战阵,辗转于成败死生之间,上托皇上齐天洪福,下赖六军将士效死用命,终得以功成,剿平了我大明开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叛乱,又兵不血刃克复南都,保全了太祖陵寝,这是何等之大的社稷之功!只因没能抓到徐、汤、刘三位谋逆首犯,擎天保国之功便一风吹了,这且不说,两位勋帅还得自请解除兵权,吕公公更是自请为太祖高皇帝守陵。家里现放着成祖文皇帝御赐丹书铁券的两位超品一等爵,还有皇上最亲信的大伴尚且如此诚惶诚恐,为父位列台阁机枢重地,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渊履薄尚难以自安,又岂能以晋位三公、位极人臣而自得?”
严世蕃说:“爹以为张、陈二位勋帅和吕公公是获罪得咎?依儿子看来,他们才真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正是爹方才说的,他们剿叛平乱,立下了社稷之功,吕公公是皇上的家奴,就不必说了,张、陈二人已是超品一等爵,皇上还能拿什么去赏他们?未必还能效法太祖追封徐达为中山王、常遇春为开平王之例,在他们百年之后也追封个异姓王不成?拥倾国之兵,挟不赏之功,又遇到这么一个雄猜多疑的皇上,那才真是祸在不测……”
这层意思严嵩也曾想到,但毕竟妄猜圣心非人臣之所敢为,因而只是一闪念而已,如今严世蕃如此肆无忌惮地说了出来,令他十分不快,更怕儿子得意忘形之下再说出什么不恭的话,忙转移了话题:“行了!事君惟忠,待人以诚,这等诛心之论不说也罢。那份御笺你可仔细看了?”
正说的起劲却被父亲喝止,严世蕃颇为扫兴,但随即便明白了父亲的殷切苦心,也不强辩,将一份奏疏的草稿递给了严嵩:“儿子已代爹草就一疏,请爹过目。”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抗战游侠
- 简介:“我愿永不超生,换得日本人下地狱,如果上天不帮我,那我就亲手杀的他们下地狱。”----------陆远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独来独往,以一敌众,杀敌无数,所向无敌。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亦是无数中国人永生难忘的痛苦记忆,数以百万计心怀家国天下的中国人葬身在这场战事中。弱冠之年的陆远为了心中的那份坚持和侠义之心,战上海、定南京、孤身出没于日本本土,杀的日军人头滚滚,令所有日本人闻之色变。用心中的坚持和一颗为国为民的侠义之心,在波澜壮阔的抗战年代里演绎出一番不寻常的侠义风范,同时成就出一段中华大地上的热血传奇谨以此书向抗日英雄致敬。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207.7万字6年前
- 女皇十二钗
- 简介:一个人能有几次重来的机会?从穿越,到重生。我经历了一见钟情的爱恋,刻骨铭心的背叛。重生后,我以为我占尽了先机,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可是,命运又将他们带到我面前。从前我怜惜的,纵容的,钟情的,再见面时,我却用尽一切的办法不想再与他们有任何的关联。只因我知道他们爱的人,从来都不是我。我爱过,爱过也伤过,感谢他们成就了重生的我。这用尽了我一世的幸运。人们都说她太疯癫,再大的悲伤也无法在她心上驻留。笑着哭了,哭到笑了。人生便是如此。这,不好么?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76.4万字6年前
- 抗日之铁血军旅
- 简介: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记下一段红色的历史。久久无法忘怀的曾经、那被鲜血侵染的过去。请求赐予重生的命运、回到那篇红色的土地。想要改写哀伤的曾经、宁愿只能挣扎的前进。我怀着一颗悲痛的心、记下一段白色的历史。久久不敢回忆的曾经、那被白雪覆盖的过去。如果给我重来的机会、来到苍白无力的过去。让我洗刷耻辱的记忆、哪怕只会惨烈的死去。那一年、鬼子侵华,烧杀抢掠。那一年、抗日英雄,宁死不屈。那一年、血光冲天,尸横遍野。这一刻,紧紧捏紧拳头,想要回到过去,成为那万千抗日英雄中的一名。不一样的穿越,不一样的体验。作者群47879080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69.4万字5年前
- 校草大人万万岁1
- 简介:踏入北家的第一天,席小童总算明白了——北奕宸,人前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小少爷,但是背后却是天天折磨自己的大恶魔!六岁七岁八岁一直到现在,这个恶魔还在欺负自己啊!“北奕宸,你闹够没有啊,欺负我那么多年,你还不腻啊!”席小童翻着白眼说道。坐在她对面的美男子,俊美无双的脸上露出一抹浅浅的笑容,站起来伸手勾起她尖尖的下巴,附耳柔声道:“不腻,因为我打算欺负你一辈子!”本书数字版权由“龙阅读”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22.9万字5年前
- 超级基地之龙行天下
- 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夜凌天偶然获得超级文明基地的认主,从此他的命运被改写,是做科技的巨头?还是……PS:【本书情节,内容纯属虚构,与现实政治,经济无任何关系】
- 12.3万字4年前
- 水煮《史记》
- 简介:如何水煮?如何将历史与现实,来一番有趣的关照呢?历史,其实很有趣,可以正经地解读,或者不正经地另读?有什么不可以?历史从来都是一个小姑娘,扮成花,弄成云,如果你的想象够穿越,真的,所有的历史,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不过是还在发生的现代史。太阳底下无新鲜事。那么,水煮一番《史记》,也许,别有一番滋味呢
- 4.2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