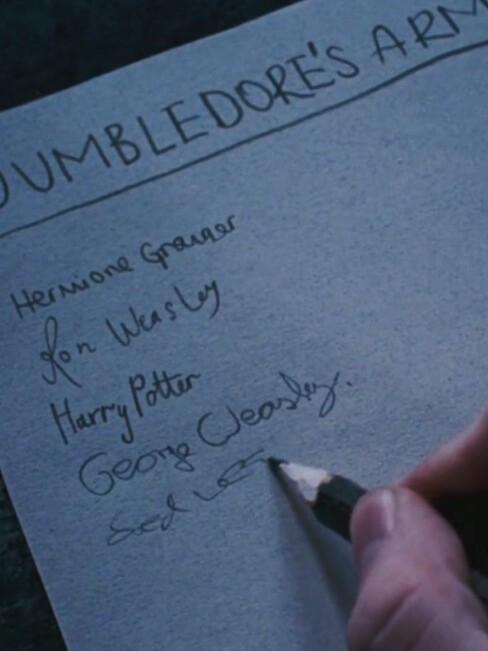第十四章唯才是举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朱厚熜接受内阁及礼部的奏议,下旨颁布“唯才是举诏”,对明经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改易,增开农经、医理、算学、格致、经济等时务科,按照一定名额,由两京三品以上大臣和外省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举荐贤能之士,也不拘有无举人功名,与明经科举子一同公车送至京师参加次年春闱大比,论才取士,中式之人经殿试确定名次,一律授予某科进士,授官任职。
同时,诏书中还号召全国士人学子除了要一如既往地钻研经义,孜孜以求圣贤修齐治平之道,还要致力于各种实用之学,报效家国社稷;并引用明成祖朱棣 “致治之道,以育才为先。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蓐而欲望秋获,不雕凿而欲望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 的圣训,要求各省学政衙门督令省府州县各级学堂招纳实学之士,开设时务学科,广泛培养各类有用人才,以此作为对学政和各级学官考成法的重要内容,予以考成奖惩;言称将在适当时候,效法乡试之例,加开时务科乡试,使得时务科取士与明经取士一样逐步走上正规,广纳贤才,为国所用。
一石激起千重浪,与其他各项新政举措一样,增开时务科的主张引起了不少死抱着“八股抡才,明经取士”祖制的迂腐朝臣,尤其是那些翰林院的清流词臣们的强烈不满。但让他们聊以**的是,时务科中式举子只能称某科进士,已经比单称“进士”的明经科中式举子低了一等,还有时务科进士不能点翰林,不能任内阁辅臣和礼部尚书、侍郎的若干规定。可见皇上还是明白,四书五经、经学义理才是治国之道,其他什么农工医卜都只不过是术,道不足才要术补之。也便是说,朝廷增开时务科不过是一时应急救难之需,大行于九州万方、充塞于天地之间的,终究还是圣贤天人性理之道!
朱厚熜的本意可不是这样,但经过了这么几年的挫折和动荡,他总算是明白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事情总得一步一步去做,也总得要让下面的臣子们能做的下去。科举制度自隋唐至今已经实行了上千年,尽管积弊重重,但毕竟关系到全国读书人的前程出路,要想彻底废除,谈何容易!甚至,在时务科进士逐步走上朝堂,成为一股新兴的官僚势力;以及出于通过应时务科谋求晋身之阶的考虑,那些士人学子关注和研究实学成为一种风气之前,进行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是不行的,只能这样通过增开时务科和在各级学堂开设实学课程,悄悄地进行渐进式的改良。因此,那天内阁辅臣告退之后,他思虑再三,最后还是接受了徐阶的这一奏议,作为对万恶的旧社会、顽固的封建思想的妥协。
不过,事实证明,这样的妥协倒是很有必要,朝臣们只闹腾了一阵子就不闹了,两京一十三省撒下去的厂卫番子暗探也没有捕捉到有士人学子闹事的迹象,让他那颗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到了肚子里,原本以为肯定要受到天下人唾骂,并准备厚着脸皮承受言官词臣雪片一样飞来的弹章奏本的四大阁员都松了口气。
其实,朱厚熜和内阁辅臣都被这几年来接连不断的变故折腾得近乎神经质,简直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增开时务科,固然会引起那些科甲正途出身,凭借着八股文章挣得一份锦绣前程的朝臣们的不满,但朝廷广开纳贤之门的做法,却得到了广大士人学子的赞同——数十万生员就靠着科举取士、三年一比谋求一条出路,可那条出路何其之窄,旁的不说,每科春闱,至多不过百十来个进士名额,千军万马都要挤过那条独木桥,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许多人考了一辈子也困守场屋,甚至还有祖孙三代同下科场应试的滑稽之事。
如今朝廷又增开了诸般时务科,无疑是在那道紧窄的科举小门旁边又开了几个墙洞,时务科进士虽说比不得正牌进士那么荣耀,毕竟也是一条晋身之阶,那些对自己经学造诣没有信心或对八股制艺早已厌烦透顶的生员们纷纷扔掉那些专一用做科场利器的程墨房稿,钻研起了诸般实用之学。往常坊间只有少数人问津的农经医书和百工之书被一扫而光,书坊不得不赶紧搬出尘封许久的雕版赶印,着实发了一笔小财。与之相对应的,高拱于前年奉旨写就的论实学思想的文章也被再次翻出来广泛传抄,高拱更被那些有心投身致用之学的士人学子奉为今贤,继前年率营团军力抗鞑靼虏贼之后,再次名声大噪于两京一十三省。
举荐生员应考时务科,本来是那些京官和地方督抚大员借机敛财的大好机会,手中的举荐名额既可以大送人情,又可以换银子。可是,朱厚熜知道,《大明律》载有明文,科举取士乃是国家抡才大典,有暗通关节营私舞弊的一律罢官撤职,贬谪充军,情节严重者还要抄家灭族,即便如此严刑峻法都不能避免那些贪官污吏油锅里捞银子,更何况这样不经考试的举荐。因此,他效法京察拾遗之法,特令都察院行文各省巡按御史加强监督,随时指斥谬误,参奏不法。为了防备抚按联手舞弊分肥,他明确规定,若有滥竽充数者,要追究举荐之人的欺君误国之罪。可这样一来,又给他带来了新的担心:京官们为了博取“造福桑梓”的美名,更能援引同乡成为羽翼,大概不会放过这样拉拢本乡才子的好机会;可那些因循守旧、四平八稳的地方牧民之官会不会怕承担责任,宁可浪费名额也不愿意举荐贤才?因此又不得不别出心裁地规定,各省未能完成核定举荐名额,要相应减少该省乡试举人名额。明经取士,为国举贤是国家大政,关系着各省督抚学政的政声,更关系本省生员前程,就冲着京城有那么多的省籍当道大僚,随时都会也不敢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做手脚。
如此苦心孤诣,恨不得把所有的漏洞都堵塞于未然,令朱厚熜苦不堪言。但是,正所谓智者千屡,必有一失,更何况增开时务科这样开天辟地头一遭的新鲜事儿,种种荒谬绝伦匪夷所思之事还是让他始料不及,比如某省巡抚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核定名额,亲自出面宴请省城几大名医,不论他们是否已经年过古稀,也非要他们同意出山应试医理科。其中一位名医愤然对曰:“太医院医正早年曾随老朽习学针石之术,如今但有疑难医案,也少不得要写信向老朽讨教,抚台大人莫非竟要老朽去拜他为房师?”此事被传为一时笑谈,更被别有用心的好事者编成歌谣予以讥讽。朱厚熜怒不可遏,以“愚顽失政”的罪名勒令那位巡抚致仕,并杖责了好几位借机攻讦增开时务科的朝臣,这才平息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可惜的是,朱厚熜想让徐渭进画院供职,为穷困潦倒的他谋一条衣食无忧,安心艺术创作的殷勤美意,不但被朝臣们误解,就连远在绍兴的徐渭本人也不领情——当那位假扮成丝绸商人的镇抚司暗探再次突然出现在徐渭的面前,声称自己已经为他打通关节,可以举荐他入画院供职时,徐渭先是错愕了好一阵子,继而感动得无以复加,最后却还是婉言谢绝了。
那位假扮成丝绸商人的镇抚司暗探受高振东指派一趟又一趟地往绍兴跑,早就窝了一肚子火;而且,他若是不能说服徐渭,回去之后就无法向三爷交代,因此对徐渭三爷的好意这种“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态度十分生气,怒道:“你这个拗相公!莫非供职画院,竟比不得你在这里卖字鬻画的好?看看你现在的穷酸样儿!守着你这个破字画摊,整日价吃风屙屁,还要受人白眼,可若是三天不开张,家里就要吊起锅子当锣敲!穷成那个样子,还充什么英雄好汉!”
那位暗探说的一点也不夸大其辞,徐渭头上戴着一顶旧毡帽,一身粗布衣裳已经洗得发白,几乎看不出原来颜色,经常伏案写字做画的缘故,右边的手肘处还打了一个偌大的补丁,脚下那双旧黑布鞋跟头上的毡帽一样,也都是补丁摞着补丁。更有甚者,眼下已进冬月,他的夹袄或许还在当铺里,身上那件单薄的衣裳根本无法抵御渐起的寒气,脸上冻得青里透紫,鼻子也冻得通红,比街上的那些店伙农夫还要寒碜。
尽管这位相交日浅的商贾朋友话说的很难听,但那份豪爽侠气和古道热肠令徐渭十分感动,陪着笑脸说:“柳兄(那位暗探托名柳青),非是小弟不识好歹,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大哥的美意,书画之道本是高洁清雅之事,拿来换取口食已是无奈,更遑论以之为本业……”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明末最后的太子
- 简介:一个落寞的公司老板穿越了明末最后悲催的太子,自己必须改变命运,开启了一段改变历史佳话。
- 1.5万字6年前
- 抗日之战将传奇
- 简介: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川军“死”字旗他是让日寇胆颤心惊的魔鬼,也是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他是让外国人头疼的无赖,也是深受国民爱戴的英雄。民族生死存亡之时,他高举抗日大旗,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QQ:1831985199微信公众号:尘土nn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443.3万字5年前
- 回到大航海时代
- 简介:南海之上,一艘中国籍的渔船遇到了穷凶极恶的海盗,渔民主角大显神威,犹如银幕硬汉一般,孤身斗海盗,全歼顽敌,却倒在最后一颗子弹下,阴差阳错的穿越到明朝初年。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以官方的身份称霸海洋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为中华的史页书写上了光辉灿烂的一笔。有幸重生在这个年代,主角董宇将有何作为呢?请跟随本书,随主人公一起去扬帆出海,大战海怪,决战海盗巨枭,智斗蛮夷,傲视弹丸小国生番蛮祖,纵横黄金航道,采摘稀世珍宝黑珊瑚,采香获取超级水沉香,灭倭寇,造巨舰,扬威地中海,发现新大陆,让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的名字从历史书上消失,好望角、合恩角从此更名...【纯属虚构,请勿模仿】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66.7万字6年前
- 横扫晚清的无敌舰队
- 简介:20**年,一支付责保护中东某国撤侨任务的舰队穿越到1900年9月,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而在现代社会中深受各种穿越剧穿越小说洗脑的穿越者们,立刻接受了穿越的现实,并且各有打算,有人想利用未来的科学技术称王称霸,甚致建立全球霸权;有人想靠自己的力量,改写中华民族的这一段屈辱历史,甚致实现普世价值;也有人想妻妾成群,腰缠万贯,过上旧时空过不上的腐败奢侈生活;还有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野心、梦想和理想。但这次穿越者们面对的不是落后无能的农耕时代国家,而是有着强大动员、组织能力,和相当科技能力的近代列强,就连历代穿越者们引以为傲的金手指也未必有明显优势,因此三心二意,各怀心事,又没有主角光环的穿越者们能否在这个乱世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412.7万字6年前
- 作文素材大全
- 简介:在小说APP的一股清流作品,希望你们不要沉迷小说,也能收获积累,本文材料源于本人所积累或书上新闻等渠道,可以摘抄,记得留名,让我知道你们的存在!感谢配合
- 1.1万字4年前
- 曹操的主厨
- 简介:穿越前,我是一名美食主播,主打自主烹饪;穿越后,一位黑长直黑丝御姐(封面那个),强横的告诉我,今天开始我就是她的人,于是我成为了她麾下的主厨,这个女人叫做曹操,表字孟德,闺名梦。在这个世界,男性自春秋之后,逐渐失去阳刚和暴力,使得女性上位,捍卫家园。偏偏女性嫁人后,又能做到专情和温婉,小鸟依人。一开始,我以为穿越到娘化的三国时代,结果才发现这个世界的恶意,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 1.7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