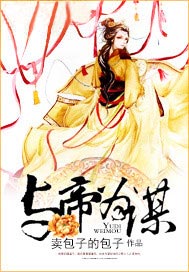第三十五章大祸临头
杨博迎着俞大猷和戚继光两人投来的惊诧的目光,缓缓地问道:“依两位兄台之见,海瑞所议井田制可能施行?”
俞大猷和戚继光都是军户出身,不懂这些民政赋税之事,都说:“请惟约兄不吝赐教。”
杨博斩钉截铁地说:“纯属空论!莫说朝廷必不采纳,即使采纳,照他这一套去弄,只怕不独大乱初定的江南,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都会先自大乱起来!”
戚继光若有所思地问道:“莫非便是徐渭方才说的夺富户之田分发百姓,恐生事端的意思?”
“还不只如此!”杨博说:“以国朝现有田亩而论,每户授给五十亩,确有富余,可地分南北,田有良瘠,人有多寡,如富庶之江南,地少人稠;而苦寒之北地,却是地广人稀,岂可一概而论之以定额?只以海瑞曾任职的昆山而论,设若你元敬有十亩田,可愿意换山陕之田?莫说五十亩,一百亩也不换!做官尚有‘宁为长江知县,不为黄河太守’的说话,更遑论黎庶百姓!还有,全国均一田赋,更断无可行之理,浙江一省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每年上缴赋税却一直占全国七分之一,而南直隶苏州、松江两府田赋,更超过其他省份数倍之多,如若均一,苏州、松江两府百姓固然得其实惠,所缺之额,岂不要加诸其他省份百姓头上?若其他省份不加额,国家财用岂不骤减?皇室用度、百官之俸、兵士之饷又从何而出?皇上心中装着九州万方,断不会如他海瑞一般坐井观天,只看见他身处之苏州及左近松江两地,是故愚以为,此议断不可行,以皇上之天聪明敏,也断不会采纳!”
杨博一番侃侃而谈,竟是把海瑞的议复上古先王井田制之策驳的一无是处,甚至,听他言语之间流露出的意思,将海瑞的策论定性为祸国之乱政也不为过分。偏偏他说的入情入理,俞大猷和戚继光也无法替海瑞分辩,俞大猷只得试探着问道:“即便海瑞囿于眼界,只顾着为治下小民请命,提不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良法善政,但他应的是能直言极谏科,朝廷增开此制科是为求取直言,以皇上之睿智仁厚,当不会以建言获罪吧?”
杨博又长叹了一声,说:“毕竟曾出身于我营团军,我又何尝愿意做此之想?只怕事与愿违啊!旁人或许不致因建言得咎,可是他海瑞,却就难说了。他与当朝首辅严嵩昔日有隙,又不认得其他当道大僚,若是严嵩以此发难,谁能帮他说话?”
戚继光不同意他这样悲观的论调,反驳道:“严嵩再是专权擅政,说破天海瑞也只是一个建言失当之过,他又怎能置海瑞下狱论死?”
“论论别的事倒也罢了,惟是国朝以农耕为本,这田亩之制,岂能随便妄议改易?这一条就先是罪过;其次,井田之制固然是上古先王的良法美意,却不合用于后世,前汉大奸巨恶王莽便是议复井田制而亡国破身,严嵩当可以此发难,指斥海瑞居心叵测,学的是赵高毁秦之法,意欲坏我大明江山社稷,诛心之论,却可当成莫须有的罪名。还有其三,”杨博压低了声音:“井田制之议可是当年建文逆臣方孝儒的主张啊!”
俞大猷和戚继光都为之一凛:一百多年前,太祖高皇帝之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大宝,是为建文帝,在一帮左班文臣的辅佐下,开建文新政,宽刑减赋,变更祖法,改易官制,并厉行削藩,以致成祖文皇帝起兵靖难,开出的逆臣名单共计二十九人,时任文学博士的方孝儒因颇受逊帝建文的信用,国家大政也多咨询于他,因此在逆臣名单中排位第四,仅次于太常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三人。嗣后,成祖文皇帝攻克南京,招方孝儒起草登基的诏书。方孝儒在朝堂上嚎啕大哭,声震殿陛。成祖文皇帝苦劝不止,授给纸笔,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方孝儒写下四个笔墨淋漓的大字“燕贼篡位”,抛笔于地,边哭边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文皇帝怒其不为人君所用,曰“诏不草,灭汝九族!”方孝儒对曰“便十族奈何!”遂被成祖文皇帝收其十族(九族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十族在九族之外,再加上门生一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弃市,本人被凌迟处死之后,还被拆散骨骸弃之于野,捡拾其遗骨者也被处死。这等酷刑亘古未有,是为后世乱臣贼子者诫之。如今海瑞沾上这样的事,只怕杨博说的他“有囹圄之灾、性命之虞”或许都失之过轻了!
“那么,”戚继光说:“依惟约兄之见,事情可有转圜的余地?”
杨博摇摇头:“事已至此,惟有期盼天佑忠良了……”
“依我看来,或许还不至如此吧,”俞大猷说:“仁厚无过当今圣上,当不会计较海刚峰那样傻气迂腐的书生之见……”
“皇上自是仁厚无双,可是,”杨博说:“如今江南初定,人心思安,皇上也为了顾惜一个海瑞而不顾满朝文武乃至天下官绅豪强的哓哓众口……”
戚继光突然想起了什么,忙说:“若真如你惟约兄所说的那样严重,海瑞的墨卷,谁又敢呈送御览?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从主考官那里想想办法!惟约兄,你是翟阁老的门生,与今科主考徐阁老师出同门,可否求他帮忙说话?”
杨博尴尬地说:“徐阁老为人一向谨守礼法规制、持正无私,此次点为会试主考,听说每日不在考场就在内阁值宿,连吏部和翰林院的衙门都不去了,偶尔回府也是杜门谢客,不受私谒;再者说来,我虽与徐阁老有那样的渊源,可是我生性不喜与官场中人交往,一次也未登过徐阁老的家门,即便今次能进得府门,见到徐阁老本人,贸然请托此等大事,他也断不肯卖个面子与我……”
其实,杨博为尊者讳,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口,徐阁老与他的师相翟阁老一样,虽都身处朝政中枢,位高权重,却都是谨小慎微,掉片树叶都怕打破头的人,此事一旦被人做成那样偌大一篇文章,牵扯进来的人一个也跑不了,他才不会淌这一汪浑水,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
俞大猷和戚继光这两年里分别与杨博共事,深知他不象高拱那样能慷慨任事,甚至,他一个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志向却不是位列朝堂、柄国执政;而是“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颇有汉朝班固投笔从戎之遗风。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对朝政党争感兴趣,更不会主动掺和到这种事情里来,也不能指望他能象高拱一样仗义执言。
沉默了一阵子,戚继光说:“不若我等明日一同求见皇上如何?”
杨博自然知道他的意思,又摇摇头,说:“此议不妥。故友闲谈之言,不足以污圣听,此其一;其二,国朝文武分班,职分也各有所司,田制涉及民政,非你我可以随意置喙之事,更遑论关乎国家抡才大典;其三,这些毕竟只是我们的猜测,妄测天心,已非人臣所该为啊!”
这也不行,那也不愿,分明是怕担干系,不愿施以援手!戚继光面色一沉,想要再说些什么,却听杨博说:“其实,或许不必我等多此一举,今日镇抚司三位太保爷在,都听到了海瑞的话,岂能不奏报皇上之理?我等还是稍安勿躁,静候皇上裁夺吧!”
杨博没有猜错,今日做东的镇抚司大太保杨尚贤在天香楼与众人分手之后,没有回自己在东城的府邸,也没有回镇抚司的官衙,而是快马加鞭,赶在宫门落锁之前进了大内,径直来到东暖阁,跪在门外奏道:“奴才杨尚贤给主子复旨来了!”
原来,他今日做东宴请营团军诸位军官,乃是奉了皇上的密旨,不用说,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皇上也想知道海瑞应试策论所议何事,他总算是不辱使命。
听完杨尚贤的详情奏报,朱厚熜也如方才的杨博一样,皱着眉,抿着嘴,样子既象是想笑,又象是要哭,最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好的,朕知道了。你辛苦了,且回去歇息。”
待杨尚贤走了之后,朱厚熜才重重一掌拍在了御案上:“好你个海瑞,你是一天也不想让朕省心啊!”
你违抗朝廷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既定国策,在昆山搞的一塌糊涂,我不跟你计较;为了让你捞个进士的学历当上御史,我不顾朝野上下的反对,专门为你量身打造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为了让你稳稳当当中个进士,我还专门派锦衣卫拿着国家公款请客,就为了查探你到底论的是什么,好到时候给你开后门。可你论什么不好你来论田制!你论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一个进士的学历,可你论田制,这个进士,你让我怎么给你?
不错,“耕者有其田”是古往今来中国老百姓的梦想,也是多数农民起义用来鼓动民众、屡试不爽的口号;不错,我是曾给俞大猷下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密旨;不错,朝廷兵马平定江南叛乱之后,我也曾将那些参与叛乱的藩王宗亲、勋臣贵戚的田地抄没,分发给百姓。可那是什么形势?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抄他们的家,分他们的田,谁敢说半个不字?
如今叛乱刚刚平息,国朝赋税重地江南百废待兴,南边的倭寇、北边的鞑靼都还没有搞定;明朝最大的隐患建州女真部的分化瓦解、迁徙异地刚刚完成了相应的军事准备,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废弛海禁、与西洋诸藩国互市通商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对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显现出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让我土改,我能吗?我敢吗?
现在已经不是你能不能中进士的问题了,而是怎么才能保全你的性命!自从朝廷开科取士,我这个皇上每天看考卷看到头晕眼花,一天顶多睡两三个时辰,六宫三千粉黛都撇在一边,当这个劳什子的皇帝我容易吗我?你还要给我找麻烦,你诚心的吧?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与帝为谋
- 简介:他是旧朝皇子,肩负着复朝重任,步步为营却也将心爱之人计谋在内;他是当朝太子,腹黑隐忍誓在朝中定下一足之位,老谋深算却陷于与她竹马初见她是旧将后裔,聪慧机敏与帝为谋立平天下,却终究难敌挚友为敌。两个女人,一生的战争,串起了北楚乱世之下的战争权谋与爱恨纠葛……时逢乱局,几番金戈铁马几番生死与共,谋复国、平天下,谁才会是最后的枭雄,谁、与帝为谋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17.8万字6年前
- 草原特种兵
- 简介:蛮荒,森林,戈壁,草原和蓝天,寒风,饥荒。严酷的生存环境,争夺食物的生死斗争。山神,毡房,羊群,黑暗和狼嗥,尊严,勇气。宏伟的草原帝国,幽深雄壮的民族史诗。在华夏5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仅仅存在井然有序的耕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巍然高大的城邑宫殿,规划完备的道路桥梁。我们还有另一种记忆,那是骏马弯弓的自由驰骋,恩仇必报的快意人生,统治人类心灵的不是人间的帝王,而是长生天的喜怒奖惩。我们的血液里,同时流淌着游牧与农耕,圣贤与天神,融合与仇恨。这里讲述的,就是:草原帝国的史诗铁血男儿的历程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65.9万字6年前
- 麻雀之海棠依旧
- 简介:喜欢的话,可以加我的QQ和微信QQ:2014511509微信:13933729281谢谢喜欢这本书的网友们,我会尽量更新的
- 0.9万字6年前
- 霸宋西门庆
- 简介:泱泱大宋,水深火热,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烽烟四起,外族觊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且看我,凭手中长剑,青锋三尺;唤世间好汉,铁血一心。虎贲三千,复收燕云旧地;龙飞九五,重开华夏新天!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281.5万字6年前
- 闻晏
- 简介:遐迩闻名四海晏然(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 2.4万字5年前
- 上古密约之山海经
- 简介:第一章:讲述的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故事,上古时代九婴乱世,慕容氏,报兄仇,专研魔之力,继而千年一场养女风波,本剧出于山海经小说一书,金木水火土,五官自我牺牲,敌力而退的故事,最终他们舍生取义,以身锁妖,再一次履行千年以下的保卫天下的约定。
- 0.1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