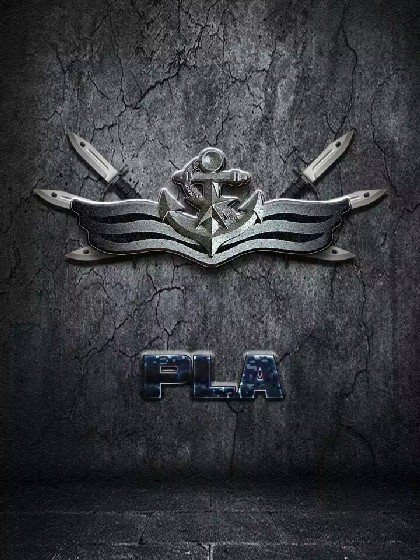第六十九章别有隐情
赵鼎才猛然醒悟过来,自己只顾高谈阔论,直抒胸臆,竟然忘记了皇上就在眼前,慌忙躬身施礼,说道:“回王先生,江南人多田少,田价比北方诸省要高,丰年六十石稻谷一亩,平年五十石一亩,歉年四十石一亩。微臣以为,今年遭了灾,也不宜低于四十石一亩。”
“那么,松江的大户愿意出多少石一亩?”
赵鼎苦笑道:“如今市面上,最多十石一亩,许多大户只肯出到八石。”
朱厚熜颇为惊诧地问道:“怎么会这么低?”
“水患一起,松江府几十万百姓遭灾,近十万百姓绝收,生计无着,不得不靠卖田度过荒年,卖田的人多了,田价自然也就跌了下来,此其一;其二,今夏收成锐减,导致粮价飞腾;还有其三……”
赵鼎又明显地犹豫了一下,这才继续说道:“粮商趁机囤积居奇,不肯借贷粮食给灾民,买田的大户又趁机压低田价,想十石八石一亩贱买灾民的田地。”
朱厚熜点点头:“前两条原因都是水灾之后的应有之事,倒也附和经济规律,关键还是第三条。你既然看到了有大户趁机压低田价的可能,有什么应变之策吗?”
“微臣以为,官府应该限定田价不得低于四十石一亩。这样一来,那些大户就不能把受灾百姓的田地都买了去。譬如一家有三兄弟,有一个人卖了田,就可以把卖田的谷子借给另外两个兄弟度过荒年,到了明年,还有三分之二的百姓有田可耕,松江就不会乱。松江不乱,应天半壁就能安如磐石,国朝三分之一的赋税收入也就有了保证。”
朱厚熜十分赞赏赵鼎这种为民请命且胸怀全局的风范,表面上却仍不置可否,问道:“你的这个意见,可曾向省里提出?”
“回王先生,一接到省里的议案,微臣就向省里直陈了陋见。数日之前,刘中丞亲临松江,微臣又当面向他禀明了松江府的实情,再次提出了限定田价的建议,只是……”赵鼎欲言又止。
“不用说,省里想必是没有采纳你的意见了。”朱厚熜冷笑一声:“是否就因为你拒不执行省里的议案,还给朝廷上疏请求先治河再议其他,他们就断了你们松江府的赈灾粮?”
几位在座的天子近臣都看得很清楚,皇上的语气虽然平淡,但按在自己膝盖上的那只手一直在微微颤抖,暴露出内心里已是何等的愤怒,只要赵鼎的说辞对应天巡抚刘清渠不利,皇上可能当即就会将刘清渠革职查办,或许还会严词申斥坐镇江南,居中统筹调度赈灾诸事的夏阁老。现在就看赵鼎怎么说了……
赵鼎苦笑道:“刘中丞言说时下已近七月,倘若再不赶插桑苗木棉,今年改稻为桑就难以见到成效,时下最紧要的赶紧让那些有粮的大户拿出粮食来买灾民的田。若将田价限定过高,不但有违朝廷律令,也会使许多大户望而却步,而赈灾安民之重担亦会全压在地方官府身上,朝廷赈灾开支要增加许多……”
朱厚熜此刻已经全然明白了:原本朝廷定下分三年去改的方略,眼下恰好发生了水患,坐镇江南的夏言和应天巡抚刘清渠两人就想着既然百姓的田已经被淹了,今秋的收成已经没有指望,朝廷也酌情减免了应天府的赋税,不如趁这个机会,赶紧让那些大户买田,赶紧把桑棉种下去,就能完成改稻为桑的国策,给朝廷交差。只要能顺利推行国策,至于那些大户愿意出多少价钱来买田,灾民卖了田后有没有生路,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了。这么做,跟三年前江南各省推行改稻为桑时,有的地方官府毁渠断水、马踏青苗乃至锁拿枷号不愿改种桑棉的百姓有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只是当年是人祸,如今恰好有场天灾而已。那一次的改稻为桑就因为虐民而虎头蛇尾,难道说,这一次,又会重蹈覆辙吗?
再往深处想,他们这么做,不但有捞取政绩、挟私报怨的用心,甚至还有勾结豪富大户、不法商人,借着朝廷推行改稻为桑国策之机大发民难财之心。若是这样,那可就不能放过了。不过,自己如今龙潜大海,惩贪肃奸一事就得等到驾幸南京之后再说……
朱厚熜沉默了一会儿,叹道:“你可真是会做媳妇两头瞒啊!也罢,子不言父之过,夏阁老和刘中丞都跟你有师生之谊,师可以不为师,徒则不可以不为徒,看你这么为难,这件事情等以后再说。我既然来了,赈灾粮一粒也不会少了松江。不过,他们说的只靠朝廷借贷粮食来安抚灾民负担过重这一点,倒也不完全是没有道理。你准备怎么办?”
赵鼎说:“回王先生的话,没有省里的支持,倘若真出现了微臣所担心的大户趁机压低田价之情事,松江知府衙门既不能抄那些大户的家,把粮食分给百姓;更不能劝说灾民忍痛把田贱卖出去,忍受大户的盘剥。可谓两边坐蜡,非但不能上解国难,下纾民困,甚或会有灾民群起闹事,以致酿成大祸,局势便无法收拾。是以,微臣只好一边从自己家里凑出若干钱粮赈济灾民,只要能保证赈粮不断,灾民有饭吃,就不会激起民变;一边压着那些粮商贷粮给官府,官府手中有粮食可以借贷给百姓度过荒年,那些等着买田的大户就无法卡着灾民的脖子贱买田地,微臣便可以与他们争田价,一是田价不能太低,太低了会招致灾民不满,或许会激起民变;二是不能让他们把灾民的田地都买了去,没有受灾的县份也可以去买。灾民甫经大灾,无不惶惶难安。种什么最好听凭自愿,且不可强令干涉。”
张居正插话进来,问道:“倘若那些大户不肯出高价买田呢?”
“稻田改种桑棉,每亩收益要比原来高出三成到五成,更有皇上爱民如子,早在推行国策之初就责令内阁拟定了仍按稻田起课征税等诸多良法善政,四十石一亩,他们已经大占便宜了。放在往常年份,每亩田价要高出十石二十石,他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张居正拱手一揖:“请赵大人恕晚生冒昧直言,设若那些豪富之家都有赵大人这般爱民之心,兴许田价就不会低至十石八石一亩。如今已近七月份,若不赶紧赶种桑棉,过了七月,桑棉插不下去,即便插下去,当年也见不到收益,那些大户人家便不会愿意拿出粮食来买田,岂不正应了应天巡抚衙门的担忧,将赈灾及日后安民的重任都落到了朝廷的头上?”
张居正在皇上身边待久了,也跟高拱一样,有什么就说什么,无论对错,皇上都不会跟他计较。不过,他这么说,也有帮着高拱替夏言分辩的用意--皇上已经摆明接受了赵鼎的说法,也就是说把罪过归结到应天巡抚衙门的头上,坐镇南都统筹调度赈灾诸事的内阁资政夏言就难辞其咎。高拱与夏言有师生之谊,说的太多,无私也有私;他却没有这层顾虑,即便不公也为公。从这一点来说,出仕不到五年的张居正,就要比已经出仕近十年的高拱更精明了,这既和各人禀性有关,也因为高拱的恩师夏言是一心谋国,不善谋身的夏言;而张居正却是徐阶的入室弟子,耳濡目染,不免学到了恩师的机心和权谋。
但是,这话听在赵鼎耳中就不免有些刺耳,甚至觉得他暗含嘲讽之意,在指责自己书生之见。若是同年高拱这么说,赵鼎勉强还能接受,张居正区区一个后生小辈,未经科举,进翰林院当庶吉士、后来调至御前行走,都是皇上破例开恩,他又有附逆之情事,难免让赵鼎这样的清正君子有些不齿;再者,赵鼎处境如此艰难,有一大半是拜这个张居正的恩师徐阶所赐,之所以至今尚未将自己的难处尽情倾吐,不过是当着皇上的面,给他这个少年新贵留一点颜面而已,未必就是怕了徐阶那个内阁辅臣的威势。
因此,赵鼎冷笑一声:“张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些大户不趁灾民遭受水患、生计困顿之际买田,莫非还要等到灾民度过荒年之后才动手吗?错过了这场天灾,等到明年,灾民看到改稻为桑的好处,自家就改了,何必要把田卖给他们去改?况且,在下已经给俆阁老去信,只要他在百忙之中回书松江,限价买田的事情大约就能成功了。”
张居正一愣:这关自己恩师什么事?恩师原本就是松江人氏,家中虽薄有良田,却算不上什么豪富之家,如何能左右田价?难道说……
他不敢再往下想了,深深地懊悔自己引火烧身,只顾着帮高拱替夏言说话,却惹恼了眼前这位连龙鳞都敢批的状元知府赵鼎,引出了一直隐而不说的实情,若是因此激怒了在座的皇上,祸延恩师,那可真是因小失大啊……
果然,一听到赵鼎提到了徐阶,朱厚熜立刻警觉了起来:“限价买田,为何要徐阁老发话?莫非暗中操纵田价的大户,就是他的家人?”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大明帝国
- 简介:当年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本书数字版权由“当当”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04.0万字6年前
- 重生之大明国公
- 简介:一次意外,让张凡这个经济专业的高才生穿越到大明朝。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人生。他到底会如何度过!已经设定好的人生道路带他走进了大明政权的权力中心,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又会给这个时代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且看张凡这样一个穿越人士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大明朝的巅峰!【纯属虚构,请勿模仿】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677.6万字6年前
- 萝莉炮娘变变变!
- 简介: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 3.4万字6年前
- 铁流——2030回忆录
- 简介:一部描写未来史的战争回忆录
- 6.7万字5年前
- 巨匪
- 简介:新书重回三国,更精彩内容,即将登陆,希望继续关注四关的新书《三国之刺客帝国》!!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18.4万字5年前
- 穿越之争霸在三国
- 简介:特种兵王孙战完成任务回国途中,被系统砸中,将他带到了一个和历史三国极其相似的世界里。这里不但有文臣猛将,还有武侠高手和宗门!孙战他想要争霸天下很有压力!不过他更有动力,因为他有系统的帮助,还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兄弟们的帮助,还有那红颜知己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统一三国不是他的终极目标!。
- 118.8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