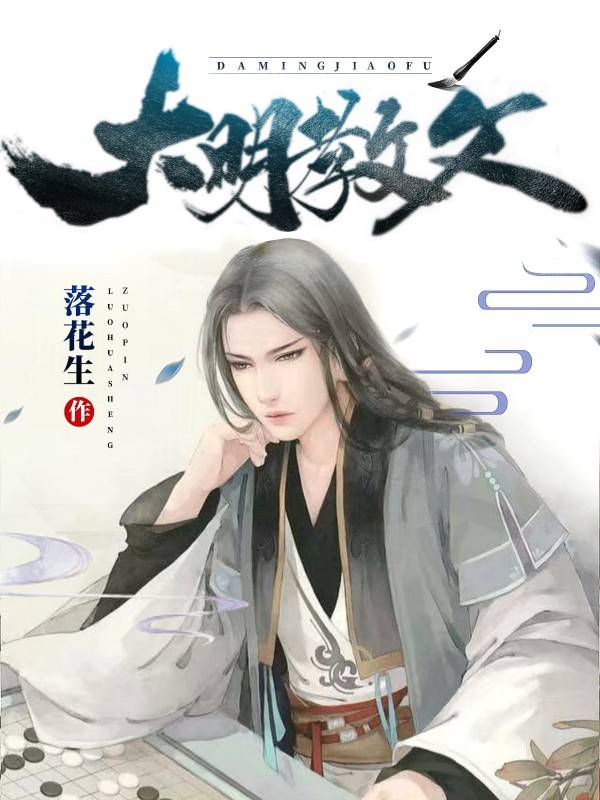第九十一章阉奴忠心
杨金水和冯保在沈一石的家中用过了酒饭,起轿到了苏州知府衙门,商议招募织工的事情。新任苏州知府齐汉生对他们十分客气,答应全力配合,两人很快就说妥了差使。
回到苏州织造局官署,杨金水反客为主,嚷嚷着吩咐道:“快打盆水来。这大的日头东跑西颠的,一身都臭了。”一边说着,一边就脱掉了官帽和宫袍。
三大织造局如今都把衙门设了起来,底下没有办事儿的人可不行,又是宫里的衙门,办的皇差可能牵扯到宫里的机密,等闲的人也不能进来,吕芳就奏请皇上,陆续从宫里派了不少黄门内侍过来当差。杨金水一声令下,那些当值的内侍们赶紧打水的打水,拿面巾的拿面巾。冯保待他们替杨金水和自己挂好了宫袍之后,就用眼神示意他们出去,自己把面巾在盆里绞了递给杨金水,嘴里说道:“师兄,有句话,也不知当问不当问?”
杨金水知道冯保有事情要和自己商量,所以才屏退了左右,自己来做这些伺候人的差使,也就毫不客气地接过面巾,一边在脸上擦着,一边说:“你我兄弟之间,有什么不好说的。”
“那师弟就直说了。”冯保说:“沈一石把作坊并到织造局名下,师兄可是请得了干爹的示?”
杨金水说:“瞒天瞒地,咱家也不能瞒皇上,更不能瞒干爹,一早就报上去了。不过,干爹如今正伺候着主子万岁爷龙驾在运河里,一时半刻且回不了话。”
这也正是冯保担心的地方,听杨金水直认之后,他小心翼翼地说:“请师兄恕罪,是不是等干爹回话之后再跟那个沈一石签订约书?”
杨金水的手停了下来,深深地看着冯保,说:“为什么?”
“师兄在司礼监当差,比我知道的清楚,有些话原不是我当说、敢说的。但师兄如此宽厚待我,我若是还藏着掖着,那就太不够意思了……”冯保先拿话把自己心意表白之后,才接着说道:“挂在咱宫里当差的那个贺兰石,每年给朝廷赚到上百万两银子,暗中贴补宫里也有好几十万,又走通了严阁老、小阁老的路子,干爹平日也要卖几分面子给他。可是,他想参股官当的事情被他那个同乡马阁老一搅和,还是个镜花水月一场空。沈一石把作坊挂在织造局名下这么大的事情,可不是咱们能做得了主的,大概干爹也不敢擅自做主,得由主子万岁爷圣裁。咱们若是抢先就做了,若是外面那些臣子闹腾起来,就让主子万岁爷为难,更让干爹下不来台了……”
杨金水把面巾扔在了盆里,说:“到底是乾清宫出来的,见识就是要比杭州的老王高出一筹。哼!照他的那种搞法,主子万岁爷确实要为难,干爹也确实会下不来台,还好咱家还不糊涂,没让他小子的几句好话给套住了。”
冯保从杨金水的话里听不出是在揶揄甚至讥讽自己,但他不知道杭州织造局的王欣王公公是怎么给杨金水说的,也不好接腔,就把面巾又在盆里绞了,说:“师兄不妨把内衫也脱了,我帮你擦一擦。”
杨金水却不领情,冷哼一声:“咱家说了,这可不是你这个位分上的人该做的事情!”
冯保脸面上有些挂不住了:“那我就又要驳师兄一句了,做了咱们这号人,伺候人就是咱们的本分,有什么该做不该做的?”
“那好!”杨金水回过头来,说:“你把内衫脱了,我来帮你擦!”
冯保一愣,结结巴巴地说:“这……这可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杨金水提高了声调:“少说废话!脱了!”
冯保见他似乎动了怒,带出了司礼监秉笔公公的威势,心里不免有些惧怕;再者,虽说去了势,也都是男人,又都在宫里当差多年,伺候主子万岁爷和位分高的太监擦身、让那些黄门内侍给自己擦身,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做了多少回,他也不敢再推辞,赶紧解开了内衫,转过身去,把光溜溜的脊背对着杨金水。杨金水当真从盆里拿起了面巾,替他擦起了后背。
司礼监秉笔太监给人擦背,大概也只有主子万岁爷才配享用,冯保嗫嚅着说:“这可当真折了我的寿了……”
杨金水一哂:“什么折寿不折寿的,还是你方才那句话说的好,做了咱们这号人,伺候人就是咱们的本分,有什么该做不该做的?”
冯保到底还是不敢坏了宫里的规矩,任他擦了两下,就忙说:“师兄,还是……还是我自己来吧……”
杨金水也只是做戏而已,就把面巾递给了冯保,示意他用另一盆水擦脸净面,自己敞开了内衫,一边擦起了脖子和前胸,一边说:“蒙你叫咱家一声师兄,咱家也不瞒你,这件事,咱家也是想了又想,好几宿都没能合眼,最后把心一横,才到了你这苏州,带着你去见那个沈一石。至于你说的那个顾虑,咱家也翻来覆去地想了。就是咱家今儿上午给沈一石说的那句话,这次朝廷复设苏松杭三大织造局,是干爹的奏议。主子万岁爷也是看在干爹的面子上,才把这一摊子事情交给了咱们几位师兄弟,咱们就不能不给主子万岁爷和干爹长脸,更不能让主子万岁爷和干爹在外面的臣子面前下不来台。咱家想过了,今年就是死,也要给主子万岁爷和吕公公死出五万匹棉布、三万匹丝绸来!”
冯保被杨金水说出的数字给吓住了,怔怔地看着他,不敢接腔。
来江南的路上,他们几个钦办织造使和织造局监正就反复商议过了,以朝廷给的一百万两开办费,三大织造局每家最多能建成五家作坊,彻夜赶工也只能织三个多月,如何能织出五万匹棉布、三万匹丝绸?这个杨公公,八成是骤然升任江南织造使这么重要的位置,求功之心过于操切了,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啊!
杨金水一哂:“看看你,还是乾清宫里出来的人,胆子怎么就那么小,听到这个数字就怕成了这样?咱家不是已经让那个沈一石今年就贡缴三万匹棉布、两万匹丝绸了吗?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接着,他正色说到:“咱家这么做,可不是在逼你们哥仨,丝绸棉布都是织出来的,不是逼出来的,把你们逼得投河上吊,该织不出来还是织不出来,故此才想出了这个法子。”
说话间,杨金水已擦完了前胸,踱回到座位上一边喝茶,一边说:“且不说明年便是主子即位三十年的大典,主子万岁爷少不得要拿出大量的丝绸棉布赏赐文武百官、外藩使臣;去年主子万岁爷巡幸草原,招抚北虏各部,你是有幸跟着去了的,亲眼目睹,对那边的情势应该比我还清楚。说句犯了天条的话,那些夷狄之众归顺天朝,可不单单是慑服于主子万岁爷的天威,他们身处荒漠,要的就是我天朝的丝绸棉布,若是不给,主子万岁爷的天威大概也慑服不了他们。今年不给,今年就会起战事;年年不给,战事就永无宁日。这小小的丝绸棉布,上面系的可是朝廷的军国大事、主子万岁爷的江山社稷啊!咱家估摸着,主子万岁爷在江南推行改稻为桑,倒有一大半的原因是为的这个。这个担子,咱家和各位师弟得替主子万岁爷和干爹担起来!有了这五万匹棉布、三万匹丝绸,咱家倒要看看,外面的那些臣子谁敢再说咱们内廷织造局的闲话!”
冯保也肃整了面容,说:“师兄如此推心置腹,我有些话也就敢说了。师兄对主子万岁爷的忠,对干爹的孝,我冯保能领会得。但万死不当说上一句,越是军国大事,咱们这号人越不能沾手,祖宗的家法、朝廷的规制,还有外面的那些朝野清流,可都容不得咱们这号人插手军国大事……”
说到后来,他不禁黯然了,声音也低沉了下来。
杨金水点点头:“说的不错,这些话,咱家也只会跟你冯师弟说一说。但主子万岁爷和干爹待咱家有十辈子也还不了的恩德,对咱家来说,尽心办好主子万岁爷和干爹吩咐下来的差使,这便是最大的忠!到江南这一两个月,咱家算是看明白了,甭管外面的那些臣子嘴上说的有多好听,全他妈的是官场上的**,改稻为桑这么大的事情,他们都敢个个卯足了劲要从中捞好处,也只有咱们这些人拼了命地给主子万岁爷织丝绸棉布。谁有功,谁有过,主子万岁爷的心比日月还明,到时候自然会明白谁才是我大明朝最大的忠臣!”
冯保沉默了一会儿,长叹道:“师兄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师兄在前面走,我在后面尽力跟吧……”
“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为了主子万岁爷和干爹,咱们哥几个也要把这件差事办下来。”
说着,杨金水突然笑了:“若是咱家没有猜错的话,今儿晚上,沈老板便会把那个芸娘给你悄悄地送来,可不能少了咱家这个大媒一杯喜酒吃。”
“师兄的好意,我心领了。可这事儿……”冯保叹道:“还是算了吧……”
杨金水一哂:“你当咱家与那个沈一石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非要拉你下水?沈一石那种商人可是精明的很,咱家给他许了那么多的愿,又不打算在里面分银子,他岂能不起疑?你纳了那个芸娘,他就安心了,督造作坊、催织棉布的事情你就可以甩给他,还怕他不能尽心替你当差?说句不怕你着恼的话,这么重的担子,杭州老王和松江小李子那两边都好说,你冯师弟却没有管过织造的事,咱家这个做师兄的不能不帮你多考虑一点……”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抗日之横扫天下
- 简介:率特战旅穿越到了三十年代,郑啸开始了抗日征程。上千精锐特战队员,用之不尽的精良装备,强大无比的后勤保障,雨后般春笋冒头的奇人异士……,咱就是要当乱世霸王,看谁不爽揍谁!强大的军力横扫华北,席卷全国,一路打的小鬼子哭爹叫娘、望风而逃,晚上睡觉都噩梦不断……***************************************本故事纯属虚构,只供娱乐,请勿模仿;发生地点为平行空间,如与历史偶似,乃是巧合!!!★★★红色尖兵总部群:32451897YY频道:95350863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62.3万字6年前
- 歪门斜道
- 简介:一个从歪门斜道里半毕业状态走出来的不靠谱青年,身高不乍地,长相如同大脑缺根弦,其实确是狡猾无比,心细如发,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玩得得心应手,泡妞更是霸道无比,那个不服就先霸王硬上弓,整到你服为止,演绎出一段母女通吃的神话,自己长相太差不用卑鄙手段讨老婆怎么把美女拿下?这个不靠谱的丑青年不算坏,也够得上优秀青年得评审标准,他心中充满热血,与大明第一贱人称兄道弟,一起荼毒祸害别人。经常性敲诈勒索坑敌人,把大明武林惹得怨声载道,将东林党坑得几乎上吊,把努尔哈赤、皇太极整得哭爹喊娘,以贱立足河套,把邻国打得落花流水,把陈圆圆掳到帐下,坑得李自成鸡飞狗跳,弄得吴大山龟呜呼哀哉不得不投靠大清。敢泡老子的女人?你信不信老子把你得把子割掉?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68.2万字6年前
- 萝莉炮娘变变变
- 简介: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 4.5万字5年前
- 抗日传奇之北战神
- 简介: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因一次护卫“闽人三十六姓”逝者东望琉球故土的东明岛之行,退役特种兵李元浩穿越到被慈禧太后称赞为“琉球忠臣”的林世功之孙林俊雄身上。对党的忠心永不动摇,对国的热爱永不改变,且看他在琉球群岛成长,遵从党中央的安排在淞沪战场和武汉会战中扬鞭,在东北大战关东军成就“北战神”,在日本本岛成为先驱,谱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传奇之歌。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28.9万字5年前
- 大明教父
- 理学工学双料博士陈恪穿越到明朝崇祯年间,成为一名寒门士子。由贩私盐白手起家,纵横在黑白两道,一步一步成为大明的教父。
- 1.9万字4年前
- 天下第一是赘婿
- 江南绿林的第一高手因为一纸婚约成为了金陵富商王家的上门女婿。不过相对于江湖上的刀光剑影和尔虞我诈,上门女婿的日子倒是平静安宁不少。或许就此彻底退出江湖,平平静静过日子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不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想退出江湖,江湖不允许,实力更不允许啊。
- 2.1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