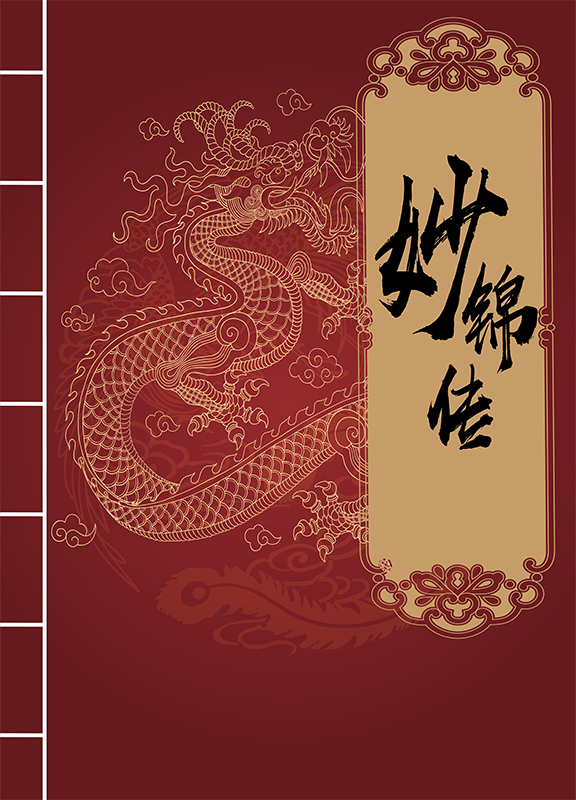第三章性情不改
那位中书舍人压低了声音,对刘清渠说:“好叫大人知道,夏阁老正在发脾气,训斥姓雷的那个阉奴呢!”
夏言为人一向刚介强横,又兼当国柄政多年,不免飞扬跋扈,加之出于士大夫的固有观念,最瞧不起那些宦官阉奴,将他们视为奴才,向来不屑一顾。不过,雷鸣身为南京镇守太监,也算是一个位高权重的貂铛贵宦,更负有秘密监视江南外臣的重任,夏言对他吆五喝六,实在有些不太寻常。刘清渠更加来了兴趣,追问道:“为的何事?”
那位中书舍人把嘴一撇:“还不是为了迎驾整修殿宇的事儿!前日夏阁老言说要把要紧的几处殿宇好好整修一番,王给谏就拟了个方案。夏阁老看了,却说太过奢靡,召来一问,原来是承办此事的雷公公的意思。王给谏还说已经照着方案开始动工了,夏阁老就越发来了气,好生把王给谏训斥了一番,还把雷公公也叫了来一同领训,还说要向朝廷参奏他们不经请示擅自决断,徒靡国帑大兴土木等诸项罪过呢!”
刘清渠心中暗自摇头:左右不过多花一点银子的事儿,夏阁老何必如此锱铢必较,要拿位高权重的南京镇守太监和位虽卑权力却不小的六科言官开刀?
不过,他随即一想便释然了:龙舟船队已经过了扬州,不日即将驾幸南都,又已经,开始动工,再改方案已经来不及,夏阁老也只能默认了这个既成事实,而被下属所挟持是掌权之人最不愿意之事,难怪他会如此生气……
那位中书舍人见刘清渠沉思不语,讨好地说:“这毒的日头,刘大人走这一趟实在辛苦。左右这个时候也不方便进去,就请屈尊到下官值房稍歇片刻,如何?”
这话说到了刘清渠的心坎上,笑道:“扰烦你了。”一边说着,一边就跟着那位中书舍人来到了西边的制敕房。
一来刘清渠毕竟是封疆大吏;二来也跟夏言有私交,那位中书舍人对他十分客气,不但命典吏打来水伺候刘清渠洗脸揩汗,还让典吏弄了个水泡西瓜进来。
内阁之中有口深井,头天把西瓜放进去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捞起来吃,又沙又甜,解暑又解渴,即便是曾任学官多年的当世大儒刘清渠,也忍不住食指大动,吃完一块,又随手拿起了第二块。
不过,就在他刚刚准备要消灭第二块西瓜时,就听到门外响起了一阵由近及远的脚步声,脚步声显得十分沉重,不用说一定是刚刚挨了骂的王瑶和雷鸣两人垂头丧气地走了。
南京各大衙门一直空悬,一应政务等若全压到了应天巡抚署的头上,加之迎驾诸事千头万绪,繁驳杂乱,刘清渠也是忙得连轴转,恨不得一天分成二十四个时辰,听到夏言已经议完了事,立刻将那块西瓜放回桌上,拿出手帕揩去胡须上的西瓜汁,整一整衣冠就出了制敕房。
进了正中的内阁值房,夏言正端坐在硕大的红木案桌前,桌上摆着好几份翻开的公文,显然还有一大堆的公务要办。见到刘清渠进来,因熟不拘礼,夏言也不起身见礼,一边指着文案横头的一张椅子,示意刘清渠坐下,一边问道:“尔公有事要找在下商议?”
刘清渠字尔升,夏言称他一声“尔公”,无疑是十分尊重也极为要好的意思了,刘清渠却恪守礼法,仍依照朝廷礼制,向夏言躬身行了拜见上官的揖礼之后才落座,也不忙着回话,反而问道:“公谨兄方才又冲雷鸣发火了?”
尽管雷鸣已经走了,夏言却还是余怒未消,气冲冲地说:“那个阉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让他整修殿宇,照我的意思,当初益逆人等整修的殿宇大都完好,只捡残损之处修补一番,再把整座宫城粉刷一新也就是了。他竟拿着鸡毛当令箭,工程造价竟高达二十万两银子,也不先送我过目,便已开工营造,如何能不让老夫动怒!”
刘清渠笑道:“要说整修殿宇之事,还是你公谨兄的首议呢!为了迎驾,整修殿宇也在情理之中,惟是你公谨兄首议此事,就让在下殊为不解了。漫说南都诸人,全天下又有谁不知道你公谨兄向来不喜圣驾巡幸之举,十年前还曾因此被斥退致仕,若非皇上离不开你,你大概那个时候便回贵溪老家管领山林去了……”
诚如刘清渠所言,嘉靖十九年,夏言第一次遭皇上的斥退致仕,便是因为嘉靖帝朱厚熜拜谒显陵之后,严嵩奏请皇上再加拜谒,他却奏请皇上启程回京,惹得皇上很不高兴。之后圣驾巡游大峪山,他又因故晚到了一会儿,受到嘉靖帝的斥责并被勒令交出以前所赐的银章、手敕等物,以少保、尚书大学士衔致仕。好在没过几天,嘉靖帝的怒气消了,便自食其言,让他留下仍回内阁视事,是为夏言三落三起的第一落第一起。作为知交好友的刘清渠这么说,当然少半是揶揄,大半是奉承,落脚还是在说皇上离不开夏言。
夏言向来率性自然,虽贵为当朝一品大员,历经数不尽的宦海风波,性情始终不改,加之刘清渠是“自己人”,也没有必要故作谦逊之态,仍气哼哼地说:“我不过是料定圣驾兴许要在南都住上一段时日,故此才想到要为皇上整修殿宇。谁让那个阉奴靡费国帑大兴土木的?不经请示便铺开了二十万两银子这么大的工程,此风断不可长,此例断不可开!”
夏言何以断定圣驾会在南都住上许久,刘清渠至今不得而知,随口附和道:“论说只为迎驾便大兴土木,委实有些说不过去。不过,你公谨兄也不必跟那帮不学无术的阉奴一般见识。这等小人,心眼比针尖大不了多少,最易生恨结怨。尤其是他雷鸣,分明是个低贱的奴婢,偏生好面子的很,至今南京士民还在笑他这个‘北京鲥鱼’!”
原来,当年朝廷平定江南叛乱之后,留下平叛军监军吕芳坐镇南京,雷鸣便跟着到了南京,当上了鲥鱼厂的管事太监,便是如今已经贵为司礼监秉笔、江南织造使杨金水曾担任过的那个职务。
鲥鱼乃是江南一大特产,肉质细嫩,是鱼中极品、天下美味,历来都是宫中指名的贡物。大内就专门在南京设立了鲥鱼厂,专司给宫里上贡鲥鱼。雷鸣出掌这个内廷衙门,近水楼台先得月,手下的人便巴心巴肝地做了一桌精美的鲥鱼宴请他这个新任上司品尝。谁知道他刚品尝第一口,立刻就拉下脸来,呵斥道:“大胆奴才,你们竟敢糊弄本爷!”手下的人被他骂糊涂了,不知他这股子邪火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遂小心翼翼地问道:“雷爷,小的们用心伺候,哪里还敢糊弄你?”雷鸣气呼呼地质问道:“你们以为咱家没吃过鲥鱼?竟敢拿些不相干的野鱼充数,这不是糊弄又是什么?”手下人以为这位新来的管事是鸡蛋里挑石头,没事儿偏要给下面的人找事,便越发小心地应道:“雷爷,这真真实实是鲥鱼。眼下不是春夏之交的鲥鱼时节,小的们为了伺候您老,十几条船在江里捕捞了五天才弄到这么一桌子……”雷鸣把头一摇、嘴一撇:“这不是鲥鱼,咱家在宫里待了二十多年,哪年不吃鲥鱼?这鲥鱼味道臭臭的,你们这一桌鲥鱼,何曾有一丝儿臭味?”手下人一听,顿时明白了,想笑又不敢笑,只得耐心解释道:“雷爷,你现在吃的是新鲜鲥鱼。咱们每年把鲥鱼捕捞起来,再用快船经运河长途送到宫里。几千里的路途,快则二十来天,慢则一个多月。这么长时间,虽说鲥鱼舱里有冰镇着,也难免腐败变味。最好的鲥鱼贡上去由皇上后妃享用,稍稍有点变味的,才赐给王侯大臣和宫里有头有脸的管事牌子们分享。您老年复一年,吃惯了变味儿的鲥鱼,反倒觉得新鲜的不好吃了……”手下人回答得委婉,雷鸣明白了个中原因,却仍不肯服输,饶自嘴硬地说:“不管怎么说,还是臭鲥鱼好吃。从今往后,咱家只吃北京城里的鲥鱼,这南京的鲥鱼,咱家不吃!”这个笑话,一时间传遍南京,说的活灵活现,语气动作都分毫不差,任谁听了都觉得好笑,拿“北京鲥鱼”来指代那些缺识少见的乡巴佬。
吕芳奉调回京之后,雷鸣升任了南京镇守太监。夏言被派驻南京,也听说过这个笑话。由于“北京鲥鱼”着实好笑,几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来夏言仍不禁莞尔,破颜一笑,随即却又叹道:“就是这样粗鄙不文之人,竟做了堂堂留都的镇守太监,岂不令人笑话国朝无人可用!”
刘清渠提起陈年旧事,明是说笑,实则委婉地规劝。不过,他见夏言不改当年位列台阁执掌朝政时指点江山的气势,便知道自己的一番苦心似乎没有收到成效,又进一步劝道:“宫里的事情,咱们这些外官可管不着,更犯不上去管。不过,话说回来,若是那些刑余之人个个都如同‘双口’那般才智过人、机心深重,也断非我辈人臣之福啊……”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纵横隋末的王牌特种兵
- 简介:为救美人独闯禁宫,搁置恩怨从军西征。揽文才,收猛将,逐鹿中原。平漠北,定波斯,扬帆海外。王牌特种兵刘子秋穿越隋末,逆袭乱世,开疆拓土,为您演绎一段不寻常的隋唐故事……群号:115455564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46.8万字5年前
- 赝品太监
- 简介:潘又安被征召入宫,在净身的时候被人做了手脚,得以保住健全的身体。只因这一疏漏,他成了“赝品”太监。也正因为这一疏漏,皇宫里才充满了欢声和笑语:他出现在哪里,那里就有故事,就有戏。诙谐幽默一本书,嬉笑怒骂一场戏。看罢犹当一笑了之,莫查史书究根问底。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84.5万字5年前
- 猎毒人小说
- 简介:高智商、高学历的化学工程师吕云鹏,凭借海关监控和一张快递单,锁定了杀害大哥吕云飞父子的凶手。他且凭借超凡的化学专业知识与过人的智慧胆识,与警方同步接近着真相,甚至破译出大哥遗留密码的真实含义。明山缉毒警察魏海看中吕云鹏的能力,与其联手,顺藤摸瓜,历经九死一生,将贩毒集团一网打尽。在与毒贩周旋斗争的过程中,吕云鹏与哥哥一样,成长为一名甘为战友牺牲、勇为国家奉献的功勋卧底。
- 2.6万字5年前
- 魏郡李
- 初平元年,当时旱蝗,林独丰收,尽呼比邻,升斗分之兴平元年,时大旱,蝗虫起,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建安二年,夏五月,蝗。秋九月,汉水溢。是岁饥,江淮闲民相食。建安八年,时大旱蝗虫起。……初平三年出生的他是济阴豪族李氏嫡子,本该有一个平顺的人生,但,三岁时,父辈死伤殆尽。八岁时,任青州刺史的大兄亡故,他想好好地活下去,只是,满堂幼弟皆孤子,千担重任压肩头,责任让他无可逃避,满腹经纶?不会。勇冠三军?没有的事。算无遗策?不可能的。仁义无双?呵呵。妻妾成群?李某自称三千弱水只取一瓢。那他会什么?会苟,活得久。
- 14.0万字4年前
- 警花与警犬续集
- 暂无介绍哦~
- 0.2万字4年前
- 妙锦传
- 中国明朝,这个国祚近二百七十余年的大一统王朝,在历史上因其辉煌与黑暗并存的特殊性,一直以来为众人所津津乐道。至千禧之年而下的二十余年里,这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朝代总是被掩盖着一层朦胧,有人唾弃其厂卫的阴狠恶毒,亦有人颂扬其威震八方的天朝国威。但无论怎么说,象征这个朝代的符号总是让人屡屡惊叹。《永乐大典》,《本草纲目》,《纪效新书》亦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难以磨灭的光辉星辰。扫荡安南,南驱倭寇,北攘蒙古,壬辰战争,铿锵铁马之声至今仍旧回旋于耳。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七下西洋,宣仁之治,火枪,紫禁城,内阁等等诸如此类,频频成为历史大家们热烈讨论之对象。三次盛世,两次中兴,一次革新。在古典王朝中,这是极其少见的。而明朝自开国以后,平均五十年就出现一次极度繁荣的社会现象,亦不可不为之惊奇。诚然,脱离洪武之治来浅谈永乐盛世无异于空中楼阁。那么,这个开国仅仅以半个甲子的时间,就快速步入巅峰的王朝,它的背后,究竟又隐藏了什么?又是谁铸就了宏伟的永乐盛世?在这盛世中,又隐藏了多少悲欢离合?请让我们慢慢走进明朝,去细细感受它给我们带来的别样美感。
- 12.1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