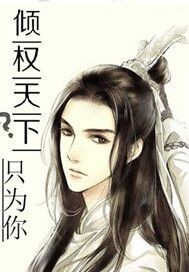第十七章再遇奇事
李贽这么说,就是一竹篙把大明官场所有进士出身的官员打翻在地了,漫说是高拱这个正经的两榜进士,就连虽没有进士科名,却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的张居正也是再度勃然色变,深恨眼前这位狂生李贽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皇上面前如此放肆地说话。若非皇上对李贽十分客气,一口一个“卓吾兄”,对他种种离经叛道的狂悖之言也毫不为忌,他们兴许就忍不住要当街呵斥这位放肆敢言的后生小辈了!
朱厚熜心中更是慨叹不已:这个李贽,真不愧是大明第一“思想犯”,果然是铁了心要把大明官场当成混饭吃的地方啊!便笑着说道:“卓吾兄果然快人快语,非是等闲之辈。只要你不怠废政务,又能清廉自守,纵然把出仕做官当成谋生的手段,也说不到什么错处。惟是‘学问’二字,却是我辈士人一辈子的大事,还望卓吾兄公务闲暇之余,精研学问,穷究义理,为我华夏文明之传承与发扬光大,尽一份心力。”
无论是先前在泉州,还是如今在南京,赏识自己的人不少,也不乏朝廷官员、硕儒名宿。然而,每当自己直抒胸臆之时,却总会遭到他们板着面孔、不留颜面的痛斥,看高大人和张大人的脸色,大概也概莫能外。惟有眼前这位“王先生”,也不知道官居几品、所司何职,却能如此开明通达,不但不责怪自己有那样离经叛道、为世人所不容的想法;反而热情洋溢地支持和鼓励自己,让李贽情不自禁地想向他敞开心扉,对他的话更是无比感动,当即深深一揖:“先生敦敦诲教,学生铭刻在心。”
“呵呵,如此便好。”朱厚熜说:“在下与卓吾兄此前虽未曾谋面,却是一见如故。不若就近找家酒肆,由在下做个东道,我等把酒叙话,再论古今。不知卓吾兄可否赏光?”
在朱厚熜本人而言,或许当年就有些对名人的盲目崇拜,而今穿越回来,自然是不会放过与大明历史上的那些名人交流的机会。只不过是因为不幸穿越成了混蛋嘉靖,以至于至今不敢去见那个以痛骂嘉靖而青史留名的嘉靖而已。
但是,他的提议却让高拱和张居正两人暗自啧啧称奇:这位狂生李贽定然是皇上梦得神授的奇才异士,皇上见到他,什么逛书坊、找书籍的事情都顾不上了,一门心思要延揽他。有这样求贤若渴的君父,大明幸甚,百官万民幸甚啊!
或许是因为朱厚熜有些过于热情,让李贽一时无以适从,正在犹豫不知该不该接受邀约,却见高拱立即把一道凌厉的目光投射过来。既然恩公有命,他也不敢不从,便说:“先生高情厚义,学生却之不恭。惟是学生还有几位同窗一道前来,且请先生容学生去与他们告罪。”
几位同学一道出来逛书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朱厚熜原本也不想在太多的人的面前曝露身份,但今天出来,一大目的便是为了了解江南士林对于朝廷推行改稻为桑之国策,以及在苏州、松江刚刚掀起的抑制豪强兼并等国之大政的反应,又有什么机会能比酒酣耳热之时高谈阔论更好呢?他便热情地说:“既然是卓吾兄的朋友,想必都是学识出众的青年才俊。左右你们选文也买了,不若邀约他们一同前往。饮酒雅谈,当然是人多热闹些个!
“这……”李贽明显地犹豫了一下,为难地说:“不敢欺瞒先生,先生想必跟高大人、张大人一样都有官职在身,与学生那几位同窗在闹市宴饮晤谈,只怕有些不便……”
国朝最重视礼仪教化,士人儒生与官员称兄道弟也是寻常之事。此外,李贽的同窗,想必也是国子监的生员。而国子监是朝廷官员的储备库,为了培养和锻炼那些未来的职官司员,朝廷甚至有意遴选监生随同正式的官员承差办事。比如说,嘉靖二十四年起,朝廷大兴农务,派出诸多宣讲团分付北方诸省府州县,就抽调了大量监生随行。由此才引发了嘉靖二十六年杨继盛呈献《流民图》揭发山东莱州惨祸,引起一场波及朝野的琼林宴乱;进而引发了撤裁东厂、收回司礼监批红大权、抬高内阁职权并设立御前办公厅、夏言三度复出担任新设的内阁资政一职等一系列耸动天下的重大朝政改革。也就是说,监生虽无官身,地位却又高于一般的士人秀才。为何李贽却说他的几位同窗与官员在闹市宴饮晤谈有所不便,就让朱厚熜和高拱、张居正殊为不解了--难道说,那些监生是当年有附逆倡乱情事的江南士人?
不过,若是因为这个缘故,就大可不必了。且不说张居正这位当年列名逆案的罪魁祸首已经跻身朝政中枢,行走御前,成为与高拱一样的天子近臣;同样与他一道列名逆案的何心隐、初幼嘉也膺选中式,成为大明王朝的正式官员。初幼嘉不过是中式三年的进士,如今已经做到礼部僧录从五品司员外郎,升官速度令朝野内外都是瞠目结舌,这些年里他还颇受朝廷信重,作为钦差常驻鞑靼俺答部归化城,料理民族、宗教事务。何心隐一门心思只想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如今虽说还只是个六品官,去年也从国子监司业的任上调到京师大学堂,出任职权与司业一般无二的教务长。以皇上对京师大学堂的重视,也不可谓圣眷不浓。以他三人的“逆名昭著”、“逆迹斑斑”,都丝毫不受任何影响,其他那些附人骥尾的士子儒生,又何必如此惶恐难安?若真是如此,那就需要好好宽慰劝勉他们一番了……
因此,朱厚熜豪爽地一摆手,笑道:“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方便不方便之说。你更不必忌讳,且将他们请来见礼。”
高拱也深知皇上的用意所在,见李贽还在犹豫,忙说:“既然王先生盛情邀约,你就不妨把贵同窗一同请来。”
李贽还在犹豫,高拱把脸沉了下来:“真有什么事情,本官一肩担了。还不快去!”
尽管李贽至今不知道眼前这位“王先生”的身份,但高拱、张居正两位朝廷新贵、天子近臣的名位在那里摆着,又有什么事情担不下来?便深作一揖:“请王先生和两位大人稍候,同窗就在那边路旁等我,学生这就去请他们过来拜见几位大人。”
朱厚熜和高拱、张居正十分好奇究竟李贽的同窗是何方神圣,让他那样的狂生也避讳莫深,便朝着他走的方向看去,却没有看见有什么青年儒生在街边驻足等候,只有三位年不过十岁的孩童朝着这边,或许是书香人家的小孩,也穿着一身儒服,还焉有其事地戴着被俗称为“太平巾”的四方巾。
令他们大为惊诧的是,李贽正是走到了那三位孩童的身边,与他们说了两句什么。那三位孩童竟跟着李贽朝着他们这边走来。
国子监所收监生,不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便是如李贽这般有门路,能求得如高拱这样的达官显贵一封荐书之人。那些求人举荐入学之人,虽说也没有功名限制,但大抵还是至少应该进了学,有个秀才的身份--若是连秀才的功名都没有,旁人怎好帮他们撞木钟,把个白丁硬塞进堂堂的太学府?而这三位孩童既然身份有碍朝廷忌讳,想必不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但他们的年纪甚幼,难道竟都已经有了秀才的功名?
明朝科举制度,各州县设府学县学,根据人口多寡分配生员名额,大府一般三五十人,小县不过一二十人,府学县学生员才算是有了秀才功名。但是,要取得这种资格,必须在学道主持的童子试中获得取录才行,还要经常到学校接受上至省里的提学御史,下到本县的县学教喻的月稽岁考,岁考在五、六等者就要被褫夺功名。真可谓是关卡重重,得来不易,有些士子儒生考了一辈子,直考到须发皆白也未必能取得秀才的功名。由于不论年龄,应童子试的都称童,故此大明两京一十三省,拄着拐杖应童子试之人比比皆是,诚为科场一大趣事。
与之相对应的,还有那些垂髫少年便进学中了秀才的,如张居正便是十二岁就中了秀才。惟其难得,便被传为一时佳话。但看这三位少年的年岁,大概比当年的张居正还要小个几岁,就更为难得了。
此外,方才那三位孩童静静地站在那里,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此刻动步一走,朱厚熜和张居正君臣二人同时发现,他们竟都是清一色的罗圈腿,就象是去年他们在草原上看到的那些蒙古小孩一样!
莫非,他们都是从蒙古那边过来的?
若是如此,倒也能解释的通他们为何那样年幼便能入国子监--去年朱厚熜巡幸草原参加那达慕大会,许下的一大厚礼便是恩准蒙古子弟入大明各级学府就学。为了表示归顺向化之心,蒙古各部都选送了一部分人前来大明求学,其中就不乏年岁尚幼的孩童。
不过,那些蒙古子弟主要集中于大同、宣府等边地,很少有前往京师求学的,更不用说是到这远隔千山万水之外的南京来。且不说饮食能否适应,单是气候、饮食与习俗,便足以令无数蒙古子弟望而却步。这三位孩童竟有如此决心和毅力,那便不能小觑了……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烽火男儿行
- 简介: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抗战尸横遍野血流成河,30万冤魂让整个南京城披上血色,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也是英魂遍地尸骨累累。年轻的懵懂学生唐城和国军连长的一次偶遇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为了心中的信义,唐城踏上了漫漫征程,从一个战场新兵逐渐成为一个被老兵们称呼为长命鬼的百战老兵。杀勇似猛虎胆似铁战不破敌阵誓不还谨以此书缅怀献身家国的英灵们英魂永在国魂长存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289.5万字5年前
- 倾权天下只为你
- 简介:犹记那年桃花盛开,她就像一谪仙的桃花仙一般,小小的身子躺在他的怀里,眸光似水,糯糯的说:“瑾哥哥,等你娶我的那天,我一定要告诉所有人,我要嫁给你了。”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稀还在耳边回荡。桃花已花开至花落,天际已云卷至云舒,那年许下的诺言就像逝去的旧时光,一去不复返。凉辰月:我没有什么青春,没有什么回忆,但光是一个你,就让我心酸不已。完颜瑾:世人皆说我甚爱桃花,却不知我爱的,从来都只是桃花树下的小小人儿。----初次写文,多加包含!期待你们的评论和意见。作者在拼命码字中.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06.4万字6年前
- 何为兵王?
- 简介:简介正在更新
- 42.7万字5年前
- 逆袭民国的特工
- 简介:他,是组织的弃子。他,是上海滩崛起的新一代大亨。他,是埋藏在对手心中的一根毒刺。他,是游走于时代舞台的完美舞者。他,是黑暗世界生死较量中的最后赢家。他原本平凡、懦弱,因为遇到一个穿越回南京最黑暗时刻的特工幽灵,开始变得强悍、嗜血。不知不觉间,他走上了一条与原先生命轨迹截然不同的道路,历史因为他的改变而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偏差。或许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他心底的热血与柔情。且看民国一屌丝,在这段变幻莫测的风云岁月中,如何逆袭为王!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54.0万字5年前
- 抗战之从零开始
- 简介:第一次写,希望大家能看进去,不断变化的系统,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抗战,除恶霸斗地主诛鬼子,另类的拯救,不一样的故事,第一次写书,相信自己会越写越好的,希望大家能看的进去
- 9.2万字5年前
- 霸世天唐
- 简介:天宝初年一个大唐盛世,万邦来朝这是一个风华雪月和霸世无双的年代,然盛世的背后切暗流涌动,一个后世探险青年阴差阳错的来到大唐盛世,他的命运和大唐的命运如何,,
- 8.4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