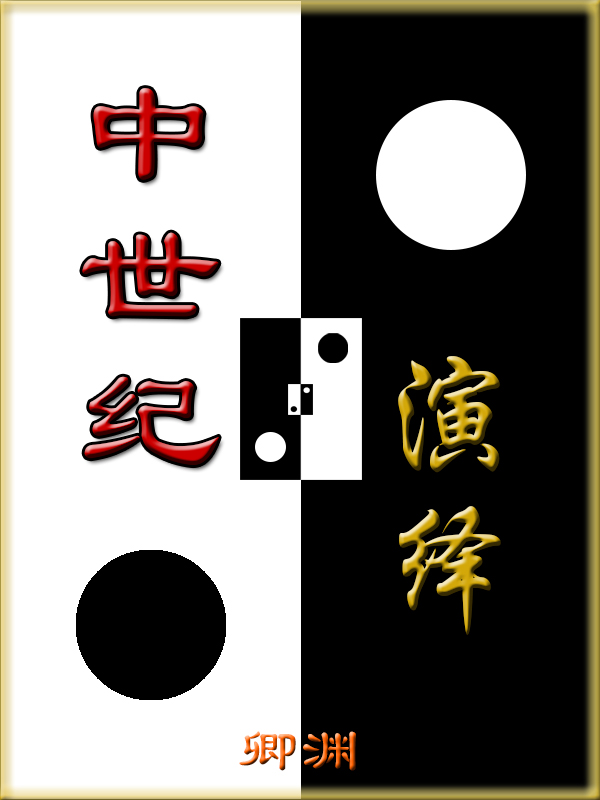第一百三十二章迫不及待
见父亲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严世蕃越发急了,口不择言地说:“爹爹或许以为儿子危言耸听吧?儿子斗胆请爹爹仔细想想:远征大军尚未抵达南洋,只是南路巡防分舰队,再加上徐海匪帮几条破船,便能取得歼敌数千、沉船数十的大胜。罗龙文的信中也说佛朗机人貌似凶顽嚣张,实则不堪一击。设若高拱戚继光率东海舰队全军杀到,佛朗机人便更没有了取胜之机。到时候,夷狄铩羽而归,远征军献俘阙下,我大明国威军威大震,皇上势必龙颜大悦,又要遍赏群臣。夏言和李春芳两人一南一北,受命统管南洋军务,无疑要分得头一份功劳。李春芳那个附人骥尾的家伙且不去说他,夏言那个老不死的东西内拥统筹调度之功,外有大帮门生故吏吹喇叭抬轿子,统军讨夷的督帅还是他的门生,这样的功劳,在满朝文武之中便无人可比。即便不能封侯,只怕再度回任内阁首揆都不足以彰显皇上赏罚之明,象张茂那个老匹夫一样晋位太师、特加上柱国,成为国朝定鼎两百年来文官之中的第一人。试问到了那时,爹爹又何以与之抗衡?设若任其重回朝堂、执掌权枢,我们严家又何来立锥之地?爹爹和儿子欲全身而退、做一富家翁也难……”
接着,他又气呼呼地说:“儿子知道,这些年里,夏言那个老不死的东西倒也识相,从不在朝政上掣爹的肘,行止也从不僭越。爹又念及昔日旧情,便想和他和衷共济、同佐明君。可是,爹怎么也不想想,坐过了内阁首辅那把椅子,尝过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领袖群臣指点江山的甜头,他岂能再容旁人骑到自己的头上?儿子敢断言,自从嘉靖二十三年被斥退回府的那一天起,那个老不死的东西就一直贼心不死、蠢蠢欲动,谋夺首辅之位的野心未尝有一日稍熄!往昔皇上出巡,向来只让内阁首辅领袖群臣、打理朝政;唯独这一次避居深宫、清修悔过,却是明宣上谕,让那个老不死的东西和爹爹共同柄国执政。皇上再度起用他的心思已是昭然若揭。爹爹若是一退再退,只恐祸在不测!”
严嵩终于开口了,笑道:“你说夏贵溪贼心不死、蠢蠢欲动,为父看来,倒是你心火太旺、迫不及待啊!”
话说到这个份上,严世蕃也就没有了任何顾虑,说道:“儿子是想能多为皇上尽忠、为爹爹分忧。可儿子这么做,也不惟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严家、为了爹爹。这些年里,爹爹虽贵为内阁首辅,可论及处境、权柄,甚至还不如当年翟銮那个老滑头当首辅的那段时日。旁的不说,前年吏部尚书李维帧老病致仕,爹爹欲举荐欧阳世伯进吏部尚书。按说欧阳世伯当吏部左堂也有五年了,升任尚书也在情理之中。皇上为何偏偏就是不同意?非得从南京把王恩茂调回北京就任天官?为了这件事,非但欧阳世伯气得大病了一场,官场之上风言风语也有不少。缘何如此,还不是因为有夏言那个老不死的东西退而不休,皇上便不能象当年那样专一倚重爹爹……”
严世蕃举出的这件事情,算是说到了严嵩的痛处--这些年里,自己日夜操劳国政,未尝有一日懈怠,也得到了皇上的信任和倚重,时常蒙赐御膳酒肴、金银锦帛。可是,他总觉得,在信任和倚重之外,皇上对自己还多了一层提防,时不时还要对自己加以限制,象是故意抑制自己在朝臣之中的威信。当年举荐自己的姻亲欧阳必进升任吏部尚书,皇上断然拒绝,就印证了这种感觉……
不过,这种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儿子公然说了出来,让严嵩既觉得难堪,又觉得儿子实在缺乏宰辅之器的城府,便把脸沉了下来,冷哼一声,说道:“内阁首辅上承圣意、下领百官,佐君治政、燮理阴阳,职责何其之重!吏部掌铨政(指铨选任命官员),是为六部之首,外廷百官以宰冢(吏部尚书的别称)为尊。设若我为首揆,姻亲为宰冢,既不合朝廷法度,更必招致朝野非议、世人侧目。为父举荐你欧阳世伯升迁尚书,不过是他逼得紧,胡乱上一道疏虚应人情而已。皇上正是体恤为父的难处,故此才调了王恩茂回京,这是圣主明君体恤臣下的巍巍圣德,哪里就扯得上什么处境不处境的话?你欧阳世伯生病也是他器小量浅之过,更与为父毫不相干!再者说来,如今皇上亲掌国政、宵衣旰食,此乃我大明江山社稷之幸、百官万民之福。我辈人臣生逢盛世、得遇明君,惟有谨遵圣谕、恪守本分,岂敢妄生窃弄权柄、夺皇上之威福而自用之心?”
听到父亲如此严词厉色地申斥,严世蕃如泄气的皮球一样,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这个时候,严嵩又说道:“你方才说的那些话,虽不无诛心之论,却也并非全然毫无道理。夏贵溪和他那位得意门生高肃卿如今都肩负有皇上的社稷之托,亦是朝野内外人尽皆知之事。为父且要问你,既然你深知夏贵溪仍深得圣心,那位高肃卿就更不必说了,为何还以为仅凭罗龙文信中所说的这件事就能扳倒他二人?”
原来,自己的话父亲都听进去了!严世蕃诧异地睁大了眼睛看着父亲,心中不禁感慨道:父亲到底是父亲,怎会不明白儿子的一片苦心?至于为何迟迟不肯表态,不过是要自己把话再说得明白些,既是为了考验、雕琢自己,更显出了无与伦比的宰辅气度。只凭这一点,那位生性刚愎自用、素来桀骜跋扈的夏言,就远远不及父亲高明……
儿子迟迟不答话,严嵩也不着急,端起了面前的酒盅,一边轻呷,一边拈起一片笋,有滋有味地咀嚼了起来。
严世蕃回过神来,这么大的事情,他早就在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又想,立刻答道:“夏言深得圣心,委实不假。但眼下却正是他最倒霉的时候--圣驾驻跸南京才两个多月,他就丢了两个省的巡抚:先是应天府的刘清渠,前些日子又是浙江的张继先。这两个省都是朝廷的钱袋子,如今都落到了我们的手中,他们夏党在朝廷说话的分量可就大不如前了。此消彼长,我们这个时候动手,别说是那些在夏党和我们之间摇摆不定的墙头草,就是他们夏党中人,也应该会有些个识时务者站到我们这边来。”
略微停顿了一下,严世蕃接着说道:“再说徐阶。貌似皇上没有追究他徐阶纵容家人横行乡里、欺官虐民的罪过,还让他主持应天府恩科乡试,可他自己心里也清楚,松江那一页根本就没有翻过去,迟早都是个事儿!这柄高悬头顶的利剑,可是由夏言那个老东西的好学生赵鼎给他挂在头上的,他心里还不得把夏言那个老东西给恨死了?那个老滑头没有反戈一击的胆量,帮我们摇旗呐喊,对夏言那个老东西落井下石,他又何乐而不为?退一万步来说,即便他还要耍滑头,坐山观虎斗,想收渔人之利,也断无以恩报怨,帮着夏言那个老东西说话的道理。只要徐阶那边的人严守中立,朝中其他那些孤魂野鬼也就翻不起多大的浪了。所以儿子认定,这是我们一举扳倒夏言那个老东西的天赐良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爹爹万万不能再犹豫了……”
儿子分析得头头是道,听着也有几分道理,可是,早在严世蕃方才滔滔不绝地搬弄口舌,希望能说服父亲之时,严嵩心里却已经把此事想的明明白白:眼下绝非与夏言一党全面决战之时!皇上乃古今罕有的雄猜多疑之主,这些年里,皇上帝王心术更是越发地精进了,如羚羊挂角一般不露痕迹地布局人事,全是为着两个字--“平衡”!当年将自己闲置、起复夏言;嘉靖二十三年闲置夏言、起复自己;嘉靖二十六年又再度起复夏言,出任新增设内阁资政……每一次朝廷重大人事变动,无不围绕着这两个字。也就是说,皇上绝不会允许朝中一党独大,绝不会容忍大明出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再者说来,眼下江南要改稻为桑,全国要清丈田亩,南洋那边还要用兵,在这个节骨眼上,皇上怎么可能让朝中再起波澜?设若皇上当真如此昏聩,早就被夏贵溪之辈玩弄于股掌之间了,还谈何富国强兵、再造中兴?
同时,严嵩的心中,对以前一直欣赏的儿子突然产生了几许失望:以他的才智,应该能够洞悉朝局、明辨顺逆;时常行走御前、侍奉君侧,更应该能够摸清皇上的心思,怎么会如此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会否是因为这些年里,仕途走得太顺,眼下又升兼了号称“天下第一抚”的应天巡抚,便迫不及待地做起了入阁拜相的美梦,以致头脑发了昏?还有,方才为了说服自己同意与夏言决战,不惜大肆渲染夏言的圣眷正浓、威望中天;此刻为了坚定自己心志,却又说夏言圣眷已衰,要落得墙倒众人推的悲惨境地,把权谋诈术用到了自己父亲的头上,这可不是身为人子所能做的事情……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争宋
- 简介:该简介已被管理员屏蔽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225.2万字6年前
- 三国听风录
- 简介:特种兵刘琦,在一次意外中穿越到了三国时期,并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八骏”之一的刘表的大儿子刘琦。此刘琦已非历史上的彼“刘琦”,看刘琦如何扮猪吃虎,默默发展。等待时机,一遇风雨便化龙,将三国的天搅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这么好的条件,荆州,收了;猛将,拿下;美女,嘿嘿,你觉得刘琦会放过么?天下,一切尽在掌中。。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59.0万字5年前
- 旭日东升
- 李云慕:“将军咱们的弓兵怎么拿着复合弓啊。”将军说:“那是墨家的十里追风。”李云慕:“。。。。。那个将军,咱们重骑兵的盔甲怎么这么轻。”将军说:“那是欧阳家冶炼出来的飞云钢,轻便合身利于奔袭。”李云慕:“丞相,你一个堂堂一品大员怎么会怕一个打铁的?”丞相:“不怕不行啊,那老家伙,随便搞点东西出来,那些江湖势力都搅风搅雨的,你说我能不怕他吗!”李云慕:“夫子,您今年究竟多少岁了?”夫子:“不记得了,记不得了,不过活的久还是有好处的。”
- 2.6万字4年前
- 千古荡雄剑
- 唐朝末年,天子昏聩羸弱,奸佞乱朝;酷吏横行,人心离散,以致烽盗四起,天下扰动。枭雄聚众百万,兴兵乱唐。各路诸候,拥兵自重,几不受唐廷节制,彼此攻伐不休,乱象始现。武林盛传,灵山使者,现身江湖,其手握秘书神剑(荡雄书和伏天剑),欲寻访真命天子相授。得剑书者,便可重整乾坤,建不世功业。武林中人,各择枭雄归附,为取书剑,彼此明争暗斗……
- 1.7万字4年前
- 中世纪演绎
- 唐纳德的前世、后世在西方中世纪时期的故事演绎。用东方人的思维与智慧谱写了西方中世纪的战国史诗。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求收藏、点赞、推荐……
- 11.0万字4年前
- 龙战于野之北宋末年
- 这是北宋末年的水浒世界,天下风云变幻,华夏内有四大寇(宋江、田虎、王庆、方腊)作乱,外有金夏辽进逼。身为汉家男儿的夏华在来到这个时代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捍卫汉家山河、保护汉家同胞的铁血征途,为华夏苍生奋斗前进不息,谱写一曲轰轰烈烈的英雄战歌。
- 24.6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