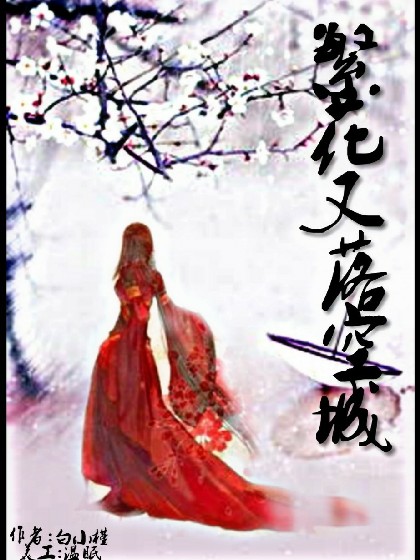第二十一章傻子表哥2
岳托倒也没闪避,大大方方地说:“岳托。”
阿木沙礼眨眨眼,总觉得哪不对,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岳托的语气似乎不像是在说自己的名字,他肿起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她,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不知道为什么,阿木沙礼就是有种他刚才其实是在说她是傻子的感觉。
阿木沙礼按捺住撇嘴的冲动,笑得愈发灿烂,这表情是日常做惯的,家里的长辈甚至底下的奴仆,没有一个不被她的笑容俘虏,然后说她可爱,乖巧,之后不管什么都会轻易答应她。
“好傻……”他别开脸。
阿木沙礼一愣。
他口齿清晰地补了句:“你笑起来真傻,就跟个傻子一样。”
她的笑容骤敛,圆嘟嘟的包子脸鼓起,眼珠子瞪得快凸出来了,她从炕上跳起来,叉腰指着他大骂:“你才傻子!你个大傻子!”
屋里静候的奴才愕然,格格居然发脾气了,这可是件稀罕事。
岳托点点头:“这样才像是三姑的女儿。”居然脱了鞋子,爬上炕来。
原以为他会生气,没想到岳托只是表情平静地爬上炕,然后整个人靠在褥垫上慢慢侧躺下身子。
阿木沙礼好奇地看着他,眼前的这个傻子表哥与她从小玩到大的表哥表弟都不一样,像大舅家的杜度表哥就很宠她,听她的话,但凡他有的东西,只要她开口,杜度眼都不会眨一下就送了给她,以至于一度让术禄看在眼里很不是滋味,杜度待自己的亲妹妹都没有这般好。再有就是大舅家的国欢表哥,因为从小身体就不好,所以很少外出,骑射游猎这样的活动,噶禄代舅母都不许他沾一下边,但有一次阿木沙礼说想去冰上玩爬犁,拉着国欢一同去,结果把国欢冻病了,回来却只说自己想去的,只字没提是阿木沙礼出的馊主意。
大舅家的两个表哥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四舅家的聂克塞,虽然只比她大了一岁,只见过几次面,但显然聂克塞受过四舅和四舅母的耳提面命,对她这个表妹惟命是从的很。
如果说表哥宠表妹,那是年长爱护幼小必须的,那五舅的长子迈达礼比她小了一岁,今年才五岁,次子文顾四岁,三子萨哈良两岁,这三个表弟来往的最多,却也最懂得礼让她,这也许是因为五舅母同时也是她的姑姑,所以这三个表弟就和她的亲弟弟一样,四个人感情最好。
七舅家有一个四岁的名叫萨伊堪的表妹,仅见过数面,似乎不是太好玩。还有一个表弟叫尚建,和五舅家的萨哈良同岁。
阿木沙礼掰着手指头在心里默默数着自己几个舅舅家的表哥表弟,忽然想起,除了三舅至今无所出之外,她对于二舅家的表哥竟然真的一无所知。额涅往二舅家去的最勤快,但同时也最反对她和二舅家的同龄孩子交往。她模糊记起去年听阿玛说起二舅的大福晋生了个小阿哥。阿木沙礼最喜欢这样的喜事,因为请满月酒的时候,能在酒席上见到好多同龄的表哥表弟,只可惜,最后额涅还是没带她去二舅家,而且把她丢给乌吉嬷嬷看管,不许她踏出大门一步。
如果没记错,那个小阿哥后来取名叫巴喇玛。
“岳托哥哥,巴喇玛弟弟现在长什么样了?”阿木沙礼决定从最容易切入的话题入手,“会走路了吗?会对你叫哥哥了吗?”
躺在炕上的岳托哼哼了声,没搭腔。
阿木沙礼伸长脖子偷觑他的脸色,可是岳托的脸肿成那样,这会儿他又闭上了眼,更加看不出喜怒来。
她想了想,换了种特别讨好的语气,伸手扯了扯他的袖子,撒娇道:“哥哥,哥哥。”
袖子扯动,岳托咝地吸了口冷气,闭着的眼睛陡然睁开,独目的右眼寒光激射。
阿木沙礼吓得急忙松口,捂住嘴巴,小屁股坐在炕上蹭啊蹭的拼命往后缩。
她蹭得快,却没岳托手伸得快,岳托的手一把抓住她的右脚脚踝。
阿木沙礼嘴角往下一拉,哭丧着脸颤声:“哥、哥……哥,你要做什么?”
岳托肿着眼看着她:“巫医还没来?”
她拼命摇头,大概又觉得摇头不够表达她的意思,抬起两只手一起拼命摇了起来。
岳托“嗯”了声,继续闭上眼:“我睡会儿,巫医到了,你叫醒我。”说着,松开了手。
阿木沙礼当即像只小兔子一样弹跳下炕,趿上鞋子便要跑,跑到一半又犹豫着转了回来,站在炕边上低头悄悄看着岳托。
“哥哥,你要盖被子吗?你这样睡,会着凉的,着凉了会生病的。”
岳托没回答。
她想了想,又踢了鞋子重新爬上炕,然后跑墙角的柜子上层去拿被子。可惜她人矮腿短,够不着,伸手抓了几次,指尖堪堪够到被面。
屋里伺候的丫头终于没法再装木头人了,上前小声问道:“格格想要做什么?”
“帮我……拿被子……啊——唔!”
话没说完,她就被滑下来的被子给砸了个正着,整个人被压在了被子下,只露出两只脚在不停地踢腾。
小丫头一边忍笑,一边将被子抱了起来:“格格,您没事吧?”
脱困的阿木沙礼大口大口地吸着气,回头看岳托,居然像是完全没有看到刚才那一幕一样,仍然躺在炕上一动不动,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她突然觉得心口酸酸的,特别委屈,换成其他表哥,早飞奔过来救她了,哪有像他这样,明明是替他拿的被子,他居然看都不看她一眼,任由她被那么重的被子砸,也无动于衷。
难怪额涅不让她去二舅家找表哥玩,原来是这样。
她委屈地想,原来二舅家的表哥根本不喜欢她,这是她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这么直接地表现出对她的不喜欢。
她阿木沙礼从来都是人见人爱的,不管是长辈,还是同辈兄弟,她嘴儿甜长得可爱,从来都是无往不利地讨大家喜欢的,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还有人会不喜欢她。
她越想越委屈,看着岳托双目紧闭的样子,突然觉得这个人特别憎恶起来,不仅长得丑陋,连他的心也是丑陋的,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讨人厌。
她恨恨地想着,感觉腮边有些发痒,用手一蹭,居然是湿的。再伸手一抹,才发觉原来自己刚才竟然哭了。
“格格?”小丫头抱着被子,忐忑不安地看着她。
阿木沙礼憋着气,咬着唇,脸上的神色变幻了好几次,最后默默地却从小丫头手里接过被子,同时示意她走开。
那被子很沉,她一个人抱不过来,于是被子一半儿抱在她怀里,一半儿拖在炕上,她踉踉跄跄地抱着被子走近岳托,嘴里甜甜地喊着:“哥哥,给你被子……”
岳托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那圆滚滚的一个影子向他靠近,他正觉得冷,猛地变觉得身上一重,显然是那个小人儿连人带被子一起砸到了他身上。
他闷哼一声,只觉得浑身骨头像是要被拆解似的,已经说不清这是种什么感觉了,说是疼,可他觉得那种感觉比疼痛还要难受百倍。
“哥哥!”阿木沙礼趴在他身上惊呼,小手伸到他鼻下探了探,只觉得灼热的呼吸喷在她手心里,像火一样烫手。她不敢伸手去摸他的脸,但再懵懂,也知道他这情况是不太好了。急忙大叫道:“去叫额涅来!快去叫额涅来!”
——————————————————
莽古济赶到的同时,一并来的还有姗姗来迟的巫医。
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岳托脸上可怖的伤势上,却忘了他身上也挨了不少打,只是莽古济万万没想到,把这孩子的衣服扒下来后,还发现了不少旧伤。
巫医原先以为这孩子是府里的哈哈珠子,不是很乐意去看,莽古济放了些重话后他才慎重起来,诊治得比原来认真了许多。
阿木沙礼坐在岳托边上,看着巫医将那裸露的小身板翻来覆去的用温水擦洗,随后又用一种不知名的草药捣烂出汁,一半儿喂进了岳托的嘴里,一半儿继续涂抹在他身上。
岳托从头到尾都没出过什么声,要不是阿木沙礼发现他那只右眼是眯起的,她都不会知道原来他是醒着的。
被扒光的岳托瘦条个子,胸前背后的琵琶肋骨突显,因为长得不算矮,所以愈发就显得身上没几两肉,加上青紫的淤伤,皮肤显得特别狰狞丑陋。
阿木沙礼心情复杂地打量着岳托,她有些不忍去看他,而恰在这个时候,乌吉嬷嬷赶在巫医扒下岳托裤子前,伸手捂住了她的眼睛。
她眼前一片昏暗,只能看见乌吉嬷嬷苍老的,布满褶皱的手纹,这时候她的听力出奇地增强了,她似乎能听见岳托的呼吸声,又似乎能透过乌吉嬷嬷的手掌,看到岳托像一条离水的鱼儿一样被人摁在了案板上,无力挣扎,任人剐凌。
“哥哥……”她伸手过去,胡乱地抓着,“哥哥……不疼,哥哥……不疼……”
她嘴里喊着“不疼”“不疼”,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也不知道喊了多少遍,终于眼前一亮。
乌吉嬷嬷放开了手。
岳托平躺在炕上,身上盖着被子,额头顶着一块湿帕子,巫医站在炕边上在擦手:“热度退下去就没事了,这次的伤倒是其次,主要还是受了惊吓。待我出去再请一次神,自然就好了。”
色尔敏道了谢,给了赏钱,请巫医出去。
莽古济坐在炕的那一头,目光幽幽地看着岳托,好一会儿才无奈地叹了口气。回过头,遽然发现女儿泪流满面地坐在岳托边上,满脸悲伤。
“阿木沙礼?”
“哥哥……”她没有听见额涅的呼唤,只是低头看着岳托,“等你病好了,我陪你一起玩。我保证不让人再打你,谁要是打你,我就……我就打他!”
岳托眼皮无力地抬了抬,最终沉沉地阖上。
莽古济又是一声叹息。
谁与为偶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天才冷血妃
- 简介:一张休妻纸,一个巴掌,一副残容。这是她从他身上得到了。再一次,她不在是她,王者的归来,化解内心深处的仇恨。而一向强势的她,却遇到了一个男人纠缠着她,可她好像,对他讨厌不起来呢。"顾轻云,这辈子你是逃不掉的!"“哼,彼此彼此”
- 1.8万字6年前
- 我的美男夫君们
- 简介:本人正宗花痴一枚,不小心赶上潮流穿越了,还到了女尊世界,从此美男抱不完。温柔可人的军倌,一点就炸的竹马……肖若水抚上隆起的腹部,眼神温柔似水道:“笑影想要男孩还是女孩?”我屁颠屁颠的跑过去扶他,笑道:“都好,生男孩我保护你们爷两,生女孩我们娘两保护你。”肖若水成功的感动的直掉眼泪。迟瑞嗤笑一声问我:“那我呢?”我白他一眼说:“生女孩我养,生男孩你自己养!”迟瑞成功炸毛。
- 23.2万字6年前
- 繁花又落空城
- 简介:读前须知:剧情很狗血。文笔的话,毕竟我才10岁,自是不如一些大大们女主略微斯德哥尔摩,不喜者慎入不要吐槽女主名字,本作者起名废喜欢的欢迎收藏ʘᴗʘ特别感谢温眠小可爱给我做的封面哦本小说的剧情没有最狗血,只有更狗血
- 3.5万字6年前
- 哦我的皇帝陛下之如果我还爱你
- 简介:【本文原创,禁止抄袭】大大QQ2477175048加群464500761
- 7.5万字5年前
- 月夜清风
- 简介:看就对了,嘻嘻。[本书绝对原创,禁止抄袭,谢谢合作。]
- 0.3万字5年前
- 将军太饥渴
- 简介:夏天的夜晚也是微凉,三更时悠悠转醒,眼前宽厚的后背让我心里一惊,:怎会有个男人在房里,难道,他回来了? ……他扳过我的身子,将我护在胸口的手轻而易举的拉开,俯身将头埋在我的颈间吮吸:“要听话,恩?”
- 5.0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