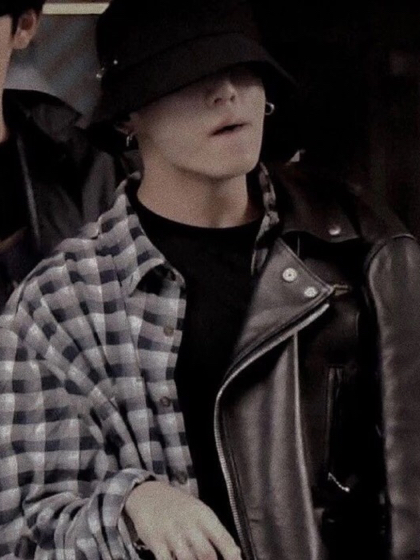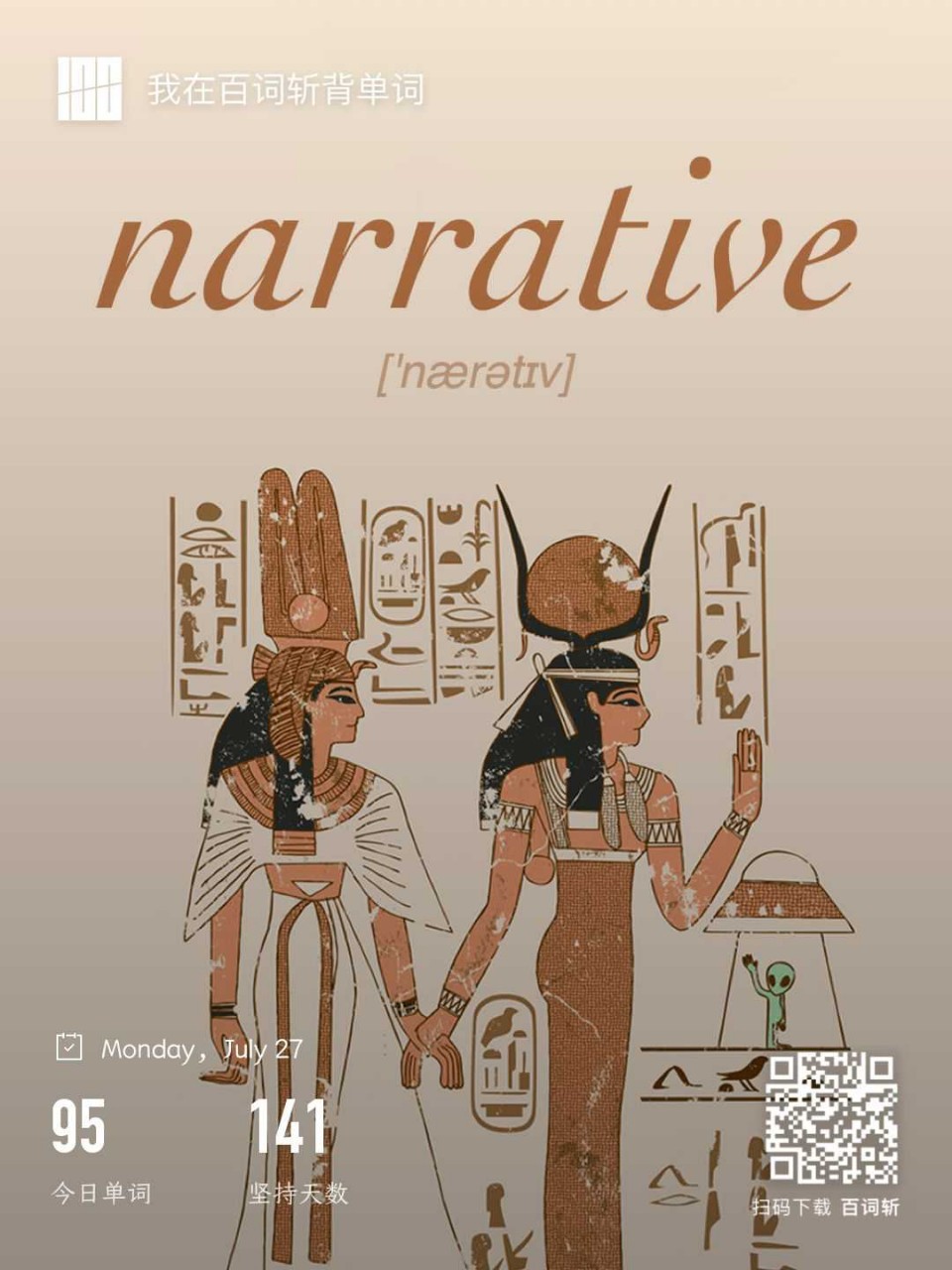诗集,风车,神明与她
神明微笑着普度众生。
我小心翼翼捧着泰戈尔的飞鸟;满口清甜地嚼着花间集的余香;在丁香花细腻的忧伤中彷徨着;也在白玉苦瓜的柔光中做一个个深蕴清莹的似醒似睡的梦。
于是我想象一抹身影在绿意盎然的藤蔓下半遮半掩,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在狭窄泥泞的小巷,乌镇旁的青砖石瓦上也攀上了影子。像梦中的蓝铃花,幽香幽香的。
——我的第一个朋友。
而我们的相遇飘开的却是一股子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好吧,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是吗。
我认。
*
我的房间很大也很空旷,白白的墙白白的顶,白白的帘子上印着蓝蓝的纹。每到清晨,阳光就缱绻着要闹落了我枕畔流着口水的梦境。它会带着一抹缥色轻手轻脚钻过帘子的捕捉,微微润出绯色的光晕来挠我的脸颊。它费力扯开我懒惰的眼皮,叫我分不清到底是不是早到了晌午。韵开了眼角湿气,待被闲置了一夜的四肢的酥麻感与云儿一样翻滚着淡去后,思绪便从遥远的雪山尖上被一把拽了回来,硬生生塞回了脑子。这时候,我就一个打挺,方才意识到我是谁,又是什么时候了。
我身侧的床位还在翘首以待,大约是受了浪漫派主义诗人的影响,我总觉得它是在等候命定的那个下凡者。时光正好气氛正好,我正陶然于其间乎的时候,理性派的产物,也就是我的床垫总会不合时宜地哼出“惹”的一声叫唤。
啊,当然了,没有人其实是最好的吧。
虽然我是很想交朋友啦…….
狭隘的床铺无论铺几层毯子都是硬邦邦的硌人,虽说腰肢被梦柔软地抱怀着,大半夜还会潮的人浑身灼热发汗。一个翻身,就引得四肢疼痛。当然其中不乏我天生体质的缘故。母亲常常捻了被子在床头给我读诗,毫无缘由的,我挺喜欢余光中的白玉苦瓜,但其中母亲读得最多倒的是舒淇的致橡树,且读着读着就哑了声花了脸,像公益戏班子里唱的江山如画。
有时候我会看着玻璃窗外面那个世界,淡淡的伤感,我会费力的撑着身子,抬起头来问母亲,我是不是被外面的那个世界除了名。每到这个时候呀,母亲就沉默起来了,她会把诗集柔柔放在桌面,背过身去,垂下头去,肩头不显眼地战栗,过一会儿再转回来的时候却还是笑盈盈的,却沾染氤氲的水汽。像开了盖的汽水,渡着丝丝凉意。
我看着日头从东边漂移到西边去染红那儿的天际线,看了足足有十四趟后,我的“专属房间”终是迎来了第一位客人。她进来时被口罩掩着脸,神情木木愣愣的,犹然坠着泪痕,我见犹怜的样子。和我进来时一样,我瞥见她也是皮肤青肿,点状出血。在走动时许些气喘,甚至于小小眩晕。待她的父母一脸疲惫地为她备置好了物品,与医生一同出去时,我便不请自来地上前去触碰她地脑袋。嗯,果然也是滚烫滚烫的。
出乎意料的是一直像个活死人一样的她一把拍掉了我这个不速之客,叫人手掌生疼生疼的。我委屈巴巴抱着手瞥过去,却惊异于她一脸淡然的神情。她睨向我,横着眉毛见怪不怪的模样,撅起嘴巴说:“怎么,没见过一点伪装术?”
少年老成。我脑袋里蹦出前天晚上新学的成语。
她环顾四周,躺倒在床上盯着窗外看,有模有样叹了口气,“怕什么嘛,生病罢了。又不是第一次来医院……虽然是第一次睡病床啦…….但发烧算是小病吧,无伤大雅无伤大雅。”
我轻轻缩回了手,手心中仍然是暖暖的,叫我几乎误以为是她脑门上残留忘返的温度。我也向那个有着细碎的树荫和像水一样会随着四季变化的风的世界看去,阳光将一溜儿流光碎金抛洒在我的窗沿,而我就要脱口的话语生生被制风机吞吃了。
我想说,可这不是仅仅发烧呀。白血病是神赐予给自己喜欢的孩子的。我们很快就会被神召回,去陪伴他了。
但我终究没有说出口,毕竟总会有一种抢风头的意味,像是有意要夸耀卖弄自己的学识面,而母亲说过的呀,做人嘛,就是要谦逊有礼。
那我还是不要说这样一个高深的术语了吧?
*
母亲说过,我是被神明偏爱的孩子。
她不只一次的这样喃喃低语,双眼通红浮肿。
记忆里第一次来医院做检查是在我鼻血不止后,报告还没出来的那天,母亲带着我去见了她的神。
她跪倒在她的神前面,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却泪流不止。我听到她感恩代谢着神对于我的厚爱,却也祈求着神明不要带我远去。
母亲站起身来,倒出白开为我冲洗鼻血。血水蹦跳在神像周身的一壑土地上,沿着纵横交错的沟壑延伸。母亲的手是颤抖着的,水瓶被战栗的指尖不慎打翻,她就用纸巾不住地轻拭我的鼻端。神像高大而巍然,余温里仍有滚烫的空间存在,烧在我的胸口上鼻腔里。于是我的手掌也就不自觉合成了一个,我虔诚又迷茫,我向上看去,神的身后是一片如血的夕阳。夕阳是不是意味着浴火重生,我不明白。但我对着微笑的神像求着被渡求着重生。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分不清神与神的差距,我是最愚蠢的信徒,活该受到神日以继夜的惩罚。可我的母亲不该。我的眼睛凝望着神,神面慈祥,阳光普照杂糅着泥垢停留在神的脸上,一小只风车被我拿在手心,翻滚得永不停歇。风车就这样呜呜地转,神像高的不像人间,我也不自觉跪了下去,叫风车砸落在地上,好像这样就可以偿清我的罪过似的。然而面对我的只有一波又一波的热浪,刻进了我的骨子里,在皮肤上头生根,在骨子里枝繁叶茂,叫我哭的肝肠寸断。我的头牢牢贴在地上,直面着神慈爱的笑,尝到了泥土的苦涩。这时候有一抹凉意靠近我的额头,我迷惘的去看,那是母亲的手停留在我的额上。
她紧紧的抱住我,怀抱像梦一样的柔软,却不心安。
我不是被神抛弃的孩子,正因为我的特殊以至我被神明青睐。神希望我可以早日陪同在他的身侧,才使我历经这样的磨难。
——母亲这样说。
“我是被神明偏爱的孩子。”
不只一个晚上我拽着小小的风车抽泣着将眼泪憋回肚里。
夜里其实是最最喧嚣的时候,很细小很细小的声音悉悉嗦嗦,都被无限放大。我坐在窗前,外面那个世界里树叶大声扯着嗓子嚷嚷,摩擦着互相取暖。冻僵的风在空中卷起废弃的纸以此来裹住冰冷的身子。哗啦啦哗啦啦,那是水管向外呕着污水抱怨的声响。医院后面不远处是火车站,夜半偶有一辆老旧的火车哼哧哼哧费力的爬过。好像在说,我也老啦。
神心慈悲,他将月光的清晖施舍在我的窗口稍作停留,他允许月的水袖在人间流连忘返,使我足以看清这一些。其实也不必的,外面总是灯火通明,虽然极少有人从我的视野内走过。梧桐叶子遮掩掉了半边天,林立的楼房也叫我看不见日出时的壮丽。
“我是被神明偏爱的孩子。”
我抱着诗集,盘腿坐在床沿,坐到腿根发麻。
“我是被神明偏爱的孩子。”
我会看向泛着青的小半边天,我会在想神明是否也会透过这扇窗注视着我。
“我是被神明偏爱的孩子。”
有时候看着路过的女孩子们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我想,哎呀,我就要一夜白头了。要是我有头发的话。
可惜我没有。
历经化疗后,我早就是一个纯正的卤蛋了。我的骨节疼痛,牙龈也有些肿胀。医生却笑着说我该庆幸还没有到肝脾肿大,头痛呕吐的时候。这说明至少癌细胞还没有攻破我的神经中枢。
“我是被神明偏爱的孩子。”
我不知道是与否,她也是么?被神明偏爱的孩子。
*
我还是孤独,可以略微聊以慰己的竟只是她也和我一样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入睡时护士姐姐会温柔的拉上我们中间的帘子,祝我们好梦。帘子很薄,而夜半总是孤寂,但我听得到帘子那头的啜泣,还有她泪眼间的吐息,于是我就吹起风车。
“呼呼,呼呼”
神明,高高在上的神明,他听得到吗?
她啜泣着,全然没有了白日里的跋扈。我知道她的脆弱,清冷的月光却被帘子阻挠了,无法穿透于她。然后我也哭泣起来,我祈求神明的宽恕,我说我不是一个好孩子,我祈求神明不要那么快叫我脱离人间的疾苦,我说我喜爱尘世的烟火。我默念起童谣而不是诗歌,泪水就顺着脸颊贯彻进病号服,呜呜的呜咽像下水管道排水时的痛苦。
我们都知道我们醒着,可谁也没有说话,没人把帘子撩开对对方笑,或者像书中那样互相取暖照亮。不,我们没有。我们为自己的命运而担忧,同时又同病相怜。呜咽中我们沉沉睡去,再在缱绻的阳光下被闹醒,头轻脚重地开始新的一天。
“我们都是被神明偏爱的孩子。”
*
神似乎分外再喜爱她一点。
医生带着她骨瘦嶙峋的父母回到病房,皱着眉头说,“这可不是个好现象。”
那时候,轻敲她的胸骨,她就会有剧烈的疼痛了。
那是她第一次毫无形象的趴在我身上大声哭泣而不是沉默地打游戏,她面色惨白,鼻涕眼泪糊了我一肩。我看着她光光的脑袋,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我万能的神明啊。
那一次她啜泣着小声对父母提出想回家乡看看,医生叹了口气表示默许。由于离火车站不远,母亲带着我也一同前往了。
走的时候她轻轻的笑,说:“再见了。”
她总是这样说。后来她出去了亦或者是去做骨髓移植都是这样的。她总是用手指拂过耳畔,好像那儿还有散下的碎发似的,疲惫的笑,说:“那就再见了。”
我也会小声回应:“嗯,再见。”
像是一种誓言,儿童之间的契约。
再见。会再见的。
*
我和她匹配到合适的骨髓只一天之隔。
医生说,骨髓移植的成功率在40%---60%左右。
嗯,至少机会不算小嘛。
于是我们接受麻醉剂的洗礼,当我懵懵懂懂的再次躺回了病房时,母亲喜笑颜开。
母亲拿起书本为神明的仁慈流泪,只因医生说手术成功的几率很高。
但“她”的情况似乎不怎么允许乐观。
她开始头痛,恶心,视力模糊。医生说这是由于腔内脑脊液会不断的向脑室产生,这时期便会产生循环障碍。
是白血病晚期的象征。等同于下了死亡通知书。
——是神明要来找她了呀。母亲这样安慰着她的父母,而我和她相对无言。她依旧像平常那样玩着游戏,而我将诗集平摊在腿上吹着风车。
“呼呼,呼呼”
她很少输游戏,自详是国服第一奶妈。但那把她输了,一败涂地。因为泪横着手机屏幕流到控制键上,失了手感。
后来医生似乎咨询了她什么意见,她就又要走了。她说想再回去看看。
那天的风吹的好大,我手中的风车转个不停。夕阳晕开一大片的红色,层叠着绿色的叶子。好美好美。火车的轮转声还是咯吱咯吱的,压着轨道上散落的鹅软石,伴随着的汽笛声,也是好大好大的。我说不清楚是夕阳吞吃了火车车厢还是火车车厢挡住了夕阳,它是逆着光,从一大片模糊的暖阳中直直冒出来的,渡着一圈暖暖的光晕,奔向我们。
她瘫坐在轮椅上歪歪头,笑了笑,露出一对可爱的小梨涡,又冲我挥了挥手。
我就一下子被眼泪冲崩了防线。
我想说再见的,可是她没有,而我知道我不能。
所以我也挥了挥手,泪影阑珊,我牵着母亲的手看着他们上了火车。风也被夕阳烤暖了似的,它捉住我眼角的水花欢快的把玩,我看到她贴着车厢的玻璃,嘴角牵扯着动了动,似乎是“拜拜”。
我瘫软在母亲的怀中,一时间我哭的头痛欲裂。其实我与她分明没有建立起什么深厚的情感,至多算作是室友再加上病友了,她玩她的手机我读我的诗集,但是我哭的撕心裂肺,像当年在神像前那样崩溃。
*
后来我康复了,出了院,也上了学,交到了很多朋友。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封建迷信。我也知道了神的存在不过慰藉。
太好了,我终于脱离了那个房间了。
我来到外面这个世界了啊。
但她被那节火车车厢载走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我随着母亲再来到神像前,说是“还愿”。神像后是一片如血的夕阳。美得叫人心悸窒息。
我跪拜在神像前说着千篇一律的感激的话语。
走的时候我将那小小的一只风车插在了土壤间。
“呼呼,呼呼”
它站立在荒芜似的土地上,转动着鸣叫。
我再向神像看去。
神对着我报以微笑。
End
一株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十里画廊.
- 简介:春风十里五十里一百里体测八百米海底两万里德芙巧克力香草味八喜可可布朗尼榴莲菠萝蜜芝士玉米粒鸡汁土豆泥黑椒牛里脊黄焖辣子鸡红烧排骨酱醋鱼不如你全都不如你
- 0.4万字6年前
- 田柾国-揪小国呆毛
- 简介:“学长,打球渴了嘛,这里有脉动。”“可是学长不想喝脉动呢。”“学长,想和小学妹接吻。”程输。
- 0.6万字6年前
- 神陨.龙皇传
- 简介:<必看>本书共60章,本书不定时更新,偏差小余一个月!——————————神界的一场灾难,导致霍雨浩拥有了金龙王的神核,龙皇在临,战天下。——————————伴随着魂导科技的进步,魂兽也随着人类魂师的猎杀无度走向灭亡,沉睡无数年的魂兽之王在星斗大森林最后的净土苏醒,它要带领仅存的族人,向人类复仇!霍雨浩带着前世记忆重生。重生来道斗罗大陆立志要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可当武魂觉醒时,苏醒的,却是…………——————————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脚踏阴阳定乾坤,荒古之今我为尊;霸天绝地无人挡,贸然一人杀天殇;血路凋零残花亡,残躯镇世仍为皇;在持神印杀四方,只为守护心中人。
- 1.7万字5年前
- 查理九世之脆弱的心
- 简介:他的心很脆弱,需要我们的保护
- 1.1万字5年前
- 祁妃杂货铺
- 简介:这里祁妃,免费封面免费封面收藏即可下单加急送100花给《赛尔号之卡樱念》
- 0.2万字4年前
- 多读书多看报,少玩手机多睡觉
- 简介:如题。开启话本新玩法。督促自己,暑假过得像个人一起玩么?
- 1.4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