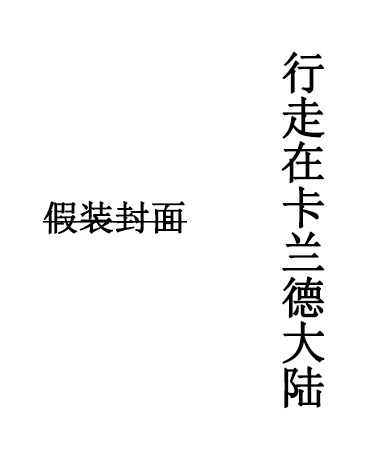Chapter 17.阿密洛(上)
披着猫头鹰翼肩饰的两个皇家事务员跟随卫兵走进这座粮仓时,阿密洛正蜷缩在堆高的橄榄箱子与弧形墙壁形成的狭小空间里昏昏欲睡。建筑的独特结构能够捕捉并放大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事务员虽然有一副软绵绵的嗓音,传到阿密洛耳里却如狮吼一般。他小心翼翼地从两只木箱的缝隙里望过去,确定来人之中没有“风沙之子”,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放松了些。他们只是来查看大致的物资状况,然后派遣专事清点的奴隶核对箱子与账目的数量及成色差异。自己只要听清楚奴隶什么时候来即可。然而两个事务员跟卫兵似乎是街邻,开始谈起诸如谁家儿子订婚之类、哪里的面包房又坑了人之类的闲话来。
阿密洛已经记不清自己躲进这里有多久了。粮仓没有窗户,只有接近屋顶的地方开了六个又长又扁的通风口。地板由切割工整的青色石块铺就,大大小小的箱子圆桶堆得像山一样高,里面装的尽是橄榄干、葡萄干、无花果干、甜枣干一类的东西,导致空气闻起来有种令人作呕的甜味,但也恰好遮盖了他身上的味道。脚下的两块石板,其中一块是可以经由墙上机关开启的暗门。地下密道通往下城区边缘的一处街口,有一座干净的蓄水池,旁边还歪歪斜斜地耸立着帝丽安时期遗留下来的公共浴室以及专门为流浪儿、乞丐、残废和穷光蛋提供干面包、臭鱼汤和烂洋葱的救济食堂。他第一次端着鱼汤坐下来的时候,旁边瞎了一只眼的老头子告诉他:“如果你喝到耗子,千万别大惊小怪。”
开饭时间是每天傍晚。迄今为止,阿密洛还没有喝到过鱼鳞和鱼刺以外的东西。赶上运气好,还能吃到一点鱼肉。
他不知道那个年轻却杀气腾腾的风沙之子以及那些士兵是否还在搜捕自己。如果是的话,显然他们没料到我会躲在干货粮仓里,还靠那种稍微有点身份的人看上一眼就会反胃的地方解决饥饿。那件老师生前命令自己穿的神庙佣人袍子已经脏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边角也破破烂烂,睡觉时左肩的位置还叫老鼠啃了一个洞。阿密洛没照过镜子,但他很确定就连莎米恩也没法认出这幅样子的自己。
自从分别以来,他没再从任何人口中听到任何有关她或是那两个埃斯洛特人的消息。想必他们已经平安离开伊西了吧,只要能搞到一艘船,抵达蛇岛应该不是难事。请求埃斯洛特的神保护她的念头也曾萌生过,但很快阿密洛就意识到自己既不熟悉永夜神祗的名讳,也不知道任何祷词、颂歌或是可以接受的祭品。他只能寄望于那个高大骇人的亲卫队长信守诺言,保她安全——最好还能给她找份翻译或者文书的工作。即使心里知道存在可能性,他还是不愿思考恋人是否会沦落至蛇岛那如苔藓般丛生的妓院里去,以免噩梦连连。
“我堂兄在图书馆工作,那儿的学者们说今年的冬天可能比以往更长更冷。”卫兵跟两个事务员说。
“我不担心冬天长不长,”个子比同伴稍微高一点点的那个事务员说,“我只担心咱们的新女王别是个像她弟弟一样的疯子。”
“啊,这话要是叫女王的狗腿子们听见,你就等着被拖去喂鳄鱼吧。”另一个事务员道,“别说我认识你。”
卫兵不太乐意地瞅着他们。“陛下是‘神选女王’,诸神选了她,带走了她的弟弟和妹妹。”
第一个事务员叹了口气。“我听说她打算拆了阿塔门神庙。”
“闭上你的嘴!”同伴呵斥他,“难道你还想拖我们俩陪你去喂鳄鱼吗?”
“‘风沙之子’的首领在陛下面前比那新上任的军务大臣还吃得开,你们肯定也听说过吧?这不是什么秘密。我只是说,女王要把阿塔门神庙改成安喀西亚神庙,是很有可能提上日程的事。”
三人谈话的内容令阿密洛惴惴不安起来。坐视贝勒奈西摧毁神庙,这是绝对不能被容许的,他心想。我坐视埃斯洛特人摧毁了蛇岛的神庙,不能再坐视伊西人自己摧毁伊西及里亚的。然而意愿上的不容许是一回事,拿出真切的行动前去阻止又是另一回事。
事到如今,我一个人,一个逃犯,还能做什么?
事务官们和卫兵离开之后,阿密洛独自一人思索到天黑,也没想出什么头绪。考虑到自己的脑袋或许是被这里的甜味给熏晕了,他便自地道离开粮仓,来到街上,然而下城区的腥臭夜风亦没对思考带来什么帮助。想来想去,他决定先冒险溜到神庙附近——甚至里面——去查探一番。躲在粮仓里能获知的信息实在太少,或许那个事务官不过是听了些毫无根据的传言而已。
不过,若此事当真牵扯到“巫师”,恐怕又是另一回事了。
借着夜色悄声穿越大街小巷时,阿密洛努力搜寻着与风沙之子首领相关的记忆。有人说他就像大祭司的影子,一个非常可怖的影子。也有人说,巫师是大祭司的弟弟,就像安喀西亚是阿塔门的弟弟一样。一个更离谱的赫罗美亚版本甚至声称伊西神话其实是个古老的故事——时间伊始之时,三个比伊西人更高等的种族的成员从遥远的星辰降在大地上,两个男人,一个女人。那两个男人便是阿塔门和安喀西亚,即大祭司和巫师。伊西人的祖先钦佩阿塔门的智慧、学识与法力,甘愿向他臣服,奉他为这片土地的国王,然而安喀西亚嫉妒自己的兄长,于是谋害了他,还将他的残躯洒遍伊西各处。那个被伊西人称作生命女神的女子寻遍埃塞河沿岸,将阿塔门的残躯拼了起来,令他复活。阿塔门对弟弟的背叛怒不可遏,却不能犯下弑亲的罪行,只好毁了他的容貌,将他发配到地表以下,禁止他与地面上的生灵来往。这个疯狂的故事还配上了颇能令人信服的细节:“巫师”脸上的疤痕乃是经由大祭司的光辉烧灼导致,而大祭司从不换下那身系铃紫袍则是因为它蕴含着复生的魔力。
在无神论者眼里,神话皆是尚未解开的谜题,宗教则是愚人给自己灌下的**。阿密洛在神庙里长大时,周围的人都同意“巫师”的疤是帝丽安统治时期留下的——即使投了降,他还是忍不住顶撞了“女武神”一次,然后就跟自己那张虽本就不怎么好看、但至少比现在好看的脸蛋说再见了。
粮仓离阿塔门神庙有着相当一段距离,赤脚则让这段距离又长了一倍。他原来的系带凉鞋早就在被追杀那天断裂、遗失了。加上藏身以来每天走的路非常有限,脚底茧子的厚实程度还不足以隔绝踩到砂砾的痛感。不过,这幅完全不会引起城卫兵注意的乞丐形象也使他无需绕路或躲躲藏藏。
抵达神庙门前时,天空已经由橙红转向墨蓝。庙顶的后面,群星渐渐展露。阿密洛四下看看,一切都是老样子——没有运石车,没有拿鞭子的监工,没有木料也没有水桶,奴工、工程师、画匠、石匠也统统不见半个……简而言之,这附近除了他看起来没有任何人。应该是好消息,阿密洛琢磨,但也可能只是贝勒奈西还没来得及组织人手。
神庙大门上的浮雕彩绘似乎蒙了一层灰,且无卫士看管。战士荷拉吉斯所在的那半边门稍稍向里开着,露出一道刚好能容一人通过的缝隙。真是诡异。阿密洛咽了口唾沫,我不应该往里走。
他边这样想边从门缝间侧着身子穿过去。
外庭空荡得叫人害怕。高耸的祭台不见祭品,却有干涸的血迹。阿密洛留意到左侧供卫士们居住的营房前有斜着裂开的门板,像是斧子劈的。他往屋内瞥了一眼,没有活人没有死尸,连一样物件都没有,整个房间完全是空的。司乐们的卧房情况也差不多,只是这一次门板干脆都消失了,仅在门槛附近剩下一只被什么东西给戳了个洞的手鼓。
祭司们的居所在内外庭交界处,是两座东西对望的梯形建筑。阿密洛被发配蛇岛前就是住在西边这座,库卡斯和塞默则是一直住在东边……不对,是“曾经”住在东边。他们那天去了城外,结果再也没回来。
但大祭司还有其他弟子。
他抱着一丝侥幸查探了一遍东西两处的所有房间,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他们全都逃走了?难道他们完全不知道贝勒奈西究竟做了什么?还是他们已经全都叫贝勒奈西给杀了?
老师的遗体……恐怕还……
他筋疲力尽地在千柱厅最底层的台阶上坐下,周围只有来来去去的清冷夜风和安稳沉寂的大理石块。阿密洛用胳膊环住小腿,脑袋抵在膝盖上,使劲咬着嘴唇。猛然间,他竟有点希望从什么地方跳出些城卫兵或是一两个“风沙之子”奉着贝勒奈西的命令来抓他,仿佛那才是神庙内部该有的景象,而非司乐女孩奏起的美妙旋律、烟与香油交织的气息、祭司指尖纺织的迷幻光辉或老师行走时紫袍上颤动的千百个小银铃。
没有灯光烛火,神庙很快就会被黑暗吞噬。他不知道自己在怀念什么,是年幼时因生长在最接近诸神之处的自豪,是为与莎米恩会面悄悄溜出门时的愉快,还是练习咒语与赞美诸神之词时所体验到的兴奋和平静。到最后,他发现自己最怀念的是大祭司。他的指导,他的箴言,他不近人情却恩威并存的培养……
夜幕之上,群星俯瞰。他仰起脸,寻到几处星辰陨落后留下的模糊晕影。
为何黑暗之主的预言破灭了,世界却比先前更加黯淡无光?
破败王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即使作为兵器也想有个家
- “以自由为代价换取一个家,你愿意吗?”答应的毫不犹豫,也许真的孤单太久了。-----------------------------------“我不管你曾经是什么身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兵器。”
- 3.2万字5年前
- 行走在卡兰德大陆
- 这是一个考完高考的学生打发无聊时间的小说。不过此前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构思。大家看的开心就行,图个快乐ヽ( ̄▽ ̄)ノ
- 3.9万字5年前
- 修仙的都是什么沙雕玩意
- 一个欧皇一个脑瘫一个公主病一个喜欢女孩子的女孩子一只狼一个觉得自己是魔修的圣女一个画童一个说书的。。。天道:见鬼,为什么这年头修仙的都是一群沙雕啊!
- 12.1万字5年前
- 转生来到漫威的利姆露
- 额没啥好说的
- 107.1万字5年前
- 论养成的方法
- 作品修改中..........................................
- 0.0万字5年前
- 管理员游戏界闯荡实录
- 我叫夜宵,是社畜,也是游戏管理员,因为可怕的阴谋,我被吸入到游戏世界中惹!还变成了吸血鬼美少女!于是乎,如何回到现实中重新当一名合格的社畜便成了头等大事当平凡的夙愿与阴谋交织之时,挂比游戏管理员闯荡异世界的故事,在此展开!管理员的故事..
- 新书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