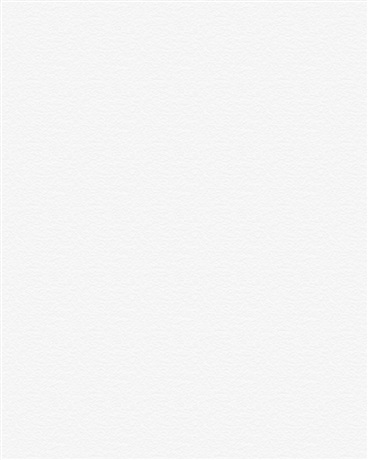木偶(在写了,都在写了,只是之前没什么灵感)
“阿嚏!”
我揉着拧得发红的鼻头,说南方的冬季不冷都是骗人的,我秋裤加棉袄照样被冻得清水鼻涕直趟,不过想来也是,毕竟魔法攻击不是靠纯靠护甲就能解决,正确的出装思路应该是死命堆血量。
额……似乎还是有些不对的地方。
罢了罢了,不要纠结那些有的没的,琉黎买得热可可再不喝就要凉了。
冷风里喝热饮是很舒服的,也许我可以换个方式描写:两个傻子大半夜站在楼顶天台找冻、还不关心身材走样大量摄入高热量食物。
但高糖份的食物的确很容易带给人简单的满足感。
那种热流从胃部扩散到四肢驱散严寒的感觉,还有大脑在高血糖浓度时带来的舒适感,无一不在告知我,糖——是种人类欲望的原始狂欢。
难怪大家喜欢将爱情的感觉比作像蜜糖一样甜蜜。
这样俗套的比喻往往最为贴切。同样,也最容易……让人失望。
琉黎你看啊!!
高台的风吹得我摇摇欲坠,十几层楼的高度说高不高,至少摔下去还是有些痛的,我挥舞双臂妄图找回平衡,但完全抑制不住自己下坠的势头。
看什么看,你重死了。
危机时刻还是琉黎跳上房檐一把拎住了我的帽子。她把我往后一拽,我就反方向摔了出去。这里就体现出猫妖的种族优势了,她踩在狭窄的房檐,柔软的脊柱让她能轻易调整失衡的重心,发达的前庭器官也让她可以在极窄的地形确立安全的落脚点。她扭过腰,单腿以不可思议的姿势立住,再旋转过身。
嘭!!!
我落地不会有这么大的声响,这是油罐车爆炸的声音,从楼底下掀起滚滚热风扬起她的发,还有随热风一起升腾起舞的光条,那是一根根莹绿色的枝条,从爆炸的火球里钻出来的枝条没有实体一般发了疯的生长,几个缠绕在一起就成了主干,随之幅照出一顶庞大的树冠!
你看!
这就是,我想要你看到的。
我摔在天台的地上,左胸胸口处的口袋滚出一只小小的白玉灯台。
灯台在琉黎惊疑不定的目光中升起并最终悬停在离她不到半米的空中,它旋转着放大,直至九寸高,七瓣白玉花瓣缓缓绽放开,七彩光芒一闪间把虚悬的参天古树尽数收进灯台,白玉的灯芯分泌出淡绿色的灯油,七瓣花瓣复又合拢,转出一朵莲华。
“琉黎你知道吗?没有人是救世主,那些自诩为是太阳的人都死了,但每个人又都是救世主,都背负着自己的小小世界,不是底线,却不允许他人轻易触碰。若一天它被损坏了,便把肉体和灵魂,统统燃烧给你看!“
今夜的风真大啊,我收起莲灯,起身看着一户户亮起的窗子,我和她站得那样高,本来零星的灯火沉浮在寂寥的夜景,就像寥落海景里的灯塔,而现在人们从睡梦惊醒,略矮几分的高楼灯火通明,似祭典时筑起的高台,挂满灯火晃晃的灯笼。
“玄冥陵阴,蛰虫盖臧,屮木零落,抵冬降霜……”
我想象着一个女人抹过五十弦的锦瑟,和着祭礼上恢弘的乐声唱着。拉近、再拉近,我想象中的视野越来越清晰,即将拨开雾气的那刻,我见到她凝脂雪玉般的肌肤迅速干瘪下去,枯萎皱缩,像烧焦的老树树皮,她的眼眶也冒出金色的火焰,很快就烧得一干二净,留下一堆乳白色的骨骼。
“我不知道,但我期待见到那样的一天。”琉黎似乎这样说道。
我看不见了,但听觉还很敏锐,所以我听得极其清晰,唯独不确定是不是琉黎在说话。我的脑子最近总是断片,脑子果然不愧是人体最不能轻信的器官之一,即便你不是脑瘫也容易因为脑残导致记忆缺失,就像我的记忆终结于三天前,这三天的记忆任凭我怎样回想都无法忆起分毫,难不成真是如琉黎所说,我吸笑气吸断片了?
想着笑气,口腔里就泛起干涩的甘甜,可雾也不是一氧化二氮,我猛拍自己脑袋,强制自己清醒过来。
雾?
雾……
将意识泡在牛奶般浓厚的浓雾里沉浸;
雾……
已经散去;
待她再次从梦境苏醒。
在那里,她又一次站在归属于原野的道路之上。
路面遍布着张开的豁口与裂纹,杂草顽强的从水泥地里探出头,而路边的路灯也早因常年的风吹日晒而显得那样的锈迹斑斑,有些更直接倒在野地,与泥土和缠绕在躯干的牵牛花藤共眠。
蚁群、飞鸟,一个盘旋在天空,同夕阳落下,蛰伏在西方的密林;一个绕过她的脚掌,像黑线一样延长,将草籽和蜷缩成球状的鼠妇送进巢穴贮藏。
在这里,现代与时间对抗,最后失落于时间的长河,一切都呈现出古旧的昏黄。
在这里,生命与死亡互露锋芒,她左手的枯木,漆黑而扭曲,右手的林子里,木槿花却开得正旺。
在这里,在她的梦里,在将生死分割的道路上,梦境的主宰目视周身笼罩不详的骑兵。
他跨 下的战马目露红光,雄健的身材上披挂严丝合缝的重铠。
骑兵踏着谨小的步子,缓慢也沉重。他逼近她,童话里也是这样描写,你看,骑士向着他的公主走去,现在他的使命完成了,我们可以把他送上绞刑架,他……可以去死了!
“你也是来杀我的吗?”
她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恰好可以看见极远端的地平线,还有即将完全落下的太阳,那象征着她将要熄灭的生命。
他并不回答,但他的战马行过的地面,被马蹄践踏过的车前草都像是被烙铁烙过一般,草叶子一半委顿下去,一半呈现漆黑的焦褐!
巨大的白色骑枪枪尖抵地,毒蛇般游行在并不茂盛的路边野草里。
他来杀她了,他的手掌因为兴奋而颤抖,他的呼吸粗重,甚至赛过骑枪挥斩时的尖啸,他的战马高扬马蹄,口中喷吐出火焰的烈马以两足跃起,帮助骑兵挥斩出圆转的弧!
她?
不,今天……是他要死了!
咣当!
骑枪格挡开劲射来的长矛,尚在抖动的骑枪被他抬至左肩,骑兵紧接着向第二根长矛投掷出去,他以马背为跳板,再次跃起的骑兵抓住第三,也是从黄昏的地平线射出的最后一支武器。
时间在这一刻定格,战马无声的嘶吼,下腹的肋骨刺破包裹腹腔的兽皮与甲胄,它浑身将要崩碎,黑色流水般的甲虫从裂开的每一个缝隙溢出,而骑士不顾一切,他要勇敢的去保护自己的公主,这真是值得嘉奖的勇气,可死亡从来就不是勇气就能终止的东西,想要终结死亡的唯一方法……从来都只有以命易命!!!
骨裂!
最后的武器沉重得超出他的想象,他的手骨已经折断,现在还抓在飞射的长矛矛柄之上——抓得死死的,即使没有血肉和肌腱,骨与骨之间也爆发出不输液压钳的力气,他妄图抓住希望!
是的,那是一支早已腐烂的手骨,现实也正按照我们一直所被灌输的认知中所期待的那样发展:希望终归只是希望,腐烂的,就该找个角落…独自腐烂!
他注定抓不住活下去的希望!
“嗯~接下来呢?”琉黎问道。
“接下来吗?”
我说着拾起马路边上已被烧焦的木偶,它落到人们围出的警戒黄线之外,之后我和琉黎隐入逐渐拥堵的人群,这时刺人的目光聚焦到我后背,口袋里的木偶也感应到了什么,一股温和的灵从腹部中脘穴汇入经脉。
我立了一刻,随后反问道:“你知道人偶最初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就像是巫毒娃娃一样,一两根草或木来构成,一缕发或者血来连接,最后再加上些许小把戏一般的干涉。”
我和琉黎走远了,救护车的警笛越来越弱,那刺人目光也再也感知不到。
“它们最初是用来挡灾的啊。寄托了施术者最美好的期望。请你一定要活下去……”
我用力地重复。
“请你一定要活下去。”
她说……雾……
“请你,一定要活下去。
他的声音让她记起许多回忆,那时她和他在树下,在火焰和群星里,她赌咒似的跟他许愿,她几乎快要哭出来。
请你……一定要活下去啊。
“所以你还是没告诉我接下来的故事。”琉黎抱怨道。
“接下来?接下来马匹踢碎了骷髅,半身截断的骷髅最终还是挡在她身前,用肋骨和仅剩的左手磨灭了神的审判。”
“真是个可笑的故事,充斥着名为生离死别的荒诞。”我说着摸了摸她的头,觉得手感不错,又摸了摸。
“所以送你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并不美观的木偶,琉黎接过,她脸色郑重,她明白这个木偶承载着怎样的一个故事。
修长手指抚摸凹凸不平的树木纹理,她最后用手帕包住了木偶,蒙上白手帕的人偶总让我想到一个成语:马革裹尸。
嗯,马革裹尸,我恍然间的有感而发,我又想到远处的悬铃木上挂着满树的反季绿叶,但那些叶子很快又会枯黄,生命再一次轮回,而它们只配化为腐殖质,为新的生命提供必须的养料......
有司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最强的我却不是勇者
- 和好基友攻略游戏时一个不小心到了异世界??好基友也不知死活???明明是最强的我却不是『勇者』职业?开什么玩笑!本书不定期更新,但是能保证每周最少两连更,保证不鸽(大概吧)X本书每周2,周4下午19-21点更新,每周保底两章,随缘..
- 6.3万字5年前
- 玉藻前奈亚子我的超能纪元
- 欢迎来到,超级英雄的世界。准备好成为英雄或者罪犯了么,还是说,准备好迎接死亡了呢?开玩笑,放轻松,本书没那么严肃!
- 4.0万字5年前
- 并不存在的幻想世界
- 【原作《限制级末日症候》,作者全都变成F,此本改文,不予上架,不做用商业用途,有必要会找原作者联系】
- 5.0万字5年前
- 从魔王城开始的异世界宅文化
- 你一票,我一票,明天魔王就出道!“偶像到底是什么?”魔王少女撒塔米娅疑惑的看着徐嘉艺。……“你说的对!萌就是正义!”洛姬雅抱着印有萝莉勇者身姿的抱枕,发出了「诶嘿嘿」的可疑笑声。……“这些东西真的可以让他们主动的献上灵魂吗?”大恶..
- 3.5万字5年前
- 举世莫敌一介醉仙
- 放过我了?哈哈哈……三年了……三年前他们诬陷我,追杀我,废我灵根毁我修为。我只是想当个凡人残喘此生,可他们却还是要苦!苦!相逼!现如今,他们怕了,他们担心了,他们……要放过我了?那好,那就去告诉他们,告诉整个修真界。来不及了,我要..
- 32.9万字5年前
- 安雾
- 这是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但是拥有魔力的安雾却成为了异端的存在。等待着她的究竟是什么命运呢?
- 2.8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