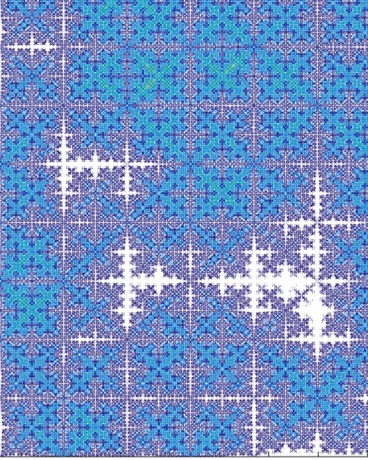停滞时空的诺言
起来,哥哥,这都几点了,起来吃饭!”萨娜咬着筷子,举着粉嫩的拳头,轻轻敲打在我多肉的躯体之上,细嫩白净的脖子上,镶嵌着蓝宝石的十字架在整齐的校服上轻轻摇摆。
“萨娜,再让我睡一会,昨天,啊~熬夜了。”我伸了个长长的懒腰,享受地躺在令人疲软的床上。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
“啊哈哈,哈,别别挠痒,我起来,我起来。”我慌忙起身,连忙穿上莫名其妙的长裤。
“那是什么?是不是晚上又偷吃零食了!”萨娜手疾眼快,将我下摆的裤子猛的一脱,当然房间里的声音,只剩下我惨绝人寰的喊叫。
“大晚上还吃烤鸡,世界上哪有你那么傻的哥哥,随便包装一下骨头就塞裤裆里,你是骆驼吗?”
“可是骆驼它位置……。”
“你还顶嘴!”萨娜双手叉腰,“谁每天给你做饭?”
“萨,萨娜。”
“嗯?”萨娜睁大她淡金色的瞳孔。
“萨娜-诺亚女士,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把那些骨头倒了进垃圾桶。”萨娜转过头笑嘻嘻的说到:“还困吗?”
“托您的福,不困了。”我又伸了长长的懒腰闭上双眼,靠在木制的窗边。
温暖的光线透过窗户的薄纱,清爽的风,略过我每一寸泛起鸡皮疙瘩的皮肤,窗外,标有艾斯特勒城辉的国旗随风飘扬,陆陆续续的学生漫步在学校的操场上,我无味咀嚼着微微烧焦的面包,落寞的看着远处温雅的女孩子背着书包慢慢走进教学楼。
“斯尔,你又在看漂亮女孩了,先把饭吃了行不行!”萨娜放下手中的碗,一脸鄙视的看着我。
“你煎的面包这么难吃,还不如买烤面包机呢。”我咕咚咕咚的喝了几口牛奶,啊,也是可惜了这牛奶,偏要配上味如嚼蜡的面包。
“不好吃就别吃,厨房柜橱有番茄酱,你将就着吃吧。”萨娜叹了口气,把擦拭干净的盘子放回消毒器中,“我先去上课了,你慢慢吃。”
“别啊,一起去多好,反正也是同桌。”我从柜中取出番茄酱,涂抹在面包焦黄的表皮上,这下好吃多了。
“正是因为这样才不一起去啊,我又不是兄腔。”萨娜从裤兜里掏出棒棒糖,剥着费劲的糖纸。
“大清早的,吃什么糖啊,和小孩一样。”我轻轻咬着指关节,看着忙碌的萨娜。
“不吃糖哪来的精神,”萨娜笑嘻嘻的看着我“今天的心情,是,香,橙,味,的,哦。”
“好好好,祝您一天愉快。”我抽出纸巾,轻轻擦拭着自己嘴角的番茄酱。
“我走了!傻子斯尔!”
“萨娜!你围裙没脱!”
“啊啊啊?”
“我看你才是傻子。”
萨娜脸微微发红,一边脱着围裙一边对我挤出两个字:“去死!”
“啪。”沉重的一声巨响,打碎了轻朦的早晨,我缠绕上的黑线耳机,收拾好碗筷。客厅上的画相,萨娜与我的虚假的笑容在塑料上浮现。在我和萨娜的肩上,附着着两只陌生的大手。
那是一个男人与女人的手,手以上已经被火焰化为灰烬,只剩下,剩下伤疤与被当做戒指的铁环。萦绕在我与萨拉的脑中。
3月28号,新纪年……几年了?
我写下潦草的日记,耳机在我耳旁轻轻咏唱,我思索着:现在三百二十几年了?自己对时间的定义,已经漠然了吗?
“现在,我多少岁了?”我自言自语到,轻轻咬着自己的指关节。
“18啊,自己的年龄都会忘,真是一个傻子啊。”
“18?”我歪着头,看着萨库拉,他的头发快要茂盛到能遮住他白净的脖子了。
“一个要长大的人,还在这叼着耳机天天逃避现实。”他拿出手表:“喏,新纪年322年,5月22号你生日啊,斯某人脑子什么时候这么不灵光了,变傻了吧。”
“已经322年了啊。”我无趣的撑着脑袋,喏,萨娜来了。”
“萨娜???我……”
“斯尔,放学还要去那破地方。”她顿了顿,“今天要早点!”
“打铃了,准备上课。”臃肿的身材,黄老猪上课没错了。
是他的话,就能安心睡觉了,早上的觉,就现在来补吧。
橘黄的阳光透过设有铁杆的窗户,蜷缩在我的脸旁,我闭上双眼,享受着眼睛与灵魂的交错所产生的恍惚之感。
我从昏黄的余晖中醒来,风,夹杂着多余的石子,扑打在我的脸上,奇怪,四楼也有石头吗?哪个缺德的瞎抛石头乱丢人啊。
我直起身,恍惚的看着离奇的世界。
这里,是哪?
废弃的大楼耸立在裂开的道路之上,正在腐烂的尸体随意的躺卧在燃烧的火焰旁。
我缓缓步行在失落的大街上,在一家店铺的标牌上,有一副残损的艾斯特勒旗标。
什么嘛,这里还是艾斯特勒嘛。
“前面的路为什么这么眼熟……”
正在腐烂的尸体,依旧躺在打碎的玻璃上,旁边的类似于油桶形状的物体,依旧火势不减,往前走去,依旧是那个带有残损国旗的店铺。
远处的炮火,慢慢侵蚀着艾斯特勒,不断的弧光从我的眼前爆炸,尽管我没有受伤,但还是让我不由惊醒。
艾斯特勒,什么时候参与过战争?
我向前奔去,穿过轰鸣的爆炸声,穿过一闪而过的军队。
面前,还是腐烂的尸体和燃烧的油桶。
军队慢慢聚集起来,他们穿过我看着一个不满10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哭泣着,怀里紧紧抱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借助最后一丝的昏黄的光芒,我看到了满身伤痕与血的我自己。
淡眉毛,轻微的眼袋下,有整齐的一条线……
我瘫坐在地上,脑子昏昏沉沉的,如同灌了浇水那般附着不清。
我,到现在,也没有迈出一步,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我的想象,仅此而已。
真正的我,睁着血红的眼睛,凝视着前方,渗出的血,染红了少年破旧的衣裳,手上的戒指,闪耀着黄昏的余光。
我强忍着眼泪,耳鸣蒙蔽了我的听觉,我看着稚气未脱的男孩,他似乎在说些什么,便抛下我,毫不犹豫地冲向向整齐的军队,凭借着他刚刚微微颤动的嘴唇,我好像明白了什么,血肉交错中,我终于明白:我无法再停留在这里了。
我的视角突然一片黑暗,无限坠落在黑暗中,失去重力的我呼喊着,可无论怎样都是无济于事。
“望远镜,万”我红着眼,哽咽着大声的向黑暗喊去。
“笨蛋,说话说清除点啊。”
晶莹的泪珠划过灰尘,带走了已经冰凉的血,久久停留在我的脸上。
“好像有一点痒呢。”
“斯尔。”
“斯尔!”
“起床了斯尔!”
仿佛被万物附着的我猛然惊醒,随即而来的,是一阵猛烈的咳嗽,
“咳咳咳咳咳咳,呕,咳嗯。”
面前是拿着红画笔的萨娜,面前的,还是那个熟悉的教室,窗外剩余的光辉,附着在我完好无损的手上。
“太好了。”若是面前没有这个看别人和傻子一样的两个人,那就更好了。
“是傻子吧,萨库拉。”
“是傻子呢。”
“被别人吓醒然后呕吐,这是傻到一种境界了吧。”
“原来,这才是血尘之泪啊。”我轻轻拭去眼泪,只是声音,还有些哽咽。
“斯尔,你是不是又惹别的女孩子生气了?”萨库拉装模作样的流出眼泪说到:“请您不要再留下饱含您每一滴感情的泪珠,这只会让你梨花带雨的脸庞更加的楚楚动人,啊,主啊,若是我因为我的错误而让一个女孩再次哭泣的话,我保证首先打湿的一定不是她的眼眶。”
“什么眼眶泪水的,乱七八糟。”
我看着萨库拉的头发:“你是不是带了假发,怎么长怎么长了?”
“啊?”
“我拉。”
“啊啊啊啊啊啊”
“啊。”
“斯尔,你干什么?很痛的。”
“你昨天的头发不是才快到脖子吗?嗯?”
“什么脖子?我一直这样啊,你怎么越来越傻了?”
我松开长发及腰的萨库拉,难以置信的看着他:“真的没有戴假发?”
“男孩子不能头发长吗?我都被我妈强行剃过一次了。”
“然后呢?”
“你骂我吴克。”
“……”
你上午不是还和我说话吗?说我虚度光阴的什么什么……
“我没有啊?你不是睡了睡了一天吗?”
我的凯亚耳机啊,我双手插兜,哦,还在。
我转过头,看着萨娜。
“死婆……啊,好痛。”我脚立即被萨娜蹂躏着。
“哥,错了……”
“干嘛。”萨娜吃着棒棒糖,一脸漠视的看着我们俩,只是她的鞋子,依旧踩在我的旧运动鞋上。
“你早上吃过的棒棒糖,是什么口味的?”
“你想吃?”
“吃那个干嘛,问你啊。”
“那请你态度再好一点点好不好。”萨娜加大力度,扭踩在灰色的网布上。
“疼疼疼疼疼,我错了。”
“嗯?”
“哥”
“柠檬味的。”知道了又怎样,我房间里还有两箱,就不劳烦你买了。
“呃……”
“怎么了?斯尔?”
“今天是几月几号?”
“11月17号啊。”
我掩饰着眼中的恐慌,佯装正常的语气对萨娜说:“我昨天吃了炸鸡吗?”
“你不是说减肥的吗?孩子傻了,没救了。”
我,身处何方?
这里,真的只是白金之都艾斯特勒吗?
“斯尔,发什么呆呢,奈加等着我们呢。”
“他……找。”
“啊?”
“没事。”
“你怎么了?不会真的有事吧?”
“不,只是没睡好。”
我没有死亡吗?上午的萨库拉,不是说今年是新纪年322年吗?
穿心的痛苦,缓慢映射在我的心脏上,四肢酸痛无比,如同被血液侵蚀一般。
眼睛,有些发花呢。
我喘着粗气,忍受着压抑的痛苦。
奈加,不应该是奈加吗?那在那个无法改变的梦境中,为何要举起那罪恶的刺剑呢?
我们穿过充满杂草的树林,在后面,有个隐蔽的扫帚间。
萨娜向值班的老师挥手致意,远远的,教师也点了点头。
打开吱呀作响的门,萨娜推开多余的扫把,打开被扫把埋没的地窖,跳了下去。
还是没变啊,从来到校园就一直这样。
那么,为什么,奈加会变成杀人犯呢?
面前,是肮脏的臭水沟,而奈加的检查室,就在学校厕所的下面。
“一如既往的臭,每天都要经过这,感觉都要疯了。”萨库拉捏着鼻子,小声的说到。
“熬都熬过3年了,你的脑子也差不多是屎了。”萨娜嘻嘻笑着,推开了演装成高压室的暗门。
“奈加!是我们!”萨娜轻按门铃。
“找不到对象……”
“这傻子天天就知道逗我们玩。”萨娜又按了一遍门铃。
“早生贵子!”
“我想把这破门砸了,吃我一脚。”
当萨娜0.0001秒伸出她那能把我屁股打肿两厘米的神腿踢向正在给我们惊喜的奈加先生后,我就知道。
这腿子踢到的,无论如何都得是人。
“噗,哇。”
“飞出去四米了,新记录诶。”
“那是斯尔比较胖吧。”
“请,请进,请下次踢人轻点。”
我们抚摸着精致的木扶手,台阶旁的透明壁橱上,摆放着不菲的标本:地球时期的知更鸟,诺泽内亚时期的翼蜢,以及卡罗乌兹的聚压龙幼崽。
“好,好漂亮。”
“再怎么样好看也是标本,灵魂不屑居住在内。”奈加转过身,“温雅,接客!”
“你这说的怎么怪怪的。”
“有什么不好的嘛,大生物家。”
“不要说这个事啊,好羞耻啊。”我挠着发热的头皮,不好意思的嘿嘿笑着
“哈哈哈哈哈,老子的梦想是娶老婆生孩子,我奈加,是为了欲望而诞生的男人。”
他兴致昂扬的喝完桌上的咖啡,从他扭曲的面部看,温雅姐的泡咖啡技术依旧没有进步。
“房间深处走出甜美文雅的成年女性,纤细的腿却不止如何安放,身上穿的仅仅是奈加强加的学生服和白大褂,不安的大眼睛有些飘忽,微微发红的脸照耀在她略显青涩的脸上。”
“你解说个什么劲,那是你女朋友。”我转着头发,看热闹不嫌事大地说着
“那两小屁孩交给你了,我掳走这个。”奈加嘻嘻笑着,按住我的手,朝房间拖进去。
“啪嗒”
奈加关上门,摆弄着桌上的人体木雕。
“斯尔,你认为,谎言,是依附什么而存在的吗?”
“依靠条件吧,大概。”
我看了看墙上的时钟,
“新纪元325……年。”
也就是说,我莫名其妙失去了人生的三年,在奈加的刺剑上。
而死不成的我,必须忍受着时不时心脏的刺痛与四肢的灼痛。
“这真的糟透了,简直比拉肚子憋着还难受。”
“谎言,无论出于何时何地,都必须要依附利益,你赚了,他亏了。”
他拿出桌上的沙漏,“沙子便为利益,谎言便为容器,当互不吃亏”,他侧放沙漏:“若为这样,却违背谎言的原则,因为无论如何,没有人吃亏便无法构建谎言,那么当你为了别人而去掩藏撒谎,错的,又到底是谁呢?”
他泡了一杯浓浓的咖啡,送到我的手旁,我轻尝一下,啧,好苦。
“苦吗?我放了两袋咖啡粉。”
我点了点头,这么又苦又涩的咖啡,虽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再次触碰时肯定还是会让人浑身一震。
“我伤心的时候,会沏一杯浓茶或者磨研咖啡豆,苦难与悲剧总是让人感慨与成长,但失去希望的人遇到悲剧,只是会变成自己堕落的借口而已。”
“因为,我要结婚了。”
“温雅……”
“嗯,确实是温雅,我喜欢她,喜欢……她泡的苦的要命的咖啡。”
“我希望你们能祝福我们,但是我父亲不允许。”奈加坐下来,隔着窗户看着隔壁的房间,可能是在想检查工作进度吧。
“所以,我希望你活着。”
“诶?”
“还没发现吗?”
“怎么会……”
“你的头发在成倍生长啊。”
我摸着自己愈发纤长的黑色头发,指甲已经长到无法诉说的程度。
“这里,已经是艾斯特勒最后的堡垒了,凭你我的身份,出去就等同死亡。”
我明白了,为什么,就只有我们三个学生和一个老师。
全部都不见了。
“那,那为什么!”我抱着头,轻声啜泣着。
我,又要再死一次吗?
奈加擦了擦镜片,冷漠地说着:“我的父亲,奈亚,开国之士,参与了“雨衣”革变,代号为“新生”在最后,无法参与人类世界运作需要的都要回归自然,便为苦难的死刑。”
“为什么……”
“人类的罪伐,再一次演绎在距离始源之地几千亿光年的卡罗乌兹中。”
“虽然我尊重人权,但是我还要保护你们这些余孽的后代!懂吗?我爸,我爹!指着我鼻子骂,我们这些擦屁股的要保护这个星球的未来!擦干净那些老祖宗的污秽!”
“那些罪恶的道德消费者,破坏环境的始作俑者,指责着我们封疆于此的后代,指责着我们为什么没给他们优渥的生活!”
地面猛烈震动着,流泪的奈加,靠坐坐在柱子上。
“老子,早玩够了。”奈加吸了吸鼻子。
“我不去哪了,我不当“洗礼”者,我要和温雅死一起。”
“所以,请你再去挽救我们,拯救这个艾斯特勒,好吗?”
“为了那些无辜的人们,请不要被他们抓住,好吗?”
我吸着鼻子啜泣着:“我,我做不……”
面前,是向我跪着的奈加,他的头重重的扣在颤动的地面,微微发颤的地面,奈加的眼泪滴落在抖动的地面上。
温雅从房间出来,旁边是泣不成声的萨娜与萨库拉。
“为什么?”
“哥,不需要勉强,难过哭出来就好了,我们是一起的呢。”萨娜的十字架,在警报灯闪烁的红光下闪闪发亮。
“下次,我请你三年前欠下的烤**”萨库拉嘿嘿笑着,看着泪流满面的我“那味道太难忘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吃一次呢。”
“斯尔君,加油哦。”
“你们……”
“我答应你,你们,拯救你们。”
地面隆隆的响着,耳边,是岩石被崩垮的声音。
“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就交给那个老头子说吧!”
“我……”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剩余的意识间,我知道了奈加所说的一切。
疼痛,逐渐消失,蒸发于阵阵发鸣的脑袋之中。
“奈加,你丫,暗算,我。”我倒在地上,昏昏熟睡过去。
“该说再见了,斯尔。”
簇拥的五个人抬着着斯尔进入保护仓,没有悲伤与埋怨。
只有理解与包容。
“完成了呢。”
“接下来该干什么,奈加长官?”
“我们就,再睡最后一觉吧。”
最后崩垮烧焦的实验室里,有一个保存完好的标本。
那一个知更鸟的标本,久久的,凝视着燃烧的天空。
“这是约定,说好了。”
少年从无尽的黑夜苏醒过来,双手,支撑着荒芜的街道。
“你看到了吗,世界的崩坏。”
“正在我眼前闪耀呢。”
耀械之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我只是个挂名执剑者
- (可能有人觉得字数少所以不看,不用担心会进宫什么的,作者在起点的两本书全部签约并且累计六十多万字)“执剑者什么的,我才不要,还是戏丧尸娘还有妹子有意思~” “首领说,只要你同意,事成之后,送你世界上所有..
- 1.5万字5年前
- 征服者之异界女王
- 我们的主人公叶良在修行星发动机的时候意外牺牲,他本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但是上帝在给了他一次新生,并给了她一个系统,看她如何在异界称王,并寻找回到原来世界的方法,重建人类文明
- 5.5万字5年前
- 散轻聚叶
- 不太严肃的·真·短篇/微科幻合集,具有类似的或同样一束世界观的。(只是羞耻的自娱自乐,笔者不是写东西的料(º﹃º),再过好多年说不定能拢在一起??)
- 2.6万字5年前
- 机甲战姬第六季
- 机甲战姬第六季这是一个普通的少女和一个人工智能的故事....
- 1.7万字5年前
- 总督小姐给的认怂书必需签
- (先明目张胆的求个收藏)一个未知文明的出现,改变了我和周围所有人的生活,让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不过,我想,只要有我们强……无敌的总督大人还在,身边的一切都会变好吧?这..
- 2.2万字5年前
- 异種
- 原名《异种》,那个種是“种”的繁体字,因为在创建时发现这名被用了,搜索后又找不到作品,一想应该是之前我在创建时挪用的……嘛!总之就是《异种》啦这是一个一群怪物被接纳和被爱的故事
- 新书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