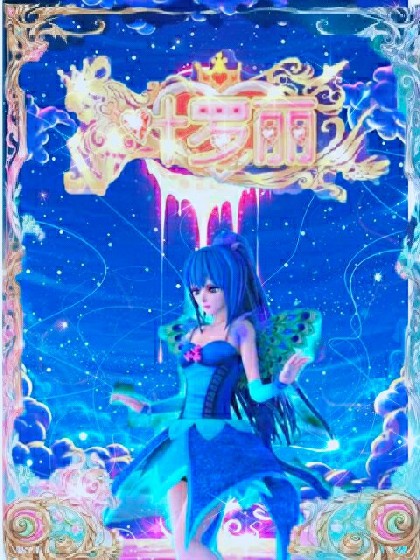2
在他刚被束缚住的那些天,凭借着对于他祖先那幼稚的信赖,他转而试图喜欢上那些文雅温和的教会信仰,因为这些伸展开去的神秘大道曾许诺他能逃避那俗世的生活。但只有当他接近这一切时,他才留意到那些空洞的妄想和美丽、那些陈腐乏味的平庸、那些看似智慧的庄重以及那些所谓的坚实真理——他看到这些令人发笑的主张让人厌烦地支配着它的大多数传道者的言行;他感到这里面满是笨拙和不雅——虽然它原本应该充满活力——那就好比是一个原始物种面对未知时恣意生长的恐惧和猜疑。而当卡特看到那些故作严肃的人们努力试图将那些古老的神话——那些每字每句都与他们那狂妄自大的宗教[8]相驳斥的神话赶出这俗世的真实时,他感到了厌烦。这种不合时宜的严肃抹杀掉了他仅存的最后一丝信赖。因为这些让他们感到满足的古老信条只不过是为了给他们那宇宙奇想的真实外貌提供一些洪亮的仪式和情绪上的出口而已。
但是,当他开始学习那些已经抛弃掉这些古老神话的人们时,他意识到这些人甚至要比那些紧抱神话不放的愚民更加丑恶。他们不知道美的本质在于和谐;也不知道在一个漫无目的宇宙里,生命是否美好本身没有任何标准可言——它只能与梦境以及早已消逝的情感协调一致,以及盲目地塑造那位于混沌之外属于我们的小星球而已。他们看不到善良与邪恶、美丽与丑陋只不过是由不同观念结出的只具修饰意义的果实而已——这些词句唯一的价值在于它们联系着那些引发我们祖先思考和感受的事物;甚至对于每个族群每种文化来说,在这些问题的琐碎细节上也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相反,他们要么完全否定这一切,要么将这一切看成是那些与生俱来的、模糊本能——那种他们与农夫、与野兽一同享有的生物本能;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在痛苦、丑恶和矛盾中继续令人厌恶地拖延下去,同时还能让自己满怀一种荒谬的自豪,认为自己逃离了某些不洁的事物,可事实上这些事物绝不会比那些仍掌控着他们的东西更加不洁。他们用那对错误神明们的恐惧与盲目虔诚换来了那些放纵和无人管束的混乱。
卡特对于这些现代的自由大多浅尝辄止;因为它们的肮脏与廉价让一个仅仅只热爱美的灵魂感到嫌恶。然而他的理由却为那些浅薄脆弱的道理所抵触,因为它们的拥护者一直都依靠着这些肤浅的道理以及一份从那些被他们抛弃的偶像那里所剥离出的神圣意义来粉饰他们自身的动物冲动[。他看见他们中的大部分,和那些他们所鄙弃的神职者[一样,无法摆脱同一个错觉——他们同样认为生活,除开那些人们所梦到东西之外,是暗含着某种意义的;同样,他们也无法放下那些不属于美的、有关伦理与责任的幼稚概念,甚至当这个世界借由所有他们得到的科学发现向世人尖叫着它既没有意识也客观地不具备任何道德情感时,他们仍拘泥于这些观念之中。通过执迷和扭曲那些有关公正、有关自由、有关和谐统一等等先入为主的错误信仰,他们抛弃了那些过去的传说与学识,抛弃了那些过去的信仰与道途;却从未停下来反思那些学识与道途正是他们当下思想与判断的唯一缔造者,也正是他们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宇宙、一个没有任何固定目的或是任何稳定而又可供参考的观点的世界中的唯一标准与指导。失去了这些人为的规定,他们的生活逐渐开始缺乏方向与生动的乐趣;直到最后他们只能努力让自己沉溺在对于那些忙乱与所谓的价值、那些喧嚣和兴奋、以及那些野蛮的炫耀和动物感官的倦怠中。当这些东西变得乏味、变得令人失望或是经历过某些情绪剧变后变得令人作呕时,他们转而开始冷嘲热讽、制造苦难、挑剔社会秩序的毛病。他们从未能认识到自己那毫无理性的本性就如同他们先祖的神明一样易变,一样充满矛盾。他们也从未能意识到“福祸所倚”的真谛。永恒的美仅仅只存在于梦境之中,可当这个世界在它对真实的盲崇中抛弃了童年和天真所蕴含的秘密时,也一同抛弃了这最后一丝安慰。
在这空虚与纷乱的混沌中,卡特努力试着如同一个有着敏锐思想和优秀血统的人那样生活着。随着他的梦境在年岁的嘲弄中逐渐黯淡褪色,他开始无法再相信任何事情,但对于和谐的热爱使得他依旧保持着与自己血统和地位相称的风度。他木然地走过满是行人的城市,发出一声声叹息,因为没有什么图景看起来是完全真实的;因为那金黄阳光洒在高高屋顶上的每道闪光,那投向夜幕里华灯初上的雕栏广场的每一瞥都仅仅只能让他再度回忆起那些曾经有过的梦境,仅仅只能让他思念那片他再也不知道如何去寻回的奇幻之地。旅行就像是个笑话;甚至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几乎未能波及到他,虽然在一开始他还是加入了法国外籍兵团。有那么一会儿,他找到了朋友,但很快又对他们那粗燥的情感,以及他们那千篇一律而又世俗的梦境感到腻烦。当他所有的亲戚开始疏远他,不再联系时,他甚至感到了一丝模糊的欣慰,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他的精神生活。只有他的祖父和叔父克里斯多夫能够理解这一切,但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
克苏鲁神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叶罗丽之思思黑化
- 简介:曼多拉被打败后,人类世界与仙境平静了许多,却出现了新的对手,那是一团黑气,它可以附体,可以给予人黑暗的力量……
- 12.1万字5年前
- 关于bug我也无能为力了
- 末日已经过去了几百年。,而人类似乎忘记了什么?不管了,就连我也懒得去提醒他们……他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 1.0万字5年前
- 姐上全是弟宠的我该如何是好
- 生在神宗,可贵为继子的楚江离生活却过得并不愉快。而四个性格不同的姐姐,则几乎把他的童年弄得是苦不堪言。两人常年的撕逼加暗斗,一人黏人得烦人,另一人则是哄不好就要哭的家伙。好不容易借着她们成人礼那天逃离出宗,却又想起与隔壁宗派某女孩的莫..
- 2.3万字5年前
- 一个正常的精灵弓手
- 啊我死了,但我又活了,总之,很乱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怎么了・_・?
- 8.8万字5年前
- 只剩小命一条的头疼冒险记
- 遇难,失忆,身无分文的平凡少年流落到了连语言都不通的异国他乡。可谓只是表面上活着。人生本艰难,何苦还为难?不过,如果就这样轻易的GG,那就太无趣了,您说是吧?
- 1.1万字5年前
- 堺命
- 简介:一界之内,万物众生。谁在颠沛流离,谁在生死相守。方平:“曾经我不知道,现在我只想守护我要守护的人”。刘子云:“曾经我也不懂,如今我只想走遍千山万水”。
- 13.5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