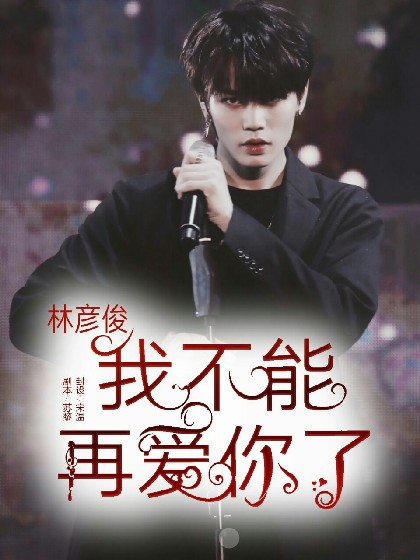番外(与正文无关)
七
复仇是一颗种子,野心和偏执只会为它提供肆虐的土壤。他处处觉得不公,活着只是不快活。他天生厌恶着贵族的一切,得到手就毫不犹豫地摧毁。这样的人记不清什么恩德,唯有嫉妒和怨恨才能撐着他活到现在。
傅家造就了他幼年的不幸,而余家也当仁不让地给过他最恶意的羞辱。余老爷的垂青不会成为他善罢甘休的理由,他受过的苦难无法偿还,野心无处宣泄,一个傅家的毁灭填不满他的意难平,他迟早会将刀子对准余家。
果不其然,在政府任闲职吃空饷的几位余少爷挨个被揪出,陆续锒铛入狱,余老爷听闻消息当场中风,阖家乱作一团。但再乱,也仅限于公馆的其下四层,顶层一如既往地被妥善隔绝,一派宁和平静。
但总有百密一疏的时候,是从前在牌局上恶意嘲弄他的大嫂,竟能瞒过看守溜到了顶层。当他回到家中,就见这位总爱穿华贵的电光绸,单凭锋利指甲就能将丈夫偷吃过的小丫头抓得血肉模糊的厉害贵妇披头散发、形同疯魔地扯着余沥的手,卑微至极地跪在地上,哭着求她救救长兄。
连缬冷静地叫人将她拖走,回头再看瞳孔无光的余沥,还能若无其事地轻声过问她的饮食和睡眠,又问她近来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他习惯了她的沉默,看到她莹润的颊上隐隐有一道泪痕,下意识地拿手去抹。
她却蓦然尖叫一声,挥开他毫无防备的手,退到床沿紧抱被褥,泪水流得无声却惨烈。他不敢再靠近,后撤到门边又回头看了一眼,连关门都像是怕吓到她,一粒尘埃都不敢惊动。
七姨太翠屏在厨房百无聊赖地切着冷火腿,回过头时吓了一大跳。她强压自己紊乱的心律,只向来人嗔道:“姑爷沉下脸来真是怪可怕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杀人呢。”
“大嫂是怎么溜进了顶层,还有转告傅家倒台的事。”连缬笑了一声,“我手底下的人命债有多少,你不是最清楚吗?”
翠屏确实清楚。他们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贫民,在最冷的寒冬抢过一张漏风的草席,也在大兵拿尖刀驱赶的时候互相掩护。翠屏至今都记得他第一次杀人,是为了给庙子巷修鞋的老师傅报仇,那年他大概十七,稳稳刺进军官体内的刀却狠得不得了。
后来他跟着一群恶徒离开,而她被卖进余家当了七姨太。她也曾反抗,宁死不从,终归还是被驯服。昔年遭受毒打的皮肉伤早已愈合,恨意却在心底反复结痂溃烂,所以多年后当连缬提出要进入余家,她只觉得天赐良机,几乎是立刻就同意了。
如今再看来,却不知究竟是谁利用了谁。
“是,都是我同余沥说的。丈夫在外头如此有能耐,妻子哪有浑然不知的道理?”她破釜沉舟地抬头回应他的胁迫,“当初咱们说好,我助你夺权毁了傅家,作为回报,你就要替我将余家清理得干干净净……”
他撇过头,极不耐烦地打断她:“所以我不是正在践诺吗?”
她险些失笑:“以你的本事哪至于如此,余家早该一个喘气儿的都不剩了!”她越说越激动:“如今我甚至怀疑,你报复傅家的动机压根就是编出来的。傅氏家主根本没有悔婚,没有侵吞乌氏的家财。你只是爱而不得,只是嫉妒傅长临。”
她等着他反驳,或者给她一掌,吼着要她清醒点,可半晌后,他如释重负地承认:“……总是瞒不过你。”
结果成了她气急败坏地迎上前,狠狠抽了他一个耳光。他也不避,抖着肩竟是低低地笑出来,然后伸手揩掉嘴角溢出的血渍,浑然不觉地擦着她的肩头离开。
八
入冬之后,余沥终于病倒。她的母亲怀她时并未养好身子,她有着生来的寒症,却因父亲长年的忽视贻误了治病,如今家中变故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切都来得措手不及。
连缬为她请西医,请营养师,可情况没有好转。她自己浑然不觉,或者只是了无生念,他坐在餐桌一旁紧盯着别人喂她吃饭,她都会乖乖地咽,然后一扭头就尽数吐了干净。
最怕的就是月中,他照例熬来红糖水,可她依旧不肯喝他递来的任何东西。这回他终于忍无可忍,撬开她的牙关就灌进去。谁知液体自齿间漫过,又从她的眼眶涌出,他惊慌失措地眼看她泪流满面,颤抖着一把捧住了她的手。
“是我错了,都是我的错。”她轻微地咳嗽几声,没得到回应,便自顾笑起来,“如果我死了,你放过我的家人,好不好?”
她哭得乏了,只又合上眼去,有冰冷水珠顺着她瘦削的腕滑下,悄无声息地浸洇在蚕丝被里,像滚落深海的一粒珍珠。未知来处,没有去路。
气候转暖的那天,他给她带来了新一期的月刊《奔流》和香奈儿的五号香水。他总是做着这些徒劳的努力,然后在她长久的沉默中满面微笑地提及天气冷暖、季节更迭。
“原来溧水河岸的花都开了……”她居然开口,他激动得屏息,全神贯注地听她继续说道,“我想去看看。”
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又稳又软的轮椅,在日光最盛的晴天推着她出门去看花。走到半途又怕她冷,遂脱下外套将她盖住。她的肤色在盛放的万千花冠下呈现出一种脆弱的苍白,眼眶却慢慢红了。
“我母亲从前是余家的花匠,她能将花养得很好。听说父亲就是因为这个,才娶了她当第三房姨太太。”
他半蹲在她身侧,昂首含笑聆听,有风袭过,细雨琉璃丝般垂在河面,衬着一汪碧水统统折进她眼底。饶是他闭上眼,依旧目眩神迷。
“但是后来,母亲不慎养死了一株花,父亲大发雷霆后就将她废弃。母亲走的时候我两岁,已经记不清她的模样了,也不晓得那究竟是怎样的一株花。”
“乌莲。”他搓热了掌心,将她发冷的手指拢住,迎上她困惑的目光,又笑着复述,“是乌莲花。”
看完花,了却心事,回到家后,她竟出神地勾起嘴角,他不记得有多久没见过她这样笑。就像从前的无数次央着自己出门带些小玩意儿一样,她忽然说想喝解酒的清茶:“就和先前那夜的一模一样,好不好?”只为这久违的笑颜,又有什么不能答应?
那种药粉无味无痛,并不容易拿到手,但他向来有门路。一番折腾过后夜色已阑,他捧着热茶走来,将她温柔地拥入怀中。她终于愿意喝下他递来的东西,还喝得一滴不剩。他觉得满足,折腰点了盏煤油灯,坐在小凳上细细地为她擦鞋。
这是最后一次了,于是她静静地看着,没有出声打扰。
斗罗:冬雨半夏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查理九世之墨晓雪
- 简介:对不起,如果不是我,希燕姐姐也不会石化……(墨晓雪)多多,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件事?(DODO冒险队)“雪,我喜欢你,你知道当我知道你成为了浮空城执法长老时我有多想灭了浮空城吗?我放在心尖的人竟然让浮空城如此轻松就拿捏住了性命。”(晴空焰)“雪,等你醒来我们就订婚好不好?”(唐装少年红着眼睛望向正在吸氧的银发少女。)“队长,我一定会达到治愈系圣灵阶的。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希燕)“呵,晴空焰,你究竟想怎么样?我累了,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是雪渊!”
- 3.7万字5年前
- 斗罗大陆之永恒传说
- 简介:(禁止抄袭)一切是命运,还是阴谋!龙神鸣,阴阳破。万物法,生命线。星辉现,永恒护。一切都只是开始,永恒之光的守护,永恒传说才刚刚开始。真的只有爱才是真正的永恒吗?永恒的命运又当如何艰辛,真正的永恒到底是什么?
- 7.7万字6年前
- 陪你到世界之巅:初恋cp
- 简介:我拼了命的努力是为了最初的梦想,可回过头才懂一切美好皆不及你,却是美好可及,你不可及…♡季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天空之外”以你之名,为你而写寄托着我的情感。──初恋cp──
- 2.7万字5年前
- 林彦俊:我不能再爱你了
- 简介:林彦俊这辈子最痛恨的女人是顾漓月,这个女人,心计深重、城府颇深、手段百出 顾漓月惨然一笑“你怎么才会爱我?”林彦俊只是嘲讽“哪怕你死了,我都不会爱你” 后来,别人都说顾漓月那个女人死了 该死,他居然好像有点喜欢上那个女人了?
- 2.6万字5年前
- 斗龙战士之圣龙世界
- 简介: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中的圣龙世界,龙王降世,连接人类世界和圣龙世界。
- 3.3万字5年前
- 朔朔长歌
- 沈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轰了出去,这乱世容不下懦夫,更容不下女人,她命贱如草芥,却偏偏不甘心就此沉没在这荒唐乱世里。一次阴差阳错的相遇成为了她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她第一次对这人世有所牵挂,有所愿求,可命运从不放过任何人,当昔日爱恨早已翻天覆地,她是否还能坦然面对自己当时的那颗初心?
- 11.4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