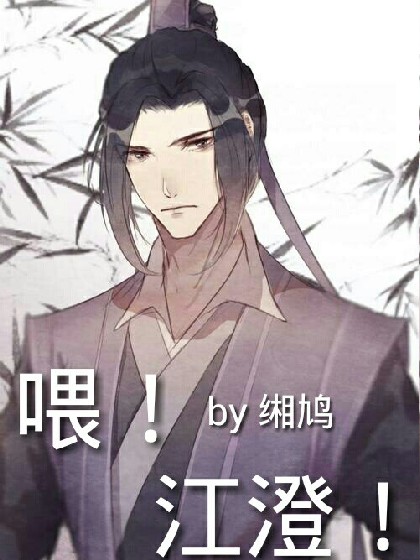第十七章 天地如栋宇
又七日,师兄寇谦之空着手来跋涉来到静室,见拓跋楠浑身精赤地盘膝坐在台阶上,脸上更瘦,晒得有些黑中透红,神情似笑非笑。
“你这样,就不怕来的人是位师姐或师妹?”寇谦之稍微诧异,避开那拓跋楠脐下那如怒蛙耸翘的所在,又忍不住专门瞧了一瞧,揶揄地说道,“餐风饮露也能这样,你的精气可真够旺盛的。”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你何故钻入我的裤裆?”拓跋楠轻轻吟道,这是近代刘伶的名句,但他神智清醒,并没有饮酒。
“你什么都没带来?”拓跋楠皱着眉头问。
“没有。”寇谦之鼻子里哼一声,左看右看,在静室角落找着拓跋楠的袍子,捡起来丢他身上,“快别疯魔了,我奉老师父的命,来接你回洞府。”
“有事?”拓跋楠一惊,一跃而起,几乎跌倒。
“有事。”寇谦之转身快步走出拓跋楠的裤子,站在静室外,“你快点儿。”
拓跋楠穿好衣裤,出门和寇谦之并排走,“是什么事?”
“我怎么会知道,只是老师父吩咐我来接你回府,有什么事自然是他亲自跟你交代。”
“哎呀,你等等。”拓跋楠挤眉弄眼说道,冲去静室后一个小山坡上,快快活活地屙了一回,在山泉下饮水,爬上树摘了几十枚青青的李子包在袍子下摆里作食物,跟寇谦之一同下山。
下山道路极险峻,两人小心翼翼,都不怎么说话,下了山再往戏浮山主峰山腰去,有了路径两人才话多起来,聊几句在静室里独处时的情形之后,拓跋楠忍不住问:“寇师兄,关于合气双修这个法门,你怎么看?”
寇谦之吹了个口哨,却没立即回答,往前走了一会儿才说道:“我想那差不多算是邪魔外道。”
拓跋楠听得出寇谦之语气里的愤懑,心有戚戚,又试探问道:“可这就是本门的修炼法门,老师父以下,似乎有不止一位师叔在修,还能说是外道么?”
寇谦之连连摇头,叹息两声,说道:“有不少本门位高的人在修,就不是外道了么?”
“卫师姐……”拓跋楠踌躇了一下,还是接着说下去,“听说是被选中和江师叔合气双修了么?”
寇谦之先点了点头,惊讶地站住看向拓跋楠,“这是近来的事,你怎么知道,是严可给你说的么,你们怎么会说起这事?不对啊,上次他去的时候这事还没发生呢!”
严可是前一次去静室给拓跋楠送水送食的师弟,才十四岁,什么也不懂,什么也没说。
拓跋楠说出卫师姐这三字时便没打算含糊地隐瞒,见寇谦之问起,便把那日卫瑄来到静室将自己推倒求欢的事说出来,后来自己坚决拒绝也说了,“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对还是错。”
寇谦之听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神情复杂,用力推了一把拓跋楠的肩,不满极了,“咳,你这人!”
“你觉得我做的是对,还是错?”拓跋楠觉得这话说出来好像在炫耀似的,他一点儿也没这个意思,或许根本就不该问。
“我怎么会知道!”寇谦之废然而叹息,似乎有极大的不甘,“前几天她才行礼入了江师叔的房中。你知道吧,江师叔已经有三名御女,又点名要了卫师姐,这哪儿是修行,明明就是淫邪之人设法给自己纳妾纵欲,却冠以堂皇的理由,霸占同门女子,让教团蒙羞,这实在是可恨极了!”他说得激动,愤愤然地一跺脚。
“那该怎么办?”拓跋楠问,他心里有些迷糊,不确定寇谦之是为卫师姐觉得可恨,还是为这种修炼法。
“现在没办法,只能听之任之,待我辈年纪增长,成了正一道的主干和栋梁,首先自己不采恶法,其次想办法在制度上革除恶法,这才是奉道信教的正道。”寇谦之语气平静了下来,也坚定得多,轻轻点头自勉,对拓跋楠说道:“你也会这样,对吧?”
拓跋楠轻轻地嗯一声,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既安定,又欢喜。欢喜的是他这辈子头一回意识到这世上有什么是不对的,不是存在着的就合理,也有存在的不合理之事,一定要有人站出来设法改变才行,这是人之为人的意义。
随即他觉到了一丝悲哀,因为在事情变好之前,卫师姐已经被牺牲了。以及他自己,明明可以做点什么却逃避,忍看着卫师姐坠入深渊,现在已经改变不了。
“我该带着她一起逃走。”又走了几步,拓跋楠忍不住说道,就算那晚上他不和她发生些什么,还是可以带她离开戏浮山,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如果是那样,你今天就肯定不在静室,我找不着你,没法带你回报,老师父要给你交代的事也就无从说起了。”寇谦之冷笑着说。
老师父要交代的事可能很重要,也可能不足轻重,拓跋楠心想。他上山时还年幼,对山外面的事情几乎一点记忆也没有,不知道在外面如何生存,这是他拒绝卫瑄的根本原因。
“寇师兄,如果卫师姐找的人是你,你又会怎么做?”拓跋楠冷不丁地问。
“大概和你的做法一样,不会更高明。”寇谦之沉默了一下,说道。
这话让拓跋楠稍感安慰,寇谦之由是感慨不已,一路又说了许多他觉得当前正一道教团不妥的地方想要改变,他有许多计划要一一改变,拓跋楠既没这个志向,也没什么感受,听而不闻。
他们没由崆山洞府正门而入,而是由一条隐蔽的山道直达后山成公兴的居所,这样不必遇见人。成公兴见两人来到,招呼拓跋楠坐下,让寇谦之去请寓所客人前来。
只剩两人之后,成公兴仔细地端详了许久拓跋楠,叹息一声,开口说道:“我还以为这事不会再有波澜,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今日我竟然要做这样的事。”
拓跋楠一沉,说道:“老师父,我不怕,请你直说!”
成公兴轻轻摇头,神色忧愁,“你和谦之本来是我最得意的两个弟子。你天赋异禀,体质上最适宜修炼本教的术法,假以时日必有大成;如果说本教术法修炼到最后真能成仙,我想那个人多半就是你。谦之志不在出世,而在入世,入世就违了修行的根本,而是原君往前搞的那一套,我担心他未来会闯下不小的祸事。”
原君就是张鲁,近两百年前的正一道长师,在汉中称王,名噪一时,尔后被曹操亲自领军扑灭,成为魏国大臣。死后他的儿子张盛离开北方回龙虎山,而使北方道门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中。
拓跋楠先还等着成公兴说自己,却不经意地转到寇谦之身上,有些失望,只能含混地言道,“寇师兄他不会的。”
“我反正看不到那一天,不去管他。”成公兴闭目沉吟一下,又睁开眼睛,像是才想起本来要说的话,“我要除去你的教籍,收回符箓,从今日起,你就不是正一道的道徒,也不是我的弟子,不许再……”
拓跋楠脑子里嗡的一声,顿时便听不见成公兴接下去说什么,眼眶红了,泪水垂了一半在框外,再接着才听见声音,“……术法精进,也会有新的一番天地等你去闯入。”
他头伏在地上深揖,再抬起来已满脸是泪,哽咽说道:“弟子知道错了,在静室里处刑三七,已经有所悟,老师父要是觉得还不够,要是刘师兄的父母觉得还不够,弟子愿意接受更重的惩罚,只求老师父别赶弟子出教,弟子不想下山,天下之大,因为,并没弟子可去的地方!”
天下之大,并没有他拓跋楠可去的地方,这是他的真心话。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成公兴深沉,又是意味深长地说道,“在崆山洞府,你不过是个无法施展本事的小道士,帮师兄弟们作法而已,出去在外就没人能限制你,谁知道你能闯出一个什么样的天地,成仙又有什么意思,不过是多一个名字在传说和故纸堆里发霉,实际上没什么意思。”
拓跋楠似懂非懂,觉得老大不对劲,可说不出不对头在哪里。
“当年送你来的人,现在要接你走,你要回你来的地方,何来没去可的地方?”成公兴叹息着继续说,“他为了带你走,备了肥羊数十只,布匹绸缎几十匹,谷物十车前来,我是个贪图财物的主持,崆山洞府上上下下几百号人口都要张嘴吃饭,我怎么能把你留下而拒绝那么多钱粮?”
拓跋楠哑然,心中顿时明白,原来是燕叔叔来了,他来接我回代地去,这当然就不是没有可去的地方,这是他年纪尚小时每天都埋藏在心底的渴望,后来屡盼不至也就死了心,当自己是孤儿一般。这回突然成真,好大一个意外。
既是意外,他心里也没什么波澜,早就知道就算回去也只是个狗崽子,地位卑下,见不着自己的妈妈。
同时他心中也涌起疑问,心想,如果是我非回去不可的情形,难道是我那弟弟出什么意外了,燕伯伯是来接我回去继承……即便不是多尊贵的位子,也算几部几万户人的头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又立即想到,不对,这事成真的前提是我那弟弟出了意外,我怎么能诅咒他,他没做错什么,到底是我同父所生的亲弟弟啊,这么想,是我自己的心肠坏掉了。
他实在还是想的,世上岂有不希望实际上让自己遭受凌辱的人受厄的人呢,那是古代的君子,他并不是,左右为难,脸慢慢涨得发红。
鹿衔花去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喂!江澄!
- 简介:人物归墨香ooc归我不拆cp群477433184佛系更文写着玩的不喜勿喷封面不知道画师所以无授权麻烦哪位小可爱知道的话告诉我一下吖
- 4.1万字5年前
- 混沌之吟,银龙与混沌的爱恋
- 简介:浩娜恋
- 0.3万字5年前
- 小花仙之暗黑之战
- 简介:光明与黑暗的大战,究竟是否会被终结?世界能否重归和平?黑暗与光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武功与科技究竟那一个是人类的选择呢?
- 33.3万字5年前
- 火影之红魔
- 简介:玖夜失误穿到火影成为鸣人的哥哥,于是世上多了一个究极弟控~~“哥哥,佐助欺负我(´இ皿இ`)”“佐助为了我弟弟的身心健康劳驾去趟地府吧~”“哥哥,大桐木桃式欺负我”“嗖嘎,那桃式桑替我向鬼灯桑问好~”某夜表示欺负弟弟的打一顿就好,不行再打一顿~嗯,没错有CP,铁定是男的玖夜,红发,有呆毛(开心时才有),爱吃糖葫芦(其实是我爱吃)
- 4.1万字5年前
- 乡村教师的血泪人生
- 简介:回忆一段往事,缅怀一个亲人。本书主要叙述贵州水城县乡村教师彭克忠的一生,真实全面反映农村生活。
- 13.8万字4年前
- 未来老婆找上门
- 我胡焕,家里年少离异,父亲长年酗酒。这种环境下,我性格死气沉沉。在不知名的大学里,我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室友欺辱我没有个性,我无能抱怨着一切。我尝试改变,但最后总以碌碌无为的逃避结束。大学毕业后,我只是个小职员。别人的生活是丰富的,我却告诉自己:“干脆就这样吧!”直到一位女孩,向我伸出了双手。从那以后,我确定我人生第一次有了意义。
- 1.2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