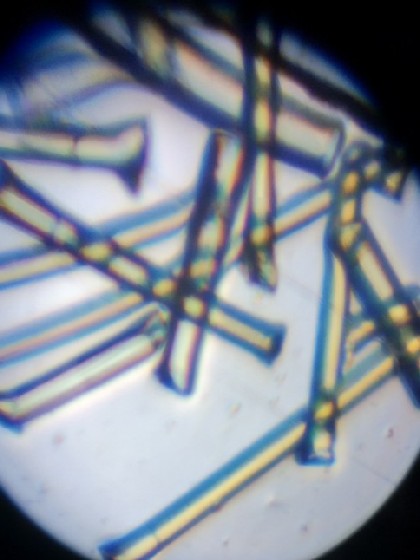十一章 授业
“杀人!”
卫陌猛地抬起头,脖子上青筋直跳,脱口说出自己掩藏在心中最真的想法。
卫陌心头一惊,也不知道在害怕什么,或者是读书人斯文的脸面,或者是父亲幼时的教导,总有一股压抑的感觉在告诉他:杀人,是不对的。
念头一闪即逝,却再难压住心中的暴虐之气:
“杀人,我就是想杀人!”
“我就是盼着有一天,我能碰到我的那些仇人,能把他们压在地下,一拳一拳的,捶死他们!”
卫陌抓起手边的碎石子,一个个的砸进溪水中,溅起一片片水花。
“挨个捶死,捶烂!”
“这辈子哪怕做不了伍子胥,我也要做个聂政!宰了朱全忠!”
秦烟微不可查的点点头,轻着脚步走到水边背对溪水,挡住卫陌的视线:“所以,有什么想法就痛痛快快说出来,不要藏着掖着。想杀人,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你身为人子,要为父母报仇,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秦烟顿了一下,又接口说道:
“但要学武,必要心诚。你只有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要去做,你才能学的安稳,学的踏实。”
秦烟说着,伸出一根手指点在卫陌额头:“人,唯不可自欺。”
卫陌仰起头,看向秦烟的脸庞。这才是前天,她反复问自己“为什么学武”的原因吗?因为自己顾忌着什么读书人的脸皮,害怕别人说他杀心重,尽捡着好话骗她。
仔细想想,自己现在算个什么东西。就因为自己在俺拓耶没的面前说了一句自己是读书人,所以还没学会那些读书人的本事,就先学会了读书人的遮遮掩掩,盖遮羞布?
屁!
你卫陌是个什么东西!
秦烟收回手,俯视着卫陌。卫陌抬起袖子蹭了蹭额头——秦烟的手背看着嫩白,一根根血管长在肉里青青浮现,但双手的指腹和手心都有一层淡淡的黄茧。这是常年练枪所留,所以按在人的额头,让卫陌有一丝丝发痒。
卫陌借着袖子遮挡,向下擦了擦脸上未干的泪痕,再度仰起头诚恳的问秦烟:
“阿姐,我能跟你学武吗?”
秦烟闭上眼,轻轻摇了摇头:“抱歉,我——教不了你。”
卫陌一瞬间难掩脸上的失望。
秦烟卷起衣摆,靠着卫陌手边坐下,环出双臂抱住双膝,望着溪水对卫陌淡淡的发问:“你愿意放弃守孝,去喝酒吃肉吗?”
卫陌低下头,心里一片纠结。要放弃吗?吃肉啊,喝酒啊,不过两三个月没碰到,现在想想心里都馋。何况打着练武报仇的旗号,谁都不会说他一句什么坏话,反而可能会夸他有孝心有志气。
只是,父亲会喜欢吗?
父亲那样的古板之人,见到了肯定会骂他不守礼节,不知廉耻。无论卫陌能说出什么理由,在父亲眼里,孩子错了就是错了,要打。哪怕他现在已经仙逝了,恐怕也会跑到梦里来指着自己鼻子骂。
卫陌害怕自己的父亲,害怕自己一做错事,就被他骂被他打。所以平日里见到父亲都缩着脖子躲起来,能不去见父亲就不去见,能离得远就想办法离得远。父亲在外面做了什么,每日为家里或朝中奔忙,他不去想,也不想打听。
印象里父亲头发已经稀疏的连簪子都簪不住,斑白的只能用头绳绑在脑后,活活把四十岁的年纪,活的像个六十岁的老叟。
现在想想,惭愧吗,后悔吗,愧疚吗?
可是现在后悔愧疚又有什么用?父亲又不会知道,他的孩子躲着他,避着他,甚至会经常气他。但他的孩子,也爱着他,哪怕只是埋在心里,微不足道。
哪怕每日早起问安,都是敷衍了事,还没有掏心窝子劝一句父亲保重身体呢。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他还没做出点事业给父亲看呢。对呀,卫陌也曾想着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去给他父母看,让他们知道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孩子也能出人头地。在少年人不切实际的幻想里,自己只要抓住机遇,凭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就能换来别人的刮目相看,甚至是艳羡嫉妒。
只是,凭什么?
凭什么你不努力,整天睡大觉,老天爷就要偏偏宠爱你,让你万事顺心功成名就?
凭什么你不务正业,整天斗鸡走马,满天神佛就要庇佑你,让你和和美美一帆风顺?
你吃过什么苦,受过什么罪?就一定要让老天爷独独宠爱你一个人?
是故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又有《易》言: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遁其一。
徐州东临郡的卫家书房内,卫宛拍着桌子对面前站着的卫陌教训:
“所谓‘一’者,生机也。是‘道’留给世间万物生灵一个博取生机一线生机的机会。天道有仁,不使人绝,但这一线生机和命运,是要靠自己去拼去努力的。”
“所以才有乾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才有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你懂不懂?”
“一天到晚尽是偷奸耍滑。你还说你努力了,你尽心了。罚你抄的书,你还让你弟弟帮你抄。你皮呢?”
说着,卫宛就将桌子上的黄心草纸一把摞起来,砸在卫陌的脸上。草纸轻飘飘的,不重,但也刮的卫陌脸疼。
卫陌低下头,学着秦烟的坐姿,蜷起双腿抱住,将头埋起来。
秦烟轻轻吁了一口气,对卫陌说:“我不为难你。能守孝,也是你的孝心。毕竟你刚才说的聂政,也是为母守了三年孝,才去替仲子行刺侠累的。”
卫陌伸出头搭在膝盖上,哑着嗓子低声辩驳道:“不是啊,侠累是谁?聂政死的时候,他母亲还没过世呢。”
秦烟斜着眼看他:“你读的哪本书这么写的?”
“《琴操》。”
“那是话本小说。你爹也让你看这种书?”
卫陌微微撇过脸,不好意思的回道:“我偷看的。”
“太史公的《史记》没读过?”
“读过一点,会几篇。”
“哪几篇?”
卫陌彻底摆过头,将脸颊放在膝盖上,用后脑勺对着秦烟:“其实就看过一篇,《项王本纪》。”
秦烟拿起地上的一片叶子,屈指夹在拇指和中指之间,向溪水一弹:“猜到了,果然是最假最像故事书的那一篇。”
“你别学项王,这人勇则勇也,但薄信寡义,最没担当。”
卫陌心里不屈,想着项羽那么大本事,能冲阵夺帅盖世豪杰,哪会像秦烟那么说的那么不堪。但现在实在是没有心思去和秦烟争辩,只想闭口不言。
半晌,卫陌收起情绪,闷闷的问了一句:“就真的没有办法学武吗?还是一定要等到三年以后?”
“有。”秦烟又弹起一片树叶,射向溪水。树叶一头扎进溪水里,又被溪水流动卷起,漂浮着跟随水流避过拦路的青石,一路向下。
“什么机会?”卫陌闻言一个激动,猛地扭过脖子看向秦烟。只是突然之间用力太猛,整个脖子不堪受力,窜起一股钻心的疼痛。卫陌摆正脖子低下头,抬起双手揉起脖子。
“内家功夫。”秦烟不等卫陌插话,接着解释道:“内家玄劲,在修炼之初,恰好是要素食寡餐,以便锁气固血,清濯体内污秽。”
“阿姐能教我吗?”
“我说了,我教不了你。我不会内家功夫,只练过家传的外家横枪。”秦烟摆摆头,看着卫陌的脸庞:“但我可以教你一点,内家行气的基本之念。”
卫陌捂着脖子,整个人侧过身子看向秦烟,眼神里充满了希翼。
“肖敬微留给你的《纯阳养生功》呢?”
“在身上。”卫陌按住胸口,伸手掏出几张已经卷角开裂的黄纸。
在慈州众人分别时,林逾蓝曾送给卫陌一柄短剑,因为在部落中行走,不好佩戴,所以一直压在枕头下收藏。唯有肖敬微留给自己的《养生功》,自己放在怀里,随身带着。
秦烟看到卫陌的劲头,忍不住出口给他泼了盆凉水:
“你不要抱太大希望。这只是一本养生的功法,只给年老体弱者活血舒经之用。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内家玄功。”
秦烟审视了一眼卫陌,见他脸上笑容渐淡,心里忍不住一叹,继续说道:“我最多只能从这册手札里,教你一点运气理念。真正的内家运气法门,还要看你机缘。”
“那些内家玄功,除非拜入名山师门,否则纵千万金,亦不可得。内家,远比外家更注重传承清正。或许等下次你平叔来了,你可以托他为你造访求取。”
卫陌低下头,有些羞涩的捏着衣角:“阿姐你都说,那些功夫那么贵,我现在一点钱都没有,不敢让平叔破费。”
秦烟扣着手指往卫陌头上一敲:“刚才教你,别学项王,要有担当。男子汉,有事相求就张口说出来,没人笑话你。欠人钱就还,欠人情就报。待人以诚,言而有信。这才是男人。”
“是。”卫陌低头认错,也不敢去捂头,认真应下。
见与秦烟离得有些近了,想着男女大防,卫陌微微向后拉开一点距离。
“阿姐,当时还没出关时,我问有你,你不是没说会这功夫吗?”
秦烟却是伸出右手抓住卫陌肩膀的衣领,将他拽到跟前与自己并排做好,左手将肖敬微手写的《纯阳养生功》摊在两人膝间:“那时候你躺着都不能动,怎么教你?”
“静心,先跟我念。”
“是。”卫陌双手环住膝盖,挺直腰背,刨除杂念。
“首言:夜阑人静万思抛,意守识海封七窍。深吸缓吐搭桥鹊,轻燕经云掠九霄。
卫陌跟着念道:“首言:夜阑人静万思抛,意守识海封七窍。深吸缓吐搭桥鹊,轻燕经云掠九霄。”
“开有乾元启运:左步开旋臂摆掌,收腰敛臀,气息深长,百会上顶身中正,左足并掌落身旁。”
“开有乾元启运:左步开旋臂摆掌,收腰敛臀,气息深长,百会上顶身中正,左足并掌落身旁。”
“再有双鱼悬阁......”
“再有双鱼悬阁......”
有一堆不知名的野雀分散落在树上,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似乎也在为这一片怡人景色而陶醉起来:
有阳光被密林遮挡,浓而不烈;有山溪泉水蜿蜒盘桓,流入一边碧色湖泊;湖边还有牧人,身后跟着稚童一起,驱赶牛羊;三两顶白云自头顶飘过,却遮不住苍穹蓝天。
而在这深翠山林里,涓涓溪水旁,有一大一小、一女一男两个人挨头并排坐着,像是在读书,又像是在唱歌。
似乎怕那跟着学唱的少年不懂,穿着素白衣衫的女子又站起身来,在溪边做起各种各样的动作,还跟少年解释起歌里词句的意思。
卫陌站起身来,一边听着秦烟对句子里的解读,一边模仿着对方,做出不同的动作。突然心中泛起一个念头:
“这一次也许,就是老天爷为自己,遁去的‘一’吧......”
念头一闪即逝,卫陌也不去多想,转而抱守清明,牵起手足腰腹,跟着秦烟打出一式“犀雷望月”。
临水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苍天再爱我一次吧!
- 简介:讲述一个天才被苍天抛弃,最终霉运连连
- 3.4万字6年前
- 穿越到斗罗大陆的城管不想摸鱼
- 当城管来到了斗罗大陆,又出现怎样爆笑的事情呢?
- 1.7万字6年前
- 伏落
- 赤乌四年,皇太子孙登病逝,吴国宫廷内的权斗增强,迫使孙权进一步打压士族和挑拨的人,一场吴宫惊变正在蕴酿
- 1.1万字6年前
- 斗3龙王传
- 简介: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脚踏阴阳定乾坤,荒古之今我为尊;霸天绝地无人挡,贸然一人杀天殇;血路凋零残花亡,残躯镇世仍为皇;在持神印杀四方,只为守护心中人。
- 2.8万字6年前
- 率土之滨
-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皆是王臣
- 0.8万字6年前
- 当大师兄实在太难了
- 在下乃十剑盟第四宗燕宗首席大弟子,原因竟然是因为只有我一个弟子?所以就被迫当上大师兄了?美少女宗主整日游手好闲,结果宗门任务全给我来做?好不容易招来的师妹们也不帮我分担压力,结果你还想上我?更何况其他门派还对我们虎视眈眈。作为大师兄的我..
- 1.8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