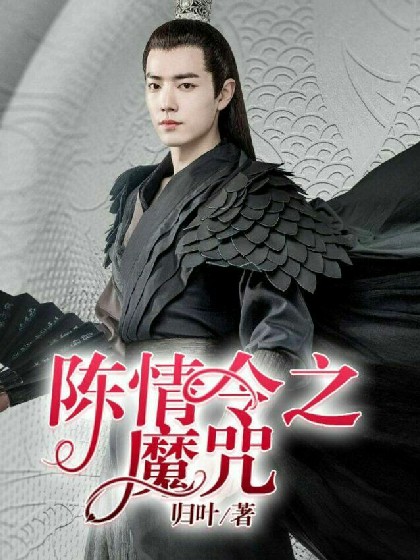番外(与正文无关)
五
那夜一杯混浊的醒酒茶成了谜团,成了心结,余沥只当是噩梦,隔日还傻乎乎地问连缬。
“是梦吧。”他想了想,又添道,“小姐睡觉不大安靜,会小声打鼾,还说梦话。”
她眼圈的一抹红转眼间就蔓延至纤长白皙的颈背,垂首小声反驳“胡说”“哪有”,却又坐立难安,眼见他笑意愈深,几乎是懊恼地将脸埋进被窝,只拿眼角余光瞪他。
这样平和的时光,很多年后再回想起来,仿佛就到那天为止了。
傅家便是在那之后出的事。自他们与华北开战后元气大伤,本想着余家子辈无能,不怕耗不到他们败光家业的一天,谁知耗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连缬。
连缬经手余家大小生意,说起来也统共不过两年。修鞋也好,算账也罢,聪明的人一通百通。商界往来举重若轻,仿佛他天生就该站在那里,信手一挥便可点石成金。外头人人尊称他一声“余行长”,说到底也才不过二字当头的年纪。
傅家起先哪肯将他放在眼里,可他手段通天,黑白通吃,有传言说他原先就是个杀人如麻、盗卖军火的帮派人物。
江左傅氏素有名望,连根拔起不易,吞并他们的产业和据点却是可以徐徐图之的。直到股市东家集体抽款撤离的那天,傅氏家主惊怒交加,竟就在宴席之上咽了气。傅氏家大业大,旁支甚多,不出三个月,大公子就死于内斗,三公子傅长临出逃台湾。至此,余家坐收渔翁之利,在江左一家独大。
而这一切依旧被连缬瞒得密不透风,因此余家内外都以为是余老爷宝刀未老,手刃劲敌。但翠屏不同,她是余老爷最亲近的枕边人,最知道察言观色,知道什么话该什么时候说,平日里能和俗不可耐的大房二房耐心周旋,与留过洋念过书的余沥也能聊得上话。
因此,这日有人到汇丰银行汇报给连缬,说是七姨太来找大小姐,他没太当一回事。回到家拧开门,余沥也只是怔忡地看着后院摇摆不定的棕榈树影,余晖跃动如金屑,争先恐后地挤进她微微发亮的瞳仁。
“一定是梦吧,连缬。”她徐徐回首,仍抱有侥幸,抿嘴笑得很勉强,“听说傅家倒了,是你的功劳……”
背脊像被打上钢条,他一时间僵硬得连手脚都不知该如何松放。否认已经不存在意义,可他还能保持无懈可击的微笑。
“因为你,原本是该姓傅的。”
六
连缬是出生在穷山恶水的鄙陋村落不错,但他的母亲来自江左乌氏。
乌氏世代官宦,却没赶上好时候,辛亥的浪潮打来,没落得一塌糊涂。所谓树倒猢狲散,从前与乌家小姐定下百年之好的男人遂忙不迭地毁了婚约,另娶高门。后来便是战乱、别离和永不磨灭的折辱,最终她委身一位粗鄙村夫,不出两年便抑郁而终。
连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却又知道,他的父亲本该是谁。
“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我原本怪不得那个男人。可天知道他是如何陷害乌家,侵吞我母亲的家财和名望,才有了日后的滔天富贵。”他口吻镇静稳定,眼角眉梢眼却镀上消极病态的红,“小姐,我该对那个掠夺我母亲一生的男人抱有什么样的态度?至于他的儿子,本该喊我一声哥哥的傅长临,我又该怎样向他讨还本属于我的一切呢?”
所以他才进了余家,借助这傅家死对头的势力进行他蓄谋已久的报复。
话毕,他走上前,陈皮的寒香随之侵袭而来,是切肤的彻骨的冷,她不由自主地踉跄后退,却被他一臂圈住了腰。
他没有逼她回答,因为他早就有了答案。他浑身痉挛发冷,漂亮的唇却是滚烫的,干脆俯下身,在她额头烙下罪恶的印记。
“我记得小姐曾同我说过,你不吃人。”他站直身,抱憾地笑了,“但很可惜,我会。”
余沥有尝试过若无其事地出门,可还下不到四楼,就有用人顶着惶恐的笑脸将她请回去。她强作镇定地说要见父亲,也被以老爷公务繁忙为由委婉拒绝。
她不傻,明白家中实际的掌权人,甚至整个江左都已然悄无声息地变了。
但这个在外头兴风作浪、人人畏惧的年轻男子,每晚无论多迟都会回家,总爱坐在小沙发上微笑着看她闭目装睡,连替她掖一掖被角都显得踯躅再三、畏首畏尾。
也有装不了睡的时候。他将要事推了提早归来,不为别的什么,多数时候是给她带一些新鲜的小礼物。满面期待地问她喜不喜欢,只得她勉强一点头,他就欢喜得像个手足无措的少年。
他会让她穿上他买的衣裙,心满意足地单膝折跪为她套上合适的鞋。也会要求她替自己念一段不知所云的英文诗,然后颇为向往地感慨他原本也能听懂的。
她如履薄冰地满足他,见他稍稍松动,才状似无意地提出想出门走走。前一刻他还在忐忑地笑,下一秒就不带商量地冷下去:“小姐是打算去去就回,还是一去不回?”他扶着膝盖,手背现出凹凸不平的青紫条纹,再抬头时眼锋又镇定又冷漠:“那么这次,我就没必要再向余老爷告密,直接派人杀了傅三就好。”
往事翻江倒海地灌来,他为她擦去鞋上的泥,棕榈树下东窗事发时他太过凑巧的不在场,父亲放出将她许配给乞丐的狠话命定般被兑现,还有他在新婚那夜说出的那句“天意”。
什么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蓄谋已久。
她如蒙重击,几乎喘不过气,而他只是无动于衷地看着她:“小姐不该还念着同他见面,小姐本就该是我的未婚妻。”他放开捏到变形的拳头,细长的手指探过来,报复似的一条条解开洋裙繁复的系带,指腹钢刀般刮过她如同草本植物的背脊。
末了,他才将那副强忍颤抖的身躯虚虚地拥在怀里,问她:“很害怕?”
她只是咬牙,不说话,唇齿渐现血的痕迹。他怅然叹息,脱下大衣将她裹好,用最哀伤无害的态度威胁她:“所以……不要惹我生气。你也不想看到余家步上傅家的后尘,对吗?”
暴雨来临前的冷风卷入室内,震得曳地的窗帘不安地飘浮。她突然回忆起先前的某个深夜,也是这样风雨如晦,她喝多了酒,他为她沏来一杯致命的解酒茶。
原来那不是梦。
——————————
求10字评论,求鲜花,跪求
斗罗:笙歌一曲诉离殇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黄明昊:我要魂穿你妹妹
- 简介:〈奶思文社〉一个非常NB草率的文社.·宠妹狂魔黄明昊/Justin×沙雕腹黑艺术生—————♡故事已开启♡———————————·尽请期待·——————
- 3.0万字6年前
- 边伯贤:姓与晚餐
- 简介:·原创·禁抄袭借鉴转载·脚本:江.时/边鬼鬼原名《性与晚餐》,话本审核不过,所以改成《姓与晚餐》<<<<<<<<<<<<被心魔缠身夜夜承欢,心魔的名字是你
- 1.0万字6年前
- 源娜恋爱记
- 简介:慢慢看。。。。
- 0.8万字5年前
- 陈情令之魔咒
- 简介:何为正?何为魔?杀人者为魔,救人者为正魏无羡:“这一切,皆因为我,我没护得了这世间,现在一定要护住你!”蓝忘机:“离开了蓝氏,你变了许多,变得和他有几分相像了。”江橙:“我能忍心杀了他,对你,却永远也忍心不了。”这一世前半辈子,你只愿活的逍遥自在。后半辈子,你只愿陪他坠入魔道!!!
- 9.0万字5年前
- 开宝一家之不想回忆过去
- 简介:不想回忆过去的,可不是开心他们,而是一个神秘人
- 2.8万字5年前
- 修罗之瞳,阴阳之花
- 简介:这个作品不是原创,而是在百度贴吧里别人同意的!但后面是自己写的!
- 3.1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