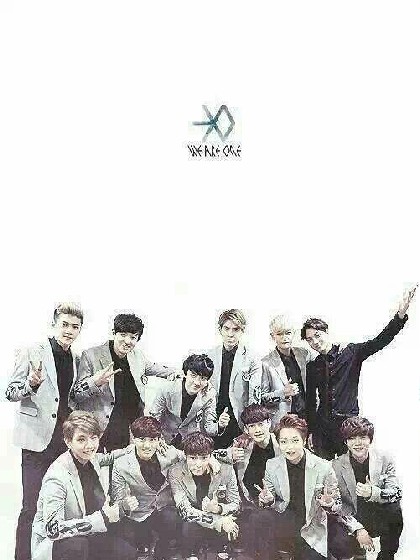第一百零三章帝后失和惹争议
夜色渐深,季梵音百无聊赖揭开莹白色的琉璃灯罩。
“娘娘,床榻已铺好。”
她心不在焉应了声,又忙唤住欲退下的随侍宫女:“你适才说了什么?”
宫女双手搭在腰际,垂首毕恭毕敬答:“回娘娘,床榻……”
季梵音抬手一阻:“上一句。”
“工部尚书与从二品巡抚两位大人连夜进宫面圣,面色凝重,似有急事禀奏。王上在御书房接见了他们,至今未出,似有通宵达旦之意……”
灯罩‘啪‘地一声盖回灯盏处,季梵音凝眸若有所思片刻,吩咐道:“更衣。”
季梵音穿过长廊,迎面正好遇上从御书房出来的工部尚书张鹏翮和二品巡抚赵卓,后者忙敛衽躬身行礼。
“二位大人不必多礼,”季梵音目光不疾不李从二人面上扫过,旋即落在绿衣葱葱的赵卓身上,浅浅一笑,“本宫听闻赵大人断案如神,王上欣赏之至,破格提拔任用。”
赵卓一本正经拱手,字正腔圆道:“承蒙王上赏识,臣定当用尽毕生所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多么慷慨激昂的一番说辞,张鹏翮肩膀微微耸动,抿嘴强忍住笑意,俯首先行告退。
待他一走,季梵音也当即遣退随行侍女。
灯火通明的宫廊,将余下二人的身影拖曳拉长。李李风中,远眺凝月的季梵音轻若无声开口:“苏姑娘一事,有劳赵大人了。”
若非他的掩耳盗铃,苏幕遮难以躲过梁榭晗的眼线。
此时的赵卓面色红哂,一改适才镇定自若的姿态,挠了挠头,憨厚一笑:“娘娘言重了,能替娘娘与王上分忧,臣求之不得呢!”
边说边霸气拍了拍胸脯,响声如雷。
分忧吗?
宫漆木门内的光线透缝而出,明晰灼亮。素手推门而入,室内宽敞的方形案几前,置了盘对弈棋局。玄色單衣的男子,深眸凝视前方的棋盘,‘吧嗒’一声,如墨般通透的黑棋脱离修长指腹,落定。
“一个人下多没意思。”
娇音刚落,如兰花般的纱裙在晃过他的眼前,一颗莹白似玉的白棋跟随纤纤素手一并落下。
梁榭潇眼皮都没掀,神色如水,平静无波,不动声色从云窑子中掏出黑棋,她亦随之。两人就这么你一来我一往,下了一个多时辰。
半晌,季梵音才逐渐琢磨出不对劲之处。素手故意在棋盘上顿了片刻,姗姗落子。烛灯下的长指骨节分明,脉洛清晰。黑子跟随他的动作从左往右,棋盘晃过一宽厚的掌影。
他,在让她!
或者说,二人在比谁的耐心更好。
黑子堪堪绕过一招就能结束全局的一隅,转而落向他处。落子的刹那,他掀起那双如墨般漆黑的深眸,浮动过一抹浅光,似笑非笑。
“技不如人,我认输。”
她面色如常扔下白棋,徒弟败给师傅,不丢人。
移动的足履刚迈出两步,素手被大掌轻而易举握住,拇指摩挲几下她的柔夷,嗓音低如沉弦,似夹带着千言万语:“生气了?”
季梵音默然垂眸,喉头如被蒺藜鲠住,红唇翕合了半晌,才似叹似怨坦言心中所想:“哥,以前习惯被你和爸妈捧在手心,如同温室里的花,拥有遮风挡雨的避所。而今,你我二人已是拜过天地的夫妻,本应同甘共苦,携手共度......”
滚烫的湿意瞬间滑落仿若一碰即碎的面颊,风一吹,冰凉如寒冰。
“......可你为何,总是三翻四次将我推向安全地带,独自一人承受泰山压顶般的巨重......”
理智又委屈的控诉,如同一把凌厉锋利的刀刃,毫不留情兜头,将他劈成两半。
大掌环过细若无骨的腰际,用力一转,二人正面相对。小心翼翼捧起泪水涟涟的清容,心疼得一滴滴舔舐咸湿的泪痕:“何来的三翻四次?我怎么不知道?”
避不开他的亲昵,她索性听之任之,嘴上却不饶人:“你早就知晓蕴儿已经苏醒,她又在短短时间内决定千里追夫,必少不了你在背后的推助!”
数日前,他狠心下了禁足令,除却梵音殿,其余之地一概皆被拂掉。就连帮忙操办红绡大婚之事,都不许。
他自己倒是勤快,公主府与王宫两头跑,美其名曰探望。也确是探望,顺便点拨。
可这一切,都是瞒着她进行的。
思及此,心头悬挂的大石又重了几分。
梁榭潇揉了揉她光洁的额头,鹅蛋般的容姿染满怅惘,他无奈又好笑解释:“连日奔波致使你感染了风寒,浑身酸痛又绵软无力,难受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可是忘了此事?”
季梵音心下一个咯噔,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她忘得差不多了,他可记得一清二楚。
优思过度加之睡眠不足,体质虚寒,寒邪一侵体,立马诱发了一场不小的烧炎症,接连不断的咳嗽如同一把锐利的尖刀,刀刀割在他的心脏。
“哥,我难受......”
恍若回到儿时,生病不肯吃药,迷迷糊糊她蜷缩在他怀中,气息奄奄吐纳浓重的呼吸声。
梁榭潇揽人入怀,紧了紧臂弯的力道。如此孱弱如薄纸的人儿,叫他如何忍心再让她受累?
季梵音摸了摸鼻尖,气势弱了两分,仍有八分的气焰:“且不论蕴儿是女儿身,从颍上到西上的路途如此凶险,怎能让她独自一人上路?”
“身为瀛洲王族的血脉,她需要成长!”言语淡漠,一字一句甚似不近人情。
季梵音气得胸口剧烈起伏,使尽全力挣脱他的束缚,扬手给了他一巴掌,冷冷道:“梁榭潇,你变了!”
如此爱民如子的你,怎可轻易葬送他人的性命?更何况这个人,还与你这副躯体有着一母同胞之情?
清晰的巴掌印落在棱角分明的五官中,他转头,深沉如潭水的眸子一瞬不瞬看着她,眼底淌过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娘娘,您吃点东西吧?”
侍女芷兰候在内室外,如往常般得不到任何回应,兀自着檀木桌上的各色菜肴,长吁短叹。
身后忽地罩落一黑影,芷兰面上一喜,忙不迭转头:“王上......”
咧开的笑容因落入眼底的明艳容颜而略显忐忑,诚惶诚恐伏地跪拜:“......芷兰拜见太、太后娘娘......”
齐羲和一身素纱浅衣,仪态端容迈进前殿。
曦光微浅的青铜镜前,神色恍惚的季梵音闻见‘太后’二字,敛眸收神,将置在手中的白玉簪插回发间。
鎏金香炉烟雾袅袅,李李拂向轻摇浮摆的纱帘。少顷,素手撩起垂帘的一角。彼时,端坐上位的齐太后正从容嬷嬷手中接过一秘色瓷杯,茶香氤氲沁香扑鼻。
芷兰仍跪伏在地,有些瑟瑟发抖。
季梵音沉吟片刻,侧身福了一礼:“梵音给母后请安。”
回答她的,是静默的空气。
金黄色的茶泽不急不缓轻啜,瓷杯李李见底。
啪-
瓷盖闷哼了声,阖紧在瓷杯上方。
“请安?”齐羲和掀眸睨了她一眼,讥诮一笑,“若非今日哀家亲自来你这梵音殿一趟,还真见不着你这儿媳的影子了。”
“梵音近日身体不适,已遣人禀告母后。”
“哦?太医怎么说?”
“无碍,静养即可。”
齐羲和动作轻柔捻起一方素帕,眸色却陡然凌厉,沉声厉呵道:“跪下!”
殿内的空气骤然凝固。
“娘娘......”
在芷兰低唤声中,季梵音敛袖跪地。
“上祖训!”
片刻,容嬷嬷手中多了条镶金方尺。皱纹蛰伏的面容上,潜藏了一双恶狠狠地眸子,如同盘亘多时的毒蛇,吐着恶心的蛇芯,对她虎视眈眈。
“往日在潇王府,你们夫妻二人小打小闹,哀家无权过问,怡情罢了,”齐羲和绕在她身侧,一步三顿,声声斥责,“而今,你们二人已贵为瀛洲国的帝后,表率之首。你可知,帝后失和,对瀛洲百姓将会是多大的影响?”
那夜,生受了她一巴掌的梁榭潇情绪复杂靠近她,她如同惊慌失措的白兔,吓得连连后退,又气又恼中,逮着什么扔什么,却无法阻止他的靠近。
恰好手边触到一物,冰冰凉凉的,她慌乱端起一泼,某人瞬间沦为落汤鸡。
趁此时,她将金盆一抛,步履未停跑出了御书房。
第二日,宫中便开始流散帝后失和的传言。
垂落绒毯的光影李李浮动,季梵音身形猛地一颤,不可置信抬眸,落入清湛眼底的,是背对着容嬷嬷的齐羲和蕴含着无数情绪的复杂眼眸。
她这是在......教她?!
而非公报私仇!
她下意识抚了抚手腕,红痕早已不复存在,可是她那句‘对不起’和‘谢谢’却一直萦绕在耳廓中,久久不散。
“也罢,做儿媳的礼仪孝道不立,最后还得由我这个做母后的出手指摘一二。”
痛心疾首的话音刚落,细弱的蝴蝶背重重挨了方尺一记。
紧接着,是第二下、第三下......
翌日,宫内又有消息流传至坊间,继王上偶感风寒龙体欠佳后,王后亦凤体受损,需静养。
有人戏称:不愧是鹣鲽情深的帝后,生病都凑一起了。
也有人言之凿凿反驳:帝后二人失和,或许只是不愿拉下脸来求和,才故意称病,避免相见尴尬。
更有说书先生眉飞色舞描述,恍若亲眼见证般:王后赏了王上一盆子水,太后闻之一愤,本就对这一儿媳心存不满,此番更是趁机拿出帝家祖训,罚了王后十数方尺,啧啧啧......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姑妄听之,入耳即过便可。
“简直岂有此理!”
书童模样打扮的清秀男子气呼呼撸起袖子,正欲上前理论一番,被一侧单手吃着包子书生模样的白衣男子信手一阻,神色如常道看了台上一眼,道:“图个娱乐而已,无需当真。”
话音刚落,茶馆内响声雷动,拍手叫好声不断,恰好掩盖书童嘴里的发出嘟囔:“帝后之事,哪里轮到他们如此调侃?他们也就仗着山高皇帝远,持胆行之……若当时红绡在娘娘身边,坚决不会让太后动长姐一根头发……”
说着说着,眼眶湿润,泛起了泪波。
季梵音无奈又好笑,这话锋转得太快,她有些适应不过来。
满足了小众百姓要求的说书先生,惊木一拍,再出口时已换成粤语。
季梵音顺势拉着她挤出人山人海的茶馆,靠在墙角一隅,拭了拭泪痕她眼底渗出的泪珠,轻若无声叹口气,故意道:“早知你这般爱哭,就带芷兰出来了……”
“没有没有,红绡没有哭……”
季梵音轻笑,看着面前这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已婚书童胡乱抹了下眼角,强颜欢笑。
“好了。”
抬手拍了拍她的发顶,二人正欲离开,不远处牛肉面小摊的交谈声瞬间落入他们耳廓——
“你听说了吗?通判府上来了好几位贵人。”
“这事,想必在咱们广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
“是啊,这场悄无声息席卷了咱们两广地区的飓风,再提起,仍心有余悸。”
“幸而当今王上体察民情,更是亲手指了工部尚书兼任河道总督,抵达咱们广篁治理飓风后带来的水患之灾。”
“这位工部尚书的名号我听过,他可是整个瀛洲响当当的骄傲。想当年黄河一代河水泛滥,他以‘筑堤束水,借水攻沙‘为号,彻底解决了先王多年的困扰……”
二人吃完黑陶碗中的牛肉面,剔了剔牙,意犹未尽继续:“另一位走马上任的两广总督,近几日更是替咱们老百姓惩处了贪污腐化多年的蛀虫,将其连根拔起,简直大快人心。”
两双素手在小玩意儿摊子上漫不经心挑挑捡捡,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牛肉面摊那两人。
“怎么又不说了?”红绡疑惑不解。
不仅不说了,还准备离开。
季梵音默然片刻,三步并作两步上前,半蹲下身拾起一枚闪闪发光的银锭,故作惊讶喊住那两人:“这是二位大哥掉的吗?”
见钱眼开的两人猛咽了咽口水,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当即笑逐颜开,点头如捣蒜。
“可小弟有个疑问……“季梵音故意将银锭在他们眼前晃了晃,“不知二位大哥如何证明这银子是你们的呢?”
“在我们离开的地方捡到的,除了是我们还能是谁的?”
“就是,你这个白面书生,疑心怎么那么重?”
季梵音笑了笑,双手交叠作了个揖,不疾不李道:“二位大哥稍安勿躁,小弟并未言这银锭非二人之财帛,只是小弟心中有个疑问,待二位大哥解惑后,当即奉还。”
两人默默对视一眼后,随即抬手一摆:“问吧。”
“小弟耳尖,听到适才二位大哥所言‘通判府上来了几位贵人’,这是何解?”
两人闻言后,当即笑得差点岔了气。
“没素质!”
红绡气得暗骂。
好不容易缓过来气,其中一褐色麻衣的男人扬眉一挑:“听你们二人的口音,不是咱们广篁的吧?也好,来者皆是客,不妨跟你们说道下那位断案如神风度翩翩的师爷。”
“哪位大人的师爷?”
另一个宽脸男人自豪道:“自然是两广总督大人的师爷!”
“口头说说不过瘾,通判府衙今日正当堂会审,我兄弟二人正欲过去,两位小弟不妨随之,亲眼见证一下那位卓然不凡的师爷是如何根据蛛丝马迹,抽丝剥茧一举擒获盘踞咱们广篁多年的蛀虫!”
参商1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彼岸仙之恋;仙妃异倾城
- 简介:她是比玉皇大帝更高的仙,因为天庭太无趣,便跑下人间体验世俗。第一世的时候,她是孤苦伶仃的杀手,只有红尘断里的四个姐妹,她被男友背叛而死,她发誓永远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男人;第二世,她穿越成了将军府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自己用实力创建了雪宫,成为金榜上的第一名。他,金榜上的第二名,偶然之间遇到了她,便爱上了她,他是人间比皇上还高的王,当两位王相遇,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简介未完,待继)
- 2.8万字6年前
- 十二神族绝命狼少的极品女王
- 简介:她是狼族的女皇。拥有着半人半妖的血统。有人说:她暴虐、荒诞、残政、杀戮、有人说:她美丽、温柔、大方、善良;传说:她曾经命人押着狼族最美的十二个少年参加她的大婚典礼。那年,她才十三岁。传说:她曾经为了狼族最美的十二个少年献出生命,死于敌人之手。那年,她才二十三岁。传说:她没死
- 14.9万字6年前
- 绝色狂妃之神妃逆天下
- 简介:她,本是21世纪的世界第一杀手,代号“zero”,但却被自己的挚爱之人所害死。 一朝醒来,却发现自己穿越到了一个与自己同名的小姐身上。这一切,究竟是天意还是阴谋? 他,是帝国的绝色王爷,这片大陆上最优秀的男子,无数少女为之心动,传闻说:不管男女老少通吃,上至八十岁老奶奶,下至六岁女童,却对她死缠烂打,不死不休。 片段1:“来,媳妇,咱来生猴子。”某男说。“不要”某女说。“为什么?”“你自己想,生个儿子吧,和你一起祸害姑娘,全世界女人都别活了,生个姑娘吧,又和我一起祸害人儿子,全世界男人都别活了。要是是龙凤胎,那全天下人都别活了我可不想被人说祸国殃民。”“没事,媳妇,生出来就不让他(她)出去祸害别人不就行了!”“…………”某女顿时很无语,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本文是作者第一次写的文章,还请多多关注呦(≧▽≦)求打赏,求推荐票!每天两更10打赏加更,10推荐票加更)
- 3.4万字6年前
- 桃花落烬绯歌处
- 简介:我愿以我之慧成为你之利剑,我愿以吾之智成为你之盾牌,我愿以吾之后背成为你之依靠,你可愿以我之名冠你之姓? ――顾绯歌 师傅曾说过我的自控能力强大得恐怖,可为什么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嘴、我的思想、甚至是我的这颗心都不听我的使唤了? ――江烬辰 看见你的第一眼我便知道你不属于我,不要再看着我,不要再对我说话,不要......你让我变得危险了,嗯?还想逃吗? ――姬离落
- 5.3万字5年前
- 不恋尘世浮华,不写红尘纷扰
- 简介:扣扣:1664955299进文社dd
- 0.2万字5年前
- 新还珠格格青幽
- 暂无介绍哦~
- 6.1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