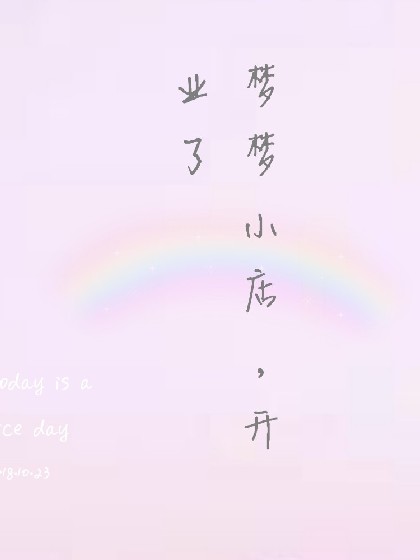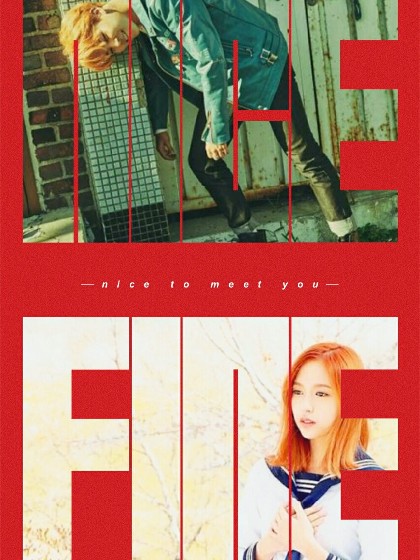二十五1
时值正午,军部办公室内乌烟瘴气着,因着前线战事不断,不仅有扶桑猛攻,内里又有卢御平的平家军逐渐逼近。而国内各房势力也在蠢蠢欲动着,虽说苏徽意早已通电全国,誓与扶桑势不两立,只是如今势单力孤,独拥半臂江山也是腹背受敌。
苏徽意连着开了几日的会,又要部署作战计划,原本就旧伤未愈,这样熬着心血,自是十分 憔悴,不过短短几日,已是像老了十岁。
这会儿天阴的厉害,乌云黑压压的,在窗前幽幽飘荡着。办公室内众幕僚正商议着作战计划,因着事态紧急,气氛自然十分低迷。
苏徽意坐在沙发上看着布防图,双腿搭在方墩上,他已经有几日没有好好休息,那双眼红彤彤的,眼底也是乌青一片。
此刻困意袭上来,他放下布防图,拿起桌上的烟点起来,转顾众人问:“国会那边是什么态度?”
秦桐隽敲了敲烟枪,说:“现在的国会也是四分五裂的,只有一小部分支持咱们,已经派了人去跟卢御平和谈了,眼下他们掌握着主动权,不知道又要开出什么条件来。”
苏徽意慢慢的抽了一口烟,说:“乔家的人有什么动静?”
站在一侧的林宁回道:“乔先生正在秘密处理财产,想是做了要离开的准备。”
秦桐隽若有所思的看了苏徽意一眼,才说:“七少,眼下虽说咱们与敌军是势均力敌,只是战事时好时坏,咱们也得做些长远的打算,不仅是人力上面,军火,物资,还是多多益善的好。”
这句话正说到苏徽意的心里去,他点点头,吩咐林宁,“请乔世钧过来。”
他狠狠抽了一口烟,便起身走到窗前,就见细密的小雨不知何时下起来,马上就要入夏,路边的金桂开的枝繁叶茂,上头零零散散缀着小花,这样被雨幕笼着,凭添了丝秋意,天空暗沉沉的,那一方的乌云汹涌的聚集而来,势如破竹似的。
他默默地抽着烟,就听秦桐隽说:“七少,有些事还是想开些吧。”
那雨在眼前纷纷扬扬着,打的金桂的叶子簌簌抖着,小花落得遍地都是。这会儿起了大风, 在空中微微打着旋,苏徽意静静地看着,隔了半晌才说:“大家也累了,都去歇歇吧。”
众人不敢多言,纷纷走了出去。室内霎时变得极是安静,他站在窗前没有动,这几日的劳神让他身心俱疲,此刻听着雨声,倒觉得清醒了几分。
正兀自出着神,门口又响起了敲门声,林宁急匆匆的走进来,面色凝重的说:“七少,才刚收到消息,李新程联合以北一线的督军张培元宣布永州独立了!”
苏徽意这才转过头来,说:“将最近的兵力全部调集过去,各站的火车,路卡统统戒严。”他顿了顿,“把老二给我下到大狱去!”
林宁也猜想这里头八成是出了奸细,仔细一想,单单一个李新程并不足以煽动北边的旧臣,那么就只有苏青阳才能做到。
苏徽意皱起眉来,快步走到桌前,拿起布防图仔细看了看,说:“张培元此时宣布独立,难保南地其余督军不会响应他!马上以父亲的名义通电全国,先弹压住眼下的局势。”
他想着如今的时局,又说:“晚上接父亲到国府饭店,请几个可靠的报社记者随行。”
门口有卫兵喊着报告,“七少,乔先生到了。”
苏徽意示意林宁下去,说:“请乔先生进来。”
卫兵很快引了乔世钧进来,他在官场混迹多年,惯会做些场面,见了苏徽意,就客气的打过招呼。
毕竟是长辈,苏徽意也分外客气,一面同他打过招呼,一面引了他坐到沙发上,说:“乔叔,事从权宜,我这个做晚辈的不得已要将您请过来,有失礼之处还请你多包涵。”
乔世钧明知道这里头的弯弯绕,就点点头,说:“如今苏军在前线流血,我们这些商贾自然要出分力,只要您七少一句话,我们商会是在所不辞。”
苏徽意笑了笑,“乔叔是个痛快人,我也就不与你兜圈子,你也知道,自打南地与扶桑开战以来,两方僵持已久,这战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定的。即便是我们苏家,要做这个长期的打算,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他看向乔世钧,目光透着不容反驳的冷厉,“我的父亲身为南地的巡阅使,责任重大。力抗扶桑是无可厚非的,保卫百姓更是义不容辞。这些年,乔叔在南地商会如鱼得水,赚了多少钱我这个做晚辈的心中有数,虽说是各凭本事,但到底是在我苏军的地界,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我苏家军在前方流血牺牲,如何能换来现在的太平?”
乔世钧已然明白他话中的意思,略一沉吟,说:“七少说的我明白,这其中的难处我也理解,只是商会从来是一盘散沙,现在时局混乱,咱们这儿的好些商人都往北边去了,连带着许多银行都破产了,这一时之间要凑一大笔的钱,恐怕不那么容易。”
苏徽意早已想到他会这么说,就赞同的点点头,“乔叔说的是,我听说你们商会的张先生最近要准备出国去了?”
乔世钧恩了一声,“现在时局动荡,他们为着自保都要往国外去。”
苏徽意说:“这位张先生昨儿求到了我手下的参谋长那里,想要一张特别通行证。原本这样的事于我而言是举手之劳,可自打与扶桑开战以来,扶桑特务就屡屡入侵,以至于在排查这一块儿要求很严格。”
他拿起烟来点上,抽了一口才说:“张先生曾与扶桑商人来往过密,特务处那帮人查出那个商人是个特务,恐怕你们那位张先生是走不了了。”
他稍缓了缓,“其实,我想让他们掏钱,方法多的是。”
乔世钧听他这样威胁,只得转变了口气,“七少英明,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我辈理当出钱出力。”
苏徽意这才笑了笑,“乔叔,其实今儿是我们家老爷子想见你,不知你给不给这个面子?”
乔世钧诧异的看了他一眼,也不能拒绝,只得点了点头,踌躇了半晌,才说:“七少,之前犬子做的事太过混账,我也不敢求你消气,只能尽量弥补了。”
苏徽意慢慢的抽了口烟,窗外的雨逐渐大起来,噼噼啪啪的打在窗子上,和着角落里的落地钟一下一下响在耳畔,他只觉得心烦意乱。
稍缓了缓,才说:“现在战事吃紧,凡事还是以大事为主吧。”
微微吐出一口烟来,起身走到窗子前,就见大雨如注,那雨滴好似在空中打着旋,重重叠叠的缠绕着,他觉得胸口炙闷难当,好似有藤蔓覆上来。
天边暗沉沉的,尽头有一圈透白的灰色,虚虚笼着雨幕,像是夏日放在屋里头的珠帘子,他想起沈蔷薇很喜欢这些东西,每每看见总喜欢将珠帘子搁在指缝之间,来回的梳理着。
他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记起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只是这样想起来的时候,倒觉得又涩又苦。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林宁走到苏徽意身边,压低声音说:“七少,府里打电话说二姨太晕过去了,要请个医生看看么?”
苏徽意略一沉吟,就恩了一声。林宁又说:“老爷子已经等在楼下了。”
苏徽意边走边问,“岗哨都布好了么?”
乔世钧一听苏笙白就在楼下,当即站起身来,说:“既然大帅已经来了,我就先下去打个招呼。”
苏徽意带好军帽,看向林宁说:“送乔叔下去。”
他又抽了口烟,将烟头扔在地上踩灭,才穿上外衣,阔步走了出去。外面雨势极大,才刚出了军部,那雨便迎面落下来,他有几日没有休息过,此刻只觉得雨水冰凉,倒是清醒了不少。
一路走下台阶,青石板上都是积水,道路两旁皆是背枪的卫戍,这一条路早早就设了路卡,远远的,瞧不见一辆车,只是空旷的街道,直直延伸到那一头去。
天边的乌云好似触手可得,雨丝仿若青烟一般,又像是沈蔷薇用过的衣料子,触手又轻又滑,氤氲似的在眼前绕着。
他看了一眼,就上了防弹汽车。前头由卫戍队开路,一路风驰电掣着,街上的景物被雨水阻隔的看不真切,隐约可见几个行人。
现今时局动荡,金陵的人流也不似之前那般多,正街的商户许多都关了门,招牌在风雨中更显落寞,就连饭馆茶楼也是人烟寥寥。
他默默看着,才问:“那边一点儿消息都没有么?”
林宁知道他要问什么,就说:“七少放心,已经派了人过去,很快就会有夫人的消息。”
苏徽意微微合了眼,像是睡意袭了上来,只想就这样闭着。隐约听见戏曲的声音缓缓传过来,那声音婉转动听,只是被雨幕缠的朦朦胧胧的,听得并不真切。
恍惚间听得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荒烟蔓草的年代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死海.
- 简介:通缉嫌疑人//巨豪呆萌女.傲娇高冷受//主动温柔攻.——神探高智商//婉约女顾客.儒雅好先生//典型乖乖女.——军阀小大人//心动通缉令.可爱机灵鬼//爱笑蛇精病.——温柔多金主//可爱小顺女.商场不败王//行走江湖说.——顽皮小医生//可爱看诊你.多金多情商//撩人小心弦.——北川–允都–涴湖–淮园–糯楠楠:“靠美丽走天下吧!”/许汓作./
- 0.9万字6年前
- 梦梦头像店,壁纸等
- 简介:每一篇里面都有17张,要抱图的话就留言要帮你做一样的话,私聊了解一下你们写小说,我来开店想做头像的来找我,报酬一朵小花花
- 0.2万字6年前
- 第八号监狱
- 简介:第八号监狱,传说中的的神级监狱,里面的人,个个让人闻风丧胆,一个神秘女生的加入,让它变得有趣起来,关于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 0.1万字6年前
- 朴智旻:樱花般的你
- 简介:本作者圈地自萌的一对cp【朴智旻&名井南】青梅竹马&先婚后爱的故事~【圈地自萌,不喜勿喷】
- 1.5万字5年前
- 往后余生,请多指教.甜_d657
- 简介:双女主双男主宋祖儿王俊凯先婚后爱念辞易烊千玺甜蜜恋爱赵今麦王源霸道女友奶狗总裁
- 3.8万字5年前
- 坏坏爹地,请勿扰
- 简介: 有一天夜里,孤儿杨梓只是走在路上就被一群混混拦住。主要是那群人居然还给她下了药。 练过跆拳道的她很轻松地就将他们给解决了,后来,她糊里糊涂地和一个陌生男人睡了…… 五年后,回国的第一天她就遇到了当年的男人。接下来他们之间又会发生什么呢?敬请期待!这是一个坑爹宝宝与嘻哈爹地之间的友爱故事!(男女主双洁,萌宝助攻。)
- 2.9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