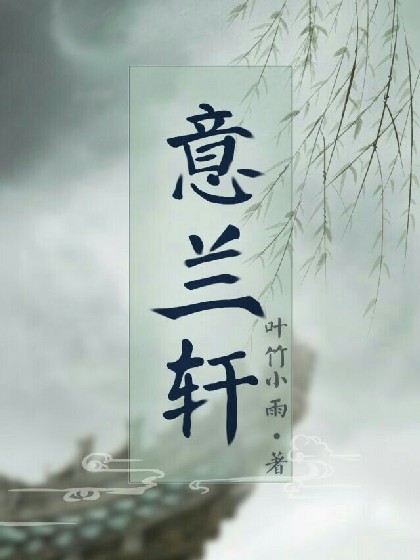第一章丧命
荀国,洛阳。
姜云妨蜷在屋檐下,间或抽搐着,如同一只濒死的蝉,抖动着自己单薄的双翼。雨水顺着瓦片的纹路,滴答滴答地,若滚珠落地。每当到了这样的雨天,她的膝盖便疼地令人发狂。
这是老毛病了。从自己嫁给萧容的第五年开始,便有了的毛病。
蓦的,静宜院的门被推开。云妨恹恹地,连抬眼都仿佛没了气力。这时候会来的,除了那个送药的丫头,还会有谁呢?
云妨卸下遮眼的白帛,模糊的双眼前,只依稀能辨认出是个窈窕女子的身影。不过这就足够了。
知道不是萧容,就足够了。
“王,王妃!您该,吃药了……”
春杏的一双手微微颤,将一碗汤药送到了云妨面前。
在她的耳闻之中,王妃姜氏,一直是个脾气不大好的人。王爷不喜她,便将她迁至静宜院,美名其曰是希望她安心养病,但其实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王爷已将她弃置一旁。
偌大的王府之中,真正有实权的,脾气真正好的,理应是那位白姑娘才对。
云妨扯扯嘴角,伸手接过汤药,只不过略略顿了片刻,便含着笑将汤药尽数送入腹中。
春杏有些好奇。她给王妃送了这么些日子的汤药,却也未曾见她发过半次脾气。永远都是留着笑意,将药喝得一滴都不剩。
她明明是笑着的,却让春杏感到莫名悲怆。
秋风瑟瑟地吹着,这可能是这个秋日的最后一场雨了,夹杂着寒意,吹的人骨头缝都生凉。
春杏接过碗,迟疑片刻,忍不住开口道:“王妃,要不,奴婢送您进屋吧。”
云妨摇摇头,将胳膊搂地更紧了些,她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忽而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叫春杏。”
“春杏,你帮我寻颗蜜饯来。“
顿了顿,续道:“……这药有些苦。”
春杏满头雾水,却也未曾怠慢,进里屋帮她翻了蜜饯出来。蜜饯似乎许久都没有人碰过了,附着一层薄薄的的灰。春杏咬咬牙,将它在身上蹭了蹭,给云妨送了出去。
蜜糖的香甜碎在舌尖,心里头却苦的发寒。云妨吃的有些急,猛地一呛,便有两滴泪湿了衣襟。
春杏见她哭了,慌了神,还未等开口问,却是她先发了声。
“……王爷,他回来了么?”
“还早。王爷同白姑娘在前线,分不开身。”
“还早……”她念叨了两句,似乎是忆起了那两张面容,挥了挥手恹恹道,“罢了罢了。你下去吧。”
春杏福福身,退了两步撑开伞离去。行至静宜院门前,她又转身看了一眼那个可怜的女人。
那个可怜的女人仿佛永远都或在蒙蒙地雾里,尘垢遮住了她的面容,但那双眼却明亮的可怕,明明视物已经十分艰难,却好似燃着一簇火。
一直都燃着那么一簇火。
若是火一直燃着呢?
留下的,是灰。
太医说,姜氏没多少日子的活头了。
王妃已经苟延残喘了四五年,这次,也一定会等到王爷回来的吧!
春杏轻声叹息,身影绰约消失在雨里。
云妨抹了抹泪,拾起白巾重新将眼遮上。
曾经的姜家,贵为四大家族之首,而她作为嫡出长女,更是满身荣华,不可一世。可能是前半生过分华贵,上天惊觉给了自己太多甜头,如今看来,竟是要收回这些甜头了。
姜家祖上出过三个皇后,所以十分重视对女儿家的养育。打小饱读圣贤书,于她来说,吟诗作对,附庸风雅,更是信手拈来。原本姜家人都以为,她的这一生会顺顺遂遂,兴许能成为祖上的第四位皇后,母仪天下,却在她十六岁时候一切都破灭了。
因为她遇见了萧容。
云妨每每想起那一日,都会发笑。起初是思念的笑,到最后,渐渐变了味道,成了嘲讽。
当时的自己,可真傻啊。
还记得那一日,重阳宴会,光影下彻,将席座疏疏而割,人影涌动川流不息,果酒的香气引人发醉,就在此时,有太监高声唱名:
“谨王殿下到——”
她抬眸望过去,有少年分花拂柳而过,光影斑驳,碎在他的发上,他眉眼淡漠,嘴角微扬,长揖而言:
“臣弟萧容,拜见陛下。”
“哎,谨之可是迟了,重阳盛宴,难道不应给先自罚三杯,聊表歉意?”年轻的帝王笑道,虽是疑问,但是动作却不容置疑,命宫人奉上了三盏酒。
萧容没有半分迟疑,笑得比那位帝王更加灿烂,借过酒,送至唇前。少年实在是美得很,很少能有人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此时便顺着他的举动将眼移至他的嘴前,却没想到少年呼啦一声撑开折扇,将酒饮下喉头。
众人这才猛地回身,讪讪将目光收回,脑中却始终盘桓着那殷红的薄唇。包括云妨。
这时云妨的母亲低低赞道:“这谨王将来必定是个大人物。”
云妨生怕泄了自己的心思,小心翼翼地问道:“何以见得?”
“忍常人之不能忍,只怕鲜少有人做到。”
萧容的确是个很能忍的人。表面上虽是一身风流恣意,心里却工于谋算,不过短短两年,将自己的政敌铲除了个一干二净。他时常拜访姜家,顺理成章的,陛下以为萧容对云妨有那么些意思,便将云妨许配给了他。
现在想来,喜欢与否,未曾可知。
五年夫妻生活,琴瑟合鸣,萧容的仕途一路畅通,到了就连帝王都得敬让三分的地步。云妨也仿佛日日都泡在蜜罐子之中,活得不知愁苦滋味。唯一的遗憾便是没有孩子。萧容说,他现在还不需要孩子,他只想和云妨两个人,先这么度过几年。
思至此,云妨忍不住嗤嗤地笑了起来。当时的自己太过于天真,信以为真,又哪曾想到陛下以多年无所出为由,将白氏赐给了萧容。当所有人都知道白氏的存在之后,云妨仍被蒙在鼓里,直到萧容连续半旬未曾归府,云妨才得知,他在白氏的别院栖着。
五年恩恩爱爱,敌不过他人一朝介入。
她努力去挽回。连绵阴雨之下她在皇宫跪了三夜无人理会无人问津,夜夜翻看情意绵绵地家书也不过是徒增哀伤。
再后来,她才可笑地发现——他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
到底是什么时候出了问题的呢?她努力地去填补两人之间的漏洞,却发现这个漏洞太大了,空荡荡的,一切都是徒劳。
她收拾东西,欲离开洛阳,却在离开城门口不远处被他派人拦下。这是她时隔三月,第一次见到他。他不再是她记忆中那副模样,略显憔悴,猩红着双眼,捏的她肩膀生疼。
他一遍遍地重复着。
“云妨,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为什么连你也要离开我?”
她几乎是被拖拽着带回谨王府的。他将云妨压在身下,随之而来的便是急风暴雨,没有解释,没有半分解释!
她多希望他能解释个只言片语,哪怕是骗自己的,她也愿意相信,且甘之如饴。
可惜,没有。
翌日,身边便是一片冰凉。也是从那日起,他派人将她软禁了起来,打着疗养身子的名头,日日送来一碗汤药。
明知那是催命符,她还是含着笑,将它一口口吞下。
这可能,是对他最后的爱意了。
白氏是个好女子,云妨会的她都会,云妨不会的,她依旧会。
她会在危急关头发明水车,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亦会在宴会上吟诗首首,不假思索,辞藻流畅华美。武可陪君战场杀敌,做一对沙场鸳鸯;文可叱咤朝堂辅君步步高升腾达飞黄。
她姜云妨究竟哪里能比得上这样的女子?
她比不起,半分都比不起!
白瑾妍便是观音活菩萨,她姜云妨只不过是个闺阁花瓶罢了。白瑾妍容貌清丽脱俗,而她姜云妨,不管再美,都是艳俗。
那好啊!我承认了你比我好,好的太多太多,那便不要抢我的夫君好了吧?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放过我?步步紧逼,将我身边的东西一点点夺取。
我只有他,只有他了!
爹爹死时,她哭着哀求萧容,求他救救爹爹。萧容说你不用担心,我会救下他的。
后来,爹爹死了,病死狱中。
哥哥被人冤枉通敌叛国,她跪在萧容书房前,祈求他救救哥哥。萧容说,你不必担心,他不会死的。
后来,哥哥死了。除了她,姜家都死了。
满门抄斩。
集市斩首那天,她亲自观刑,官兵将她拦在场下,一口一个王妃。
是啊,若不是因为她是王妃,今天死在这里的,也有她的一条命。
可是所有人都死了,她一个人,一个人守着王妃的名头,又怎么能活下去呢?
刀起头落,她晕了过去,醒来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萧容。
她揪着他的领子,哭的撕心裂肺。
“萧容,我只有你了……”
萧容,我真的只有你了。
为什么就连你,也要离我而去了?
白瑾妍的家族迅速的取代了姜家,成为了京城第一大族,白瑾妍也成了上流贵族之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得贵女。
可是这样的女子为何要同她来争抢萧容?
天下男子千千万,为何白瑾妍看上的,偏偏是她的男人?
这个问题纠缠了云妨四年。她恨,真的好恨,恨也没用,怨也没用,梗在心头,积怨成疾。
不过——这一切很快就可以解脱了。
她没多少日子了。自己的身子,总归自己更清楚些。
寥寥半生,荣华富贵过,潦倒混沌过,死了,只怕是一曲烟云而过。
这恐怕是她的劫。无论是白瑾妍,抑或是萧容,都是她姜云妨的劫。
“若有来生,若有来生……”
若有来生,该怎样呢?
把他抢来?
成为他的阻碍?
不!不能这样了!
那样,太累了。
那便这样吧。
若有来生,只盼我们无处相遇,无缘已对。
永乐十三年,初冬,王妃姜氏殁。
誓不为妃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意兰轩
- 简介:乱世之中,风华嫡女,又能创造出几番人生?后宅之中又能藏起几颗慧心?嫡庶之别,又有多少差别?一朝重生,唯独看不透自己的命运是否又是另一种悲哀?桃花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我想描写的不仅是嫡女成长记,更是一个家族的兴盛史。
- 1.3万字6年前
- 一品弃妃:冷傲王爷的囚宠
- 简介:【已完结。12月订阅所花KB会全额返还】他娶回她,只是为了报仇。不过是一抹温情,冰化了她那颗冰冷的心,最终,她沉迷在了那场有预谋的从未享受过的爱恋中。可是,到头来,才发现,这一切不过是场云烟……“我们的孩子,还未出世的孩子。这礼物……你可满意?”那日,他迎娶正妃。她含笑送上自己的礼物。满室的血腥味,他大惊。“如你所愿,我爱上你了!”锋利的匕首刺进胸膛,她笑着流出血泪,满目苍凉。百里沧溟,你既不仁,休怪我不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群号:185636788敲门砖:任意角色的名字。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73.9万字6年前
- 延禧:穆弘恋
- 简介:这里是顾穆甯与弘历之间的爱情,当弘历是宝亲王的时候与穆甯是情侣关系,后来弘历登甚,娶了富察容音后,又高宁馨……最后弘历与穆甯在一起……
- 1.3万字5年前
- 陈情令-含月君驾到
- 简介:十六年前,姑苏蓝氏诞生了一位小姐叫蓝萱字忘雪。他有两位兄长(蓝曦臣和蓝忘机),他还有一个叔父(蓝启仁)。听有些人说:“姑苏蓝氏三小姐,美若天仙”,还有些人说:“他一岁弹琴,两岁就能练剑,三岁单手写,四岁就会被家规,五岁跟随两位兄长下山”。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 13.8万字4年前
-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折汐恋
- 简介:封面仅供参考,折颜(你笑一次,我就可以高兴好几天;可看你哭一次,我就难过了好几年)白汐(我并没有喜欢哪一种类型的人,如果我喜欢你,我喜欢的就只是你。)
- 3.5万字5年前
- 楚国佳人
- 简介:楚国正一品定国公之嫡长女云琬倾楚国皇帝之嫡子(皇四子)池墨宸此文纯属娱乐!!!
- 2.2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