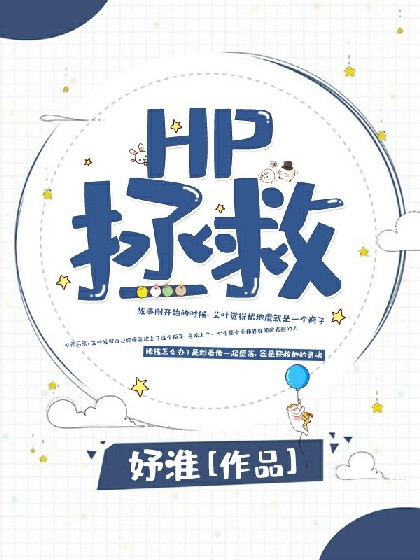第五十一章 相国
秦皇崩逝后的第二年凛冬,百年难遇的大雪笼罩了中州腹地。
距横断山脉千里之外的帝都青阳,此刻仍是一片暧昧不清的灰红混杂,瘦硬的冷风荡起暗白的尘土,旭日的红光倾泻下来,苍苍茫茫的城池屋脊、山河红颜便在这一片骤然升起的红光紫雾之中若隐若现,直像是流光溢彩的天上街市,降临在眼前这片恢弘而致远的碌碌尘寰,白光绚烂,金红交织,怪异得让人目眩神晕。
随着近年来的北方局势动荡频现,常有北境蛮族越过苍莽无际的冰魄之海南下叩边,致使帝国北部烽烟四起,民不聊生。此刻,整个古老而安逸的城池却仿佛一座巨型的要塞堡垒,沉默地扼守在蜿蜒曲折的汾水南岸。
出得南门,掠过一片植满枫林的矮小土丘,方圆数百里的芜湖便宛若一颗璀璨的明珠,正正点缀于城市的南端——作为秦国的心脏与命脉,青阳北临汾水,南拥芜湖,既有农田灌溉之利,又有商旅舟楫之便,其繁华与兴盛便如命中注定一般不可遏制地绽放开来,与汾水北岸的宜阳、荥阳二城遥遥相望,共同支撑起了整个丰饶繁盛的万里秦川。
此时的芜湖再不复往日的波光粼粼,罕见的霜冻与大雪轻易将这座一望无际的大湖化作一片纯白的平地,与远方的山林田畴施施然融成一片,消逝在苍莽无际的天地之间。
在这天寒地冻的朦胧初晨,却赫然有着一叶扁舟静静荡漾在方圆三丈有余的狭小水面上,一位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老翁正独自于漫天风雪之中盘膝垂钓,一双丹顶白鹤拂过翠水,掠过白冰,轻盈地落在老者的身侧嬉戏玩乐,不时发出几声欢愉的低鸣。
远方蜿蜒的官道之上忽然响起一阵车马粼粼的细密声响,轺车檐角清脆的铜铃击响在凛冽的风中,稀疏而拖沓。
老者手中细长的竹竿蓦地一颤,身旁的云鹤仿佛察觉到了危险,惊叫着振翅而起,盘旋于风雪肆虐的长空之下不敢靠近,亦不愿丢下静坐的老翁就此离去。
车马未至,一道低沉而威严的声音却已拂过耳畔,令人不禁心生震撼,“相国大人倒是好生自在,似这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着实令老夫艳羡万分呐。”
老者双目微眯,沉默片刻,头也不回地低低说道:“将军言重了,如今这天下之大,能容老夫的也不过这三丈见方的小小湖面,又何来闲云野鹤般的逍遥与自在。”
“相国大人何出此言?”来人缓步上前,垂首看了眼冰原中央赫然裂开的狭小湖面,摆手笑道:“若是大人所想,便叫老夫肃清整个芜湖的三尺寒冰,又有何难?”说罢,便欲运起斗气震碎脚下冰封的湖面。
老者微微摇头,低声开口:“将军心中早已明了老夫心意,又何必再做那等无用之功……”
“既然如此,想必相国大人也已清楚在下的来意。即便行之无用,但只要能让大人满意,本将也自当尽力而为。”
来人话音一顿,望向天边久久不去的一双云鹤,微微一笑,“没有人束缚着它们,它们却因心系先生而不愿离去,那么先生在此独守,又是谁……牵绊了先生?”
船头的老者身躯一颤,苦笑摇头:“过了这个冬天,老夫便要一百一十五岁了,作为一个无法修炼斗气的平凡之人,早已是半只脚踏入了棺材里,将军这又是何苦来哉……”
“非是我要为难先生,实在是帝国北部万千子民离不开先生……而先生,亦是不忍弃万民于水火,就此挂冠离去的吧。”来人厚重的铠甲在晦暗的天光下闪烁着渗人的寒芒,却没来由地令前方的老者心中一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倏忽逝去百年的戎马岁月不禁又在他的脑海之中清晰浮现。
那时的他也不过是一位堪堪十五的瘦弱少年,只因家境贫寒而投身军旅,不求保家卫国,但求三餐温饱。灵根全无的他注定只能作为低贱的炮灰勇往直前——血肉横飞的战场无疑是他最后的归宿,不过早晚而已。
他如是想,直到他遇到了身后的将军。
那时的将军,也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穷小子罢了。
同样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夜晚,全军三千残部尽皆受困于岭南潮湿寒冷的险山密林之间,骁勇善战的秦国锐士也终于尝到了南诏丛林猎手的阴狠与毒辣。
“这里的林木实在太湿了,无法生火……”瘦弱枯槁的他嗫嚅着苍白的嘴唇向黑暗中的队正颤声汇报,下一刻迎来的便是意料之中的,疾风暴雨般的鞭挞与辱骂。
“一个斗气全无的废物,老子带着你还不如带条狗有用!”队正一脚踹翻了垂首跪地的虚弱少年,虽然力道不大,却足以令两日未曾进食的他摔得五脏翻涌、天昏地暗,堪堪滚入一旁冰冷的雪堆之中方才止住了去势。
“快拿干粮来!”队正啐了口唾沫,伸手一摊,朝地上蠕动的人影恶狠狠地道。
他身躯一颤,晃晃悠悠地从雪中爬起,裸露在外的双臂与脸颊冻得紫红。
“还不快点儿,嫌鞭子吃得不够饱么?”
“啪”得一声脆响,犀利的寒光在他的身侧带起一道苍白的雪线,冰凉的劲风刮得他面颊生疼,如遭刀割。
“方才……方才突围的太过突然,干粮,干粮都……”少年面如死灰地跪在冰凉的雪地之中,出于对死亡本能的恐惧令他话语闪烁,吞吞吐吐,竟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诡异的沉默瞬间笼罩了整个狭小的营地,这一回,便是其余围坐一旁的军士,也在此时齐刷刷地向这个虚弱的伙头兵投去了饿狼般冰冷的目光。
“你好大的胆子!”一道高大的黑影瞬间掠近,轻易覆满了他狭小的视线,耳畔刮过凄厉的寒风与狂怒的低喝,“干粮丢了,你怎么没丢,是要叫我们吃了你吗?”
他只觉浑身一轻,随即落在更远处的一株雪枫之下,阵阵霜雪抖落,掩盖住了他瘦弱的身形,他却感觉到一阵诡异的温热捂暖了胸前,他微笑着伸手轻轻拂去,只觉入手处湿滑一片——那是他吐出的热血。
渗人的呼啸声再度响起,他清楚的知道,队正的这一鞭足以夺去他脆弱的生命,他的嘴角缓缓露出一抹解脱的微笑,天地间的风雪仿佛也在此刻凝滞,静默地迎接他归入轮回的那一瞬的到来。
“还请大人听属下一言。”尚显稚嫩的声音蓦然响起。
想象中的剧痛并未到来,恍惚中,他睁开模糊的双眼,一只同样瘦弱的小手竟生生捉住了那支悬在空中的金鞭,温润的细微白光萦绕在那人苍白的掌中。
那就是……所谓的斗气么?
他心中苦笑。
“是你?”队正一愣,面色冰寒地望向突兀站出的少年,“你要替这个废物求情?”
“大人,眼下军粮尽失,即使我们皆有斗气傍身,却也绝难在逃亡中撑过七日,而眼下大雪封山,大将军的援军至少还要半月方能入山驰援。”那人回头望了眼树下虚弱的少年,缓缓松开手中的长鞭,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
“老子当然清楚得很,用不着你小子在这儿废话。”队正冷哼一声,卷起长鞭微微冷笑,“你说这些又有何用?“
少年叹息一声,向前躬身一揖,“属下还记得上回突围所走之路,愿意与他一同寻回物资,将功折罪。”
他不太记得自己是如何从那处吃人的炼狱逃脱了出来,只依稀想起一只带着腥红鞭痕的瘦弱小手紧紧抓着自己的小手,背着自己羸弱的身躯辟开漫漫长路上肆虐的风雪。
“给。”他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枚冻得硬如石块的干饼,得意地笑。
“你……”少年略带迟疑地接过,不自觉地舔了舔干燥开裂的嘴唇。
“嘻嘻……我才不会……给他……我们,再也不回去,好么?”他目露渴望地看向低头不语的少年,满脸希冀。
雪势渐大,遮天蔽日,耳畔是风穿过山林呜呜地狂吼,黑暗里,他看不清他的脸,只是那双握着自己的苍白小手捏得分外用力。
时光荏苒,倏忽百年过去,昔年的两个贱如草芥的贫苦少年此刻早已脱胎换骨、位极人臣,只是这一路上的披肝沥胆、舍生忘死所换来的一切究竟是否如他们所愿,或许也只有他们自己心中明白。
“若换了今日的你,那一夜,你还会选择回去么?”老者凝视着幽深的湖水,低声开口。
来人微微一颤,深深望向那道苍老的背影,视线在刹那间晃了一晃,昔年那个走出阴霾、意气风发的少年仿佛又从时光的水镜之中走了出来,微笑着问他。
现在的自己,又该如何选择?
“裴毅……”来人轻声低唤,看着那道忽然颤抖的背影,摇了摇头,喃喃低语,“我们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们……”
“这大秦,也早已不是往昔的大秦……”老人声音迟缓,手中的钓竿在风中轻颤,“自先皇逝去的那一刻起,我的心,也早已随之而去……你知道么?北境的蛮族也好,雷族也罢,可怕的从来不是来自外部的强敌,而是我们自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狼性……太上皇的优柔寡断,整个帝国朝野的麻木不仁,又岂是我这个行将就木之人所能轻易改变的?有我没我,一个鸟样罢了。”
“不是我们变了,是这个天下再也容不下我们。”老者望着远方苍莽的天际,喟然长叹。
奇异的沉默笼罩了风雪中的二人,天上的云鹤在空中徘徊,不时发出几声低沉的哀鸣。
“我记忆中的裴相,断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将军微微摇头,肃然低声:“即便我已不再是我,不会为了所谓道义再豁出性命原路杀回……我的改变却仍是为了我们的家,为了万千子民能够安享太平,而你……”
“你却真的,变得不再是你……”将军一挥腥红的大氅,厚重的铠甲在风雪中敲击出铿锵的声响,“裴毅,我只再说一句,太上皇已秘密前往接回青妍殿下,并决议废除婚约,你……好自为之吧。”
“你说什么?”老者愕然。
“我没工夫同你说笑,眼下宫中那位雷族少爷可不好伺候,还有一堆事关北境难民的烂摊子,这便回了。你……继续钓你的鱼吧。”将军不耐地挥了挥手,一掀幕帘入了车架,倏然消失在远方灰白的官道之上。
“站住!曹炎烈,老匹夫,把话说清楚!”老者霍然起身,险些一个站立不稳跌入水中,空中的云鹤灵巧地跃至老者的身侧,一左一右将他从晃悠的小舟之上轻轻托起。
他手中的鱼竿在此刻蓦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抖动,老者意念一闪,猛地一提手中纤细的竹竿,却见银线末端笔直的金钩之上赫然咬着一尾肥硕的锦鲤,挣扎着带起一串晶莹的水花,在初晨的阳光之下熠熠生辉。
斗破苍穹之魂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美色封面铺
- 简介:在店内制作封面免费♡关注店长♡收藏店铺♡完成指定的美工要求即可取关取收可耻.-需要请按格式在评论区下单♡格式见章节①『店长的话』-店长:苏幼幼铺内美工:苏幼幼,张却安,姜幼恩,匪欢,良夜辰,边小白,墨丞,楼柒,冷兮,悠天然,初妃落兰,败凉安,夏时橙,顾漫卿,沈怡冉,雅辞,楠钥,云朵,沈欲,沈南辞,十里霓裳,虞欣,玖希笔芯♡画心心♡
- 1.7万字5年前
- EXO血瞳异能者
- 简介:活着太累了
- 10.5万字5年前
- HP拯救
- 简介:故事刚开始的时候,艾叶觉得伏地魔就是一个疯子。可是后来,艾叶发现自己好像喜欢上了这个疯子,喜欢上了一个令整个巫师界都闻风丧胆的人。她该怎么办?是跟着他一起堕落,还是拯救他的灵魂?[剧情很雷,不喜误入][穿越女主cp伏地魔]作者原创,禁止转载,抄袭谢谢!
- 24.8万字5年前
- 我是砒霜,她是糖
- 简介://糖和砒霜二选一,世人皆选糖.//可又有谁知道?砒霜也曾是糖.//只是历经风雨。成了毒药./噢,是的,我是砒霜,她是糖./所以,你会陪我吗?—千万别像猫一样,在风雨中长大。遇到点爱以为是家。-//友情客串:Moon月,灼北阳,苏言沫等.〈书群:167733453〉【九创文社:韵昔】【2018.11.01签约】【2018.8.7删掉所有章节重写】【原创望喜.❤】●已签约,禁止转载or借梗●不喜勿喷
- 25.9万字5年前
- 开宝之一生所爱为梦而来
- 简介:不告诉你!自己看去!(本文不虐)
- 2.4万字5年前
- 大唐女法医之念念不忘
- 简介:要说这偌大长安城内最幸福的女子那必是京兆杜氏的小娘子——杜念妮!其父杜如晦乃是当朝右仆射,大哥杜构官至尚舍奉御,二哥杜荷迎娶了城阳公主封为襄阳郡公,杜小娘子也被封为知韵郡主,长姐杜心仪嫁于兰陵萧氏萧颂,萧郎君对妻子极为宠爱,对她这个妹妹自然不差,可惜杜心仪杜娘子去世的早,这原本天造地设的一对也就阴阳相隔,萧郎君也是长情之人,对杜小娘子也是照顾有加。就是这样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子,却是爱错了人!
- 1.9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