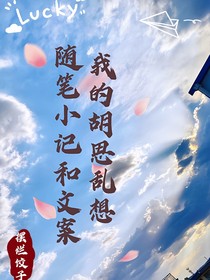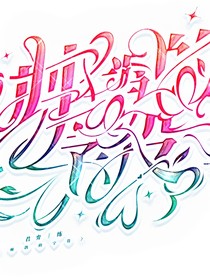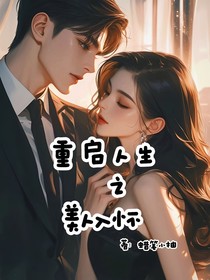37
【《无量空处:以普遍怀疑质精神病理》,文刀十布,2024.4.1】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人物质疑整个世界合理性的作品,比方说虚拟现实题材的开山鼻祖《克莱茵壶》。这些作品中人物对于世界的质疑在笛卡尔的《沉思集》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工具,是发挥《沉思集》思想根源作用的奠基石,是被笛卡尔称为“普遍怀疑”的方法。
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疑团,有些“神创论”者说在地底发掘了五十万年前的子弹壳,还会问出“月亮为何恰好放置于一个充当地球防御位置的轨道上?是有人把他放在那儿的吗?”这样的问题。科学的拥护者们当然会坚定地声明子弹壳是假新闻,并用万有引力公式解决第二个问题,但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来思考,无论是探究子弹壳年份的半衰期还是万有引力公式都基于数学,而数学则在此前提下难以置信。这便是普遍怀疑,颇有些“从来如此就对吗?”的意思。他怀疑的是人外部的一切。
限于我个人水平的桎梏,我今天要说明的并非是月球到底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秘密,也对于弹壳到底年方几何不感兴趣。我今天要质疑的是精神病的病理。
精神病,这个“病”字就已经表明医学研究者在坚信既存科学的情况下给出的定义:这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现象,是大脑或器质性或精神性的病变。不仅如此,他们还给精神病下了“难以治疗”的定义。虽说是难以,但这个限定词是基于既存科学在未知或未全知领域中的严谨性给出,,实际上大部分人在看到精神病时第一反应想的是“无法治愈”或“无可救药”。
本文质疑“精神病是无法治愈的有害病变一事无需再言,话不多说,现在开始应用普遍怀疑。且让我援引某动漫作品的一句台词:
“领域展开·普遍怀疑”
根据《沉思集》的内容,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思考,因而发出思考的我们也随之确定,即“我思故我在”。那么我作为一个可以确定的事物对我之外的一切命名——“无量空处”:即“我”那充斥着无法相信之混沌的容身处。在这混乱而不确定的地方,精神病是病变这一件事已经不再成立,现在以“我”之思考导出对其质疑的确定性:
第一,在未应用普遍怀疑前,人们对于精神病的认知基于观察,无论是对病人行为的剖析还是对其死后大脑的解剖,其研究方法是观察,而在无量空处,由于外物的不确定性,观察是不确定的。因此,对精神病理的普遍认识从方法角度不确定。
第二,人们对精神病人眼的思考知之甚少,皆凭借自身认识来推断。而精神病人的思考作为确定的事物被不确定的证据描述,显然不合理。故其从证据角度不确定。
如此可以认定先前认识在无量空处被推翻。现在开始重构其定义。
首先从“我”的角度,也是目前唯一确定的角度出发。我们每天都有许多思考,其中有一半以上指向一个共同的基本思考——“我该怎么活下去?”比如“我中午吃什么?”、“我上哪儿搞钱?”等都属此类。因此“我”要活下去这一点对于所有人来说全部确定。那么人的所有行动亦为此而动亦可以确定。大义凛然的烈士并非不惜命,而是为了心中的信念,也就是更为坚定的思考向死而生,自杀者的自杀行为基于“我死后会解脱”,其本质是希望自己前往另一个世界活着。
那么多出现于强烈刺激、重大灾难后的精神病,在此语境下成为“帮助患者活下去的行为”。听起来很大逆不道,那从无量空处取几个基于思考的,即确定的例子来证明:
一常年被家暴的孩童产生一个攻击性极强的第二人格,为何?因为孩童为了活下去,产生了“怎么样才能打过家暴者”的思考,当这思考改变了大脑时,第二人格接管身体反抗家暴。一医泽四方的中医在被批斗后产生创伤型应激障碍,只要和“红”有关的东西都能吓得她大惊失色慌忙逃窜,为何?因为她被红战士批斗惨了,她害怕了,她想活下去,一定要躲过他们。
这么一看是不是很合理?
现在让我们解除普遍怀疑,在已经被笛卡尔确定的现实世界中研究刚才得出的结论有何意义。既然精神病是“为了让患者活下去”的手段,那我们是否可以用某些方法让患者相信其他的一些手段能代替精神病让他们活下去以此来治愈精神病呢?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会知晓。
雷声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我的睡前脑回路
- 小短篇,文案,小故事
- 3.0万字4个月前
- 君某人的无偿封面铺
- 君某人的封面铺(含教程)没关铺,就一直接格式:作品:作者:类型:网站:小字(素锦必填):花/简约∶底图:自带尺寸:不支持加急,心情好的话会给......
- 2.3万字4个月前
- 龙珠:开局布玛成了我女友
- 穿越七龙珠世界,原来是宝箱系统带着他穿越,让他更意想不到的竟然是还有一个系统。 别人来到龙珠世界都是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我是......
- 7.4万字4个月前
- 重启人生之美人入怀
- 爸妈去世,目睹女友出轨,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舒朗还没来得及打脸渣女,就发生了车祸。一场意外,让他重回了高中,这一次,他决定再也不当舔狗了。舔?......
- 10.0万字3个月前
- 虎脊
- 本书以中国东北虎为视角。先以野东北虎白山,从出生到成长,成为一代虎王的一生。后面延续到我国虎文化领域。来展现我们中国独特的虎文化图腾。
- 2.8万字3周前
- 火凤凰:接过使命与荣光
- 接过这把钢枪,就像接过使命与荣光!CP哈雷
- 7.8万字3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