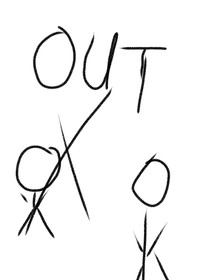seven
其实要说不满,她也没持续多久。反倒是他,更变本加厉了。
同一天一晚下,是八点二十。她照例去送他回家。其实在这个时候,她与他即便是不公开,旁人也都知道七七八八了,她也厌烦躲躲藏藏,那总有一种黄子韬和徐艺洋的感觉,索性就再没管八卦那档子事儿了。
她在连廊里看到了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坚固的冰敷在上面,化不开,打不破。她也就没说话,只是沉默着走在他的身边。
对了。她率先开口打破了死寂的尴尬,今天晚上没办法跟你聊天了。
为什么?他的声音哑着,像是在雾霭里浸润过一样。
平板出了点问题,没办法登帐号了。她说的的确是事实。
拿来,我给你重新登上。他没看她。她忽然间排斥起来:不用了,不聊就不聊了。
不行!去取。他的语气里带上了命令,毋庸置疑。
她到底还是取来了。她看着他弄着平板,走在路灯微弱的校园里。她近视,五百度,在黑夜下自是看不真切,更别说还叠加着散光。隐隐约约,她听到了些许嘈杂的声音,大约是初中生,也在微弱的道路里散步打闹。她根本就没想过那群孩子是过来惹事的,进而也出现了糟糕的结果。
他们挑衅他,用激光笔晃来晃去,红色的点,激发了鲁莽的野兽,鸟惊鱼散,也终没躲得过兽的速度。
他们与他打架了。她看到他将一个孩子撂倒在肮脏的被千人踏平的地面上,掐着那孩子纤细的脖颈——他真是疯了!她使出最大的气力去拉开他,她一遍又一遍的喊着他的名字——阳,阳!
那真是糟糕透了。她失去了所有的语言。她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样的闹剧,每个人都在辩解着自己,都认为自己没有错。
黑色喜剧。
就那么闹到上了二晚,她飞奔向教室,将他扔在无边的黑暗里。
她突然间想尝尝烟是什么味道。她的姐姐,在她面前唯一一次抽烟,是看到他跟在她的身后来见面的时候。她看着自己最爱的姐姐亲手打碎了完美的滤镜,夹着烟尾,吐出团团烟雾,笼罩住背景,映衬着如同致命的罂粟花,不可方物。那或许也是一种麻痹地盯着自己陷入泥沼的濒死感。
混乱。熵增。
一整个二晚,他都在跟她争吵。她根本就没有办法安心学习,没法逃入自己的心房去整理这一切。他步步紧逼,句句指责,质问她为什么抛下他回来上二晚,质问她是要他还是要学习,质问她为什么没有帮他......她气得浑身发抖。
你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她笑了一下。用落差来形容最为合适了。她一整个二晚都听不进去他的委屈,他的指责,他的烦躁——她只是在退让,在道歉,然后无力的下垂,憋住了懦弱的眼泪。娜,她的朋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帮着她吵架说理。娜只是单纯的看不下去他那么令人无语而已。她很感激娜。
他说他过几天带着几个人把委屈还回去。他说他已经拉了几个兄弟了。他说他初中又不是没约过架。他说他根本不怕。他说她一点都不偏着他。他说他买的那些良品铺子是他攒了好久的钱。
没有梅子。倘若他当时不强硬着要给她买,她根本不会开口去要。
她不能猜透自己当时的心情。她只觉得天旋地转。
她翻开英语报纸打算写B篇阅读,发现没办法静心写作业。还有一百二十天就要高考了,寒假也就只有短暂的十一天。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间想起这些争吵,她看向窗外下过雪后依旧没有白色的路面,淡淡的忧愁侵入了她的眉头。
她不知道每一片雪花下落时在想什么,她也不知道云层之上是否真的住着亡灵,她更是不知道每一颗流星是不是故去的亲人所捎来的祝福——一切都是秘密。她到底有没有了解过这般灿烂寂寞的世界?她到底有没有勇气来直视过往,现在,与未来?她会不会在自己死去的时候依旧承受着回忆的焦灼与痛苦?
她只想喝一口孟婆汤,重新铺白绢纸。
她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继续送他回家,继续在平板上聊这聊那。过了几天,也就真忘了还有打架这一回事了。可她的右眼皮从她与他谈了开始就一直在跳,从未停歇。不出一周,班主任找她谈话让她不要谈恋爱,甚至在课堂上阴阳她被外表迷惑蒙蔽。说不难过那是假的。
每周天下午她都会返校去跟他见面。她将东西放在教室里,就转头出了教学楼,出了校门口,坐上他的电动车后座。
走吧,兜风。她掏出耳机插在MP3上,点开了边伯贤的Ghost。
成,兜几圈。他转了一下把柄,车轮胎轧过柏油路面的渣滓,风越过他掀起了她的发丝,灌入了她的衣服。她松松的环着他,任凭自己的思绪沸腾在一穿而过的空气里。夜晚的灯光总是奢侈的,她只能看见他的后脑勺。他的头发长了。
人在一秒钟里能想很多事情,抓住它们的概率小之又小。
只有空白,也只能想起空白。
如果这就是爱,那喜欢算什么呢?如果这就是喜欢,那怎样的有算作是爱呢?凭借那点可怜的岌岌可危的信任?那只是不在意罢了。
他说他自从与她谈了之后,就没怎么跟女生聊天了,说是要给够她安全感。她也从来不去翻他的手机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她拿着他的手机就只在B站上搜视频看。她并不喜欢窥伺别人的隐私——这跟她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她是没有什么隐私的,因此她不喜欢去看别人的手机,探查别人的隐私,同样的,她也很排斥别人看她的手机,包括他看她的聊天记录,每一个人,每一条消息地往过看。她刚开始的时候有反对过,可是终究气力不如他,让他抢了去。他的咄咄逼人,他的霸道,他的无理——她也就当他是个孩子了。可其中的苦涩,他根本不懂。
十一月份期中考试结束,分班的决定依旧没有出来。他十分着急,每一天都在给她发消息说分班会怎么样,能不能跟她在同一班。她每一次都笑着安慰他,不管在不在,学就是了,高考才是最终的目标。
又不安稳的过了一周后的周六,普通的早读,迎来了突然的分班通知。连同她在内的班级前十二,调去重点班一班上课。而他依旧在五班待着,连进次重点二班的资格都没有。他又是着急又是生气,连连去找年级主任说这不公平。
这是规则。学校是制造规则的人,学生们又能如何呢?不过,这确实在意料之外,她以为重点班的排位是不会有变化的,依旧是两个重点班。可这样相当于只摘出来了一个重点培养的班级。
这是这样的一个变动,她跟萌开始做同桌。
一班的第一节课,是数学课。数学老师,也即是班主任,讲得飞快,像是有人在后面追赶着一样,她只能捕捉到只言片语简单的记下来课后研究。快多了,每一节课都是无比的快,她开始担忧自己是否能适应这样高的强度,两节晚自习整整五个小时,作业都没有写完,更别说自己刷题了。
她瞥了一眼萌。萌适应性很差,已经哭了一天了,她很担心萌的状态。
分完班近一周,她白天安慰萌,晚上在平板发消息安慰他。她觉得她被撕成了三个碎片,剩下的一个默默地整理自己的恐惧与焦灼,让自己尽快调整状态,回到正轨。
无缘轨道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如宁相救
- 双女自行林楠有些惊讶,抬头看向沈妤风吹起沈妤的头发沈妤笑着看林楠脸颊泛着红晕林楠靠近沈妤手放到了沈妤手上从沈妤的视角看,光从林楠的背后照着林......
- 7.2万字4个月前
- 总裁,小猫又躲起来了
- 简介正在更新
- 0.5万字3个月前
- 我不是傻只是舍不得
- 十八岁的成锦杭正值青春年少,却遭遇了人生中的重大变故——父母离世。从此以后,他的世界变得灰暗无光。然而,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这个可怜的孩子,他......
- 6.8万字3个月前
- 栖梨花
- 从2010年老宅绣球到宇宙级蓝晒,从个体记忆到文明基因,最终回归
- 6.4万字2个月前
- 杉栯
- 青梅长大,俩情相悦
- 0.3万字1个月前
- 无恙人间
- (非传统末世文,主角病但不弱,有副CP)“暴雨来了,迟早有一天所有人都会被暴雨回溯”人们坚信是暴雨把人回溯了而并非是世界抛弃了我们。一切都是......
- 0.7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