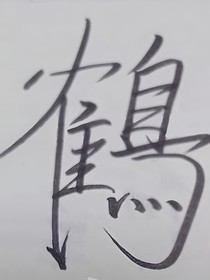第二百二十九章 荣兄
“我没有罪……”
一滴泪滑落男子的脸颊,尽没于他青涩却生了凌乱胡须的下颌,他空洞的眼睛直直地凝着牢狱的栅栏之外,一身狼狈的血污。
牢狱的大门吱呀响动起来,惊得老鼠“吱吱”乱窜,那青年猛然扑向门的方向,颤抖地辩解道:“父亲,父亲,我没有罪,我没有罪!”
已至关押荣兄牢房,我堆了堆地上的干草,坐了下来。
见是我,荣兄有些尴尬。
随即是失落,他苦笑着低下了脑袋,仍是抱着最后一丝期望,道:“父亲呢,我想见父亲。”
父亲大约是不会来了。
我摇了摇头打破了他的念想:“我不是父亲派来的,是皇祖母让我来的,她让我打探打探你的情况,她很关心你。”
我这么安慰着他,隔着栅栏抚着他伤痕累累的身体,同情一叹:“郅都对你用刑了?”
荣兄仍然沉默。
不过他终于愿意抬起头来看我了。
他面色惨白,形容憔悴,面容削瘦得让人几乎忘记了他先前的模样,那支离破碎的胳膊抬着沉重的锁链,手上带着黑黝黝的血痂。
他的手要抚摸我的脸蛋,犹豫再三,又懦懦地收了回去。
荣兄勉强笑起来,一如我知事以来平和的面目,哄孩子似的摇头:“这些不是你一个小孩子该知道的。端端,你回去吧,你还小得很哪,还是不要牵扯进来得好。”
他干裂的嘴唇有些颤抖,话毕断然推开了我:“你回去,若祖母和皇帝问你,你就说我很好,明白吗?”
难道非得如此地步吗?
一阵死寂的风吹进来,我流下了冰凉的眼泪。
皇帝是不会放他的,除非……
我咽了咽口水,没来由心头一阵恐慌。
我环顾四周,自袖中取出一把早前备好的剪刀,对着木栅栏磨比划两下,又掏出铁针,匕首等物塞给了他:“我晓得你非死不可,是以您还是赶紧逃吧,逃到天涯海角,皇帝抓不到你的地方,做个平民百姓,一辈子不要露头,也好歹比年纪轻轻被人打死了强!”
荣兄出乎意料地抬起头看我。
他怔愣地拿着我不知从哪里来的杂七杂八的工具,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八弟,你?”
话未毕忽然有人自门外不耐烦地大喊道:“时候到了,时候到了!”
我与他使了眼色,拍拍屁股站起身,同是大嗓门地喊了回去:
“知道了知道了!”
我出牢狱的时候碰上郅都回来,想起荣荣兄的状况,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若不是他,我兄哪能这样?
郅都却笑眯眯拦住了我:“八皇子来这里干什么?莫非是得了皇帝的旨?”
得皇帝的旨,天,他也真是敢说。
我拨开他的胳膊,指了指身后乌烟瘴气的大牢,阴阳怪气地反驳道:“得了谁的旨?也不知谁得了谁的旨?要真是让人知道你这番酷刑得的是谁的旨,丢的又是谁的脸?你不过是只小猫小狗,最好还是收敛些的好。”
“你!”
郅都脸色微变,一阵踯躅的沉默里看了眼未央宫的方向。
他脸上的犹豫一瞬而过,似乎明白过来些什么,又勉强恢复平素谨慎的面目,为我让开了道:“胶西王所言甚是,不过还请您保守秘密。”
那瘦削的阴影笼罩着我,仍有些不服气意思,压低了声音道:“您知道,这并非臣的意思。”
此人便是我对皇帝臣属最初的印象。
拜访过兄长和母亲,我拉着杜信去梁国溜达,买了些吃食玩意儿,隔壁的堂弟山阳王又念叨着想我,让我去看看他。
堂弟已是病得很重了,不晓得患的是什么病,脸色青黑青黑,很不好看。
总算是我来了,堂弟无神且空洞的眼睛里冒出光采,拉着我道:“我下辈子做你的小鸡,你不许骑我马马,也不许揪我头发,我会很乖很乖……”
这么说着堂弟忽然咽了气,眼睛瞪得很大很大,不愿闭合。
死不瞑目不是什么好寓意,我怕他追我的魂,遂应下来:“好啊。”
堂弟的双目遂放心合上,屋内外遂哭了起来。
我几位堂兄弟皆是这么年纪轻轻就死了,昔日打闹的好友如此烟消云散,使得我有些不安,我怕我也会早死,问了杜信好几夜,得了他十来遍长命百岁的哄骗,又卜了好几遍地卦,总算安心下来。
大约是此行的确对我影响太大,忧虑在心,又或许是出来奔波太久太累了,我回国的途中忽然发起了热,等到王都的时候,已是烧得有些糊涂了。
“咱们王都又添了个国相。”
我蔫蔫地翻过身,听着王全与我的报禀:“这国相很是遵从皇帝的律令,他趁您不在这几月,又开始征收赋税了,还要在王国设儒学,还与臣义正辞严道您浪荡散漫,要奏请皇帝找师傅给您念经……唉,恐怕您又要受罪了。”
我正是寒噤,听到某两个字猛然打了个哆嗦:
“儒学?”
我祖母好似说过,儒学乃是害民的毒学,儒生皆是“大愚若智”的犬马之徒,她平生最是厌恶儒学儒士,并不让我读儒书。
只是我已过了被人压着读书的年纪,这多事的国相我自然不惧,挑挑眉冷笑道:“让他且先蹦跶几日,等寡人病好了再与他较量。”
天府管理员-d972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雷安:一心只想占有你
- 家族遗传精神病史校草雷狮X温润如玉偶尔丢骑士道的风纪委员安迷修紫罗兰色被侵染猩红“雷狮……你的眼睛?”“怕了么?”
- 5.0万字3个月前
- 直播算命:下山后我成了大佬
- 三清观出来后,为了谋生,我开始了直播算命之旅,不过过程似乎让我有点出乎意料起来…
- 17.9万字2个月前
- 爱——癌
- 1.1万字2个月前
- 期许如约
- 古风类,穿越,文笔不是很好,多多谅解
- 0.3万字2个月前
- 未完的画框
- 梦境中的游乐园,给你无数次重来的机会,兑换奖品,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去迷失森林,你会选择留下,还是逃离。
- 0.3万字1个月前
- 西游:西行悍匪集团
- 如来佛祖:“唐三藏,你们怎么现在才到灵山?”唐三葬:“我有早到的习惯吗?”如来佛祖:“今天摆台子呢,是为了孙悟空的事。”唐三葬:“刑者它打着......
- 2.0万字5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