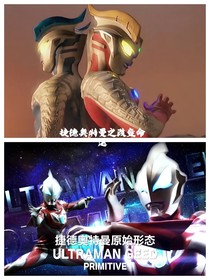第十三章:又见故人
从岩下村的门口进入后,眼前又是新的一片场地。刚下过大雨,道路泥泞得很,不好走路,下驴后的黄张二人还需卷起裤腿行动。
正对面乃是一个广场,其间的村社小台已经结了许多蛛网灰尘,表演器具横七竖八地倒在台面上。旁边那个破败的小院里,散落着各式各样的杂物,木桶与旧箱仿佛被时间遗忘般横陈在地上,诉说着往日的种种不甘。
一道简陋的门板栅栏歪歪斜斜地竖立着,仿佛下一秒就会不堪重负地倒下。斑驳陆离的砖墙默默承受着岁月的侵蚀,与先前所见的不远处那座直插云端的塔楼形成鲜明对比——一面是衰败的遗迹,一面则是光鲜的新世。真可谓“这头剩山残水,那边容光焕发”。
大抵还在村的边缘,所以一时不见来来往往的过路人,黄张二人便往那个小院的内院走去。
约莫又走了五十步后,黄张二人见内院的门半开着,料想里头还有人居住,便预备着走上前去问问。
一个手持团扇、约莫四十岁的圆脸女人此时在小院里转悠。却见她一弯柳叶眉,戴着银雕耳饰,身着粉色袄群,头上梳着散开留海与一条辫子,虽然有了些年纪,但那副面容依旧姣好。
 (图为87版家春秋梅表姐,差不多长这个样子,再稍微老成些)
(图为87版家春秋梅表姐,差不多长这个样子,再稍微老成些)
听到外边的动静,那女人先是躲在半掩的门后,眺了眺外边的光景,在转悠了几圈后,还是决定到门口来。
“可是寻人?”女人先开口道。
“哦,只是借过,意外到这岩下村来。”
“听您口音,似乎不是本地人?”
“是。怎么,有何异处?”黄嘉琪旅行许久,还未有人问过自己的口音,倒是奇怪。
“巧了,我也不是本地的,那请先进来吧。”女人说。
待二人走到院子里头,女子似乎发现了什么,忽而带些惊讶的语气认准道:
“是您…啊,老师,自从那年起,许久不见了,没想今日到在这里撞到。”
“你…”黄嘉琪些许吃惊,没反应过来。“我确实不太记得了。”
“我是梓漆啊…”女人笑道。
刹那间,黄嘉琪心底隐藏着的某份苦楚被翻了出来。那会正是崇祯末与弘光初的两年,当时他正值青年,那女人却还只有十二三岁,时过境迁,不想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
那会,小狼君正沉痛在小狼公主和名下门生的背叛中,叫国家的战乱与个人的哀思交织在一起,难以自拔。失意中,他关停了集会,姑且当了个私家的教书先生,也便是这个时候认识的黛梓漆。
由于这小女孩的名字正巧谐音“待子期”,颇有期盼故人的意思,所以黄嘉琪就把对小狼公主残存的那一点念想,顺理成章放在了这几个字身上。继而朦朦胧胧地,他对着自己的这个女学生也萌生点怪异的好感,着实有些痴痴恋恋的意思。
说真的,每当看见这小女孩,心里莫名就会舒畅好多,把过往的坏事给短暂地抛在脑后。尤其那次自己在角落里抹眼泪,还叫年幼的梓漆意外看见,被她偷摸着跑过来询问递手帕——而立之年的汉子被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安慰,真是羞死个人。
所以出现这份好感并不怪他,此间温情怎不叫人感慨。可更多时候二人还是保持着师生情谊,没有逾矩——好在时候未久,江南丧乱,小狼君的教书生活也终究告停,隐居山林去了。
现如今,人已年近花甲,风流往事不便再提,只是当黄嘉琪重新省视这段案件时,发觉眼下却还有些许问题需要处理。
“啊啊,这,确实巧。”黄嘉琪应道。
“现在如何做起了道士?” 黛梓漆打量了一下师徒二人,问道。
“不愿剃发易服、躲避灾祸呗,你等女流自然体会不到我们如此爱国热情。”
“那可不一定呢…历史上的烈女可少么?不过你们这些男人不愿意记录下来罢了。”黛梓漆抚着团扇,缓缓说道:“不提从前的话,近来的事也不少。就说丁未那年吧,云南可不就出了个土著的女英雄?带了万把人就敢往平西王脑门上糊,却连个名都不知,只被呼作陇氏。”
“罢罢,就当我错了,为师不与你争辩——要想你当年的嘴皮子也厉害得很。”黄嘉琪摆摆手,苦笑道。
“那这位是?”黛梓漆转过头,看着一旁瘦削却俊朗的年轻人。
“哦,这位是我近几年收的徒弟,大家都叫他小张。诶,我的门生中就属他最机灵,讨人欢喜,所以为师此行就带他下山来转悠转悠了。”黄嘉琪说着拍了拍小张的肩膀。
“呀,你是黄老师的学生,我却也是呢…”黛梓漆微微含笑,对小张说道。
小张也是尴尬地笑笑以示回应。
“那我,是不是该叫你师姐了…”小张思索了一会,问道。
“挺好的,显我年轻。”黛梓漆不乏欢喜地说道。
“他可崇敬那个宁波的张公了,出门在外时常和我念叨孤忠精神、学他的话术。只惜咱实力孱弱,没兵没甲,比不得人家青史留名。”黄嘉琪说。
“既然都是文化人,你背一段他的诗出来如何?”黛梓漆问道。
于是小张立马苍水公附身似的,义正言辞、声情并茂地背了一段《寄宿石庵与居人道定西侯往事》。背诵间还格外注意模仿自己偶像的言行举止,忽而激昂地高吭,忽而黯淡地沉吟。
“汉腊谁留十五年,琴亡岛屿尚苍然↗。
野人偏爱甘棠树,义士犹吟华屋篇。
海有浮鸥/怜后死,村无眠犊/忆前贤。
请看缑岭今宵月~可得将军/勒、马还!”
这首诗乃是十几年前张煌言在舟山割据之时,哀悼伤病离世的友人张名振所做。二张的军旅往事于此闪烁,与他们同姓的小张便也颇觉有心,便把这篇格律记得牢牢的。
一首念罢,他意犹未尽地回味着那些词句,仿佛他真打过仗,也失去过一个很好的战友似的。
“好诗好诗,只可惜现如今那东西是本禁书。”黛梓漆叹息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我等小民究竟无能,泱泱刍狗,命数悠悠。”
不知道为何,小张感觉这场面是在学堂里被长辈抽查了一番,心里不太是滋味。但好在梓漆相貌亲切、态度和蔼,便舒缓了几分陌生情绪。
“老师现在在做什么呢?”黛梓漆问道。
“唉,在山上呆得久了,下来活动活动筋骨,看看现在这山河大地是怎么个回事。”黄嘉琪打个哈哈。
“哦…”
“诶,师姐,您是怎么见到我师父的呀?”小张接过话来。
“我的父母挺开明的,时至国家动荡,百姓少有安宁,便愿我多学点文章意理,也好明个是非忠奸。所以请了您老先生来,不想…”
“你没嫁人么?”黄嘉琪问。
“二十年前也曾有个玉树临风的夫君,只惜后来染了风寒,留我一人守着这套院子。”
如此,三人在岩下村交谈一番,相互熟络。
不知为何,小张总感觉来者不是师姐,而是隔了辈分的长辈,毕竟人家还是明末的遗民,而自己完完全全是康熙年间的人了——凭着几个文学大家的笔墨寻找,以稀碎的传闻去勾勒前朝面目。
其实这种感觉并没有错,确实就是隔了很久。
毕竟,那个“前朝”实质已经烂透了,从上到下一致地溃败,并没什么好怀念的。所谓抗清,在如今却不过是一句标榜自己有高尚道德的话——要想啊,从明末陕北起义开始,到如今吴耿的反叛,历经五十年战乱,大多数百姓早已人心思定——倘若这时候再出来对抗“天命”,不是哗众取宠是什么?
连庄子上都说:“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现在打着为了百姓的旗号出来反抗清廷统治,不恰似砍掉手上那长多的第六根、隔开脚上连着的拇指么?看似是施行了仁义,实则追究起来毫无意义,违背了自然规律。
孤臣孽子,负隅顽抗,冥顽不化,可笑可悲。
……
孤臣孽子—独狼与三藩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捷德奥特曼之改变命运
- 柯南为了救少年侦探团不幸重伤但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但是好在有一位系统救了柯南的命如今他在原来的世界已经死亡了也回不去了既然这样系统告诉他让他去......
- 6.7万字4个月前
- 4家:追光少年
- 2.6万字4个月前
- 博物馆与夜
- 1.1万字2个月前
- 黑白之境
- 坚决与黑恶势力做斗争,不向不法分子低头扫黑除恶惩恶扬善有钱的命是命农民的命不是命吗?!”【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0.8万字2个月前
- 铁勺少女与六个帝国笨贼
- ——六个疯子,六个悲剧,一场荒诞的逃税革命——在女皇统治的帝国里,连呼吸都要缴税。德拉科·光颅,一个沉迷占星术的秃头逃兵,用铁锅和骰子预言未......
- 1.3万字4周前
- 换位中
- 我是林小雨我是林小鱼
- 9.6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