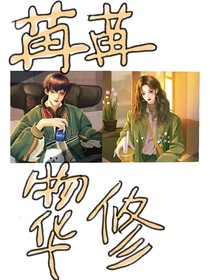第一章 庙岭(一)
我和程海仁是同村。小时候跟伙伴们在村头玩耍,惹爹娘生了气,扔过一把生锈的镰刀,骂一声,到坡里割草去!于是我们脏乎乎的几个,战俘一样,耷拉着脑袋出现在通往山里的崎岖小径上。偶尔,会遇上一个脸色黝黑,戴一顶蓝布单帽,肩上背一个家织布包袱打成的包裹的人埋头前行。同伴中的一个低语一声,程海仁来了!
来人抬起黑铁一样的方脸,眼珠朝我们滚几下,继续埋头赶路。等那人渐渐走远,我们一阵骚动,几只小脚散乱地撮在道路中央。最先认出程海仁的伙伴扯大嗓门喊道:程海仁——他——爹呀!我们齐合:哎嗨——哎嗨——哟!声音饱满锐利,长蛇一样在山谷和白云之间悠来荡去。
如此反复,那人终于沉不住气了,驻足回首,朝我们愤怒地挥了挥拳头。我们齐刷刷地绷紧神经做出准备逃跑的姿势。那人并没有追赶,整一整肩上下滑的包裹,讪讪着走了。
此刻,他若是处在高处,一定收脚将一块圆滚滚的石头踢下。石头欢蹦乱跳地跑下,钻进田里,野兔一样撞得庄稼棵抖出一道粗线。我们一起大呼,快看啊,富农糕子搞破坏啦,抓住他,绑起来!那人一慌,低头转身,样子极狼狈地跑了。
我们村叫“马蹄庄”,名字起得小气,村却是洼峪镇最大的村子。认得程海仁的伙伴叫歪松。歪松的一个亲戚住在村东头,他常跟着爹娘到村东去玩。一次,歪松对我说,程海仁他爹是个大坏蛋哪。我问为啥,歪松说他也不晓得,只知道程海仁他爹垒过村里的大戏台。
我立刻想起那天和伙伴们到大队院子去玩时见到的情景。一群老头抬着满筐的土石在大队院前台阶下不声不响地垒戏台。里面腰弯得最厉害的叫罗天富。旧社会,罗天富像压迫过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的地主一样压迫过村里人,他的腰就是解放后经常挨批斗低头认罪弄弯的。当即我就想跟罗天富这样的人一起垒戏台,肯定不是好东西。程海仁他爹是大坏蛋的事伙伴们很快都知道了,于是就有了那声程海仁他爹呀哎嗨哎嗨哟的喊。
那时我哥正读小学四年级。一次,哥放学回来得很晚,脸上汗津津的。我问哥干啥去了。哥说去搜电台了。去哪里搜电台?村东程海仁家。我来了兴致,程海仁家真的有电台?哥说程海仁他爹弄的,昨晚,程小江从他家门前走,听见他家里嘀嘀嗒嗒响,跟电影里敌人发电台的声音一样。我问,搜出来了?哥丧气地说,没有,那老家伙死活不承认,说那声音是他家的黑猪拱栏门时栏门上的铁环发出的。我替哥着急道,这老家伙真不老实。哥笑了,也没便宜他,叫我们拳打脚踢了一顿。我对哥顿生羡慕,哀求说,哥,下回你们再去搜电台时一定带上我。哥的脸一沉,可不行,等你长大以后吧。
于是我盼着长大,盼着上学,盼着像哥那样兴冲冲地跑回家,向娘讨要几毛钱,从学校领回一条鲜艳的红领巾,盼着像哥一样排在游行的队伍里举着彩纸做的小旗高喊口号。
终于,我也能上学了。而学校里一切都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没有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没有了盖住墙皮的大小字报,当然更没有去程海仁家搜电台。同爹娘相比,老师要严厉得多,整天逼着你写写算算,最叫人受不了的是那些多如牛毛的纪律,仿佛偏冲着你做不到才制定的,小心着小心着还是免不了犯上一条,犯一条就得经受点小小的但在那时看来像是塌天的灾难。渐渐地,对哥做的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淡忘了,倒是隐约听人说起过程海仁。先是大队给他家摘帽了。那时不知道摘帽的含义,以为大队不让程海仁家的人戴帽子了。又听说程海仁在他教书的那个小山村做了啥坏事,叫人打了,说他是“程害人”。
倒霉蛋柳建军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忆许安
- 1.8万字5个月前
- 小雨点落
- 许回在她最胆小的那年遇到了想让她勇敢的人,但最后,她还是没能勇敢一次。胆小鬼的代价就是,永失所爱。“我在安静的青春里,热烈的爱着一个少年。”......
- 1.2万字5个月前
- 桂瑞:小猫和我回家
- 校园文,主桂瑞,复写奇文和熙铭
- 2.6万字2个月前
- 不施粉黛的女孩
- 从小县城到大城市……她说公交车不来就走一走路
- 0.6万字2个月前
- 苒苒物华休的苒苒
- 苒苒和叶归州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 8.3万字2周前
- 他的绿茶味盛夏
- 当迟傲的冰茉莉泼湿林竹昊的物理作业本,两个少年的夏天在墨渍里开场。篮球队王牌迟傲,人如其名冷冽如冰,却被转学生衬衫领口的薄荷香乱了投篮准头。......
- 6.0万字4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