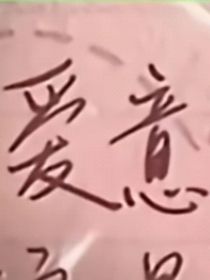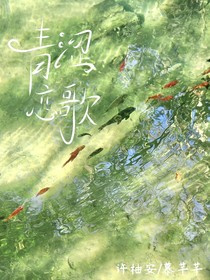第一章 庙岭(五)
在对程海仁的称呼上,我着实为难了几天。按同事关系,我应称他程老师。从同乡的角度,程海仁与我的外祖父同辈,我应称他姥爷。与程海仁说话,“老师”和“姥爷”这两个称呼常常同时挤到舌尖,叫我在极短的时间内犹豫不决。我很快发现称呼程海仁“姥爷”比称呼“老师”更叫他高兴,便不由自主地习惯了“姥爷”这个称呼。
自从我当着袁若北的面唤了程海仁“姥爷”,袁若北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曾有意无意地问过我一句,柳老师,老程和你真是亲戚啊?我笑笑,不是,他和我外祖父同辈,其实家隔着挺远,我都不知道他家住在哪里。袁若北用一种怪怪的眼光看着我,看样子本想再跟我说几句,但张了张嘴巴竟没有说出来。
从那时起,我隐隐感到他和我之间猛地拉开了一段距离。为消灭这段距离,我主动跟袁若北接近,背着程海仁,主动流露一点对程海仁的不满,以期同袁若北搞好关系。我接近袁若北的结果是袁若北把我当成程海仁的密探而严加防范。程海仁把办公室的肥皂拿回宿舍用,袁若北察觉后,皱起眉,我当即对程海仁的行为表示了不满。袁若北却突然舒眉展眼开心地一笑,嗨,一块肥皂,又值不了几个钱,叫程老师用吧。随即打发学生又买了一块。而不当着我的面,他却对王松财大骂了程海仁一场,骂他是财迷,连块肥皂都舍不得买。王松财眉飞色舞地告诉我时,我彻底丧失了同袁若北搞好关系的信心。
程海仁与袁若北之间的裂痕日益明显,我跟哪一方多少表示点亲近,都会伤害到另一方,或者说给双方造成力量悬殊。上次集体喝酒后剩下一点花生油,袁若北悄悄锁了起来。程海仁对这事又特别上心,简直称得上明察秋毫。放学后,程海仁咬呀切齿地对我说,建军,袁若北把剩下的那点花生油藏起来了,这个穷鬼,真是小肚鸡肠,咱离乡背井地到这里来,就是吃了那点花生油,还不是应该的,操他娘,这是有意跟咱过不去啊!
第二天,办公室的人到齐后,程海仁喊进一个学生,说,去伙房把我那半斤油拿来。学生应声拿来。程海仁接过油瓶,启开盖子闻了闻,皱眉道,咋不是正味,拿出去扔了吧,别把人药死了。学生走后,程海仁开玩笑似的问我,建军,半斤油多少钱?我说一块五吧。程海仁撇撇嘴,噢,才一块五啊,我寻思准值金值银的哪。我斜眼一看,袁若北脸上开始泛红。
程海仁继续说,建军,别看一块五毛钱,有些小里小气的老娘们,还真拿着当回事哪。如果我顺着程海仁的话说下去,很明显是站在程海仁一边攻击袁若北了。如果对程海仁的话不作应答,程海仁肯定认为我倾向了袁若北。我急中生智,将墨水瓶碰倒,鲜红的液体血淋淋地溅到衣服上,于是我堂而皇之地出去洗衣服,从两个人的争斗中退出来。
在这一点上,王松财比我高明得多。一会给程海仁捋捋胡子,趁着程海仁被捋得舒服,再给袁若北搔搔痒痒,打发得两人没气没火的,把他看成局外人。王松财那一套我学不来,只好笨拙地干些不合算的蠢事。空闲时,我尽量只跟王松财扯几句,因为这样,程海仁和袁若北都没有意见。
和王松财相处也不那么顺心。王松财喜欢打乒乓球,问我会不会打,我说不大会,他便执意要和我去玩玩。正是课外活动,球台边围满了学生。王松财的球龄一定很长,虽然技术不是多么好,却磨练出一个古怪的发球方法。王松财接连发了五个怪球,我竭尽全力,只抵挡了三个。旁边一个学生甜着嘴夸赞王松财,说王老师发的球真是神了!
王松财得意洋洋地提出和我开一局。我说玩玩算了。他不肯,非要和我比个高低,且做出一个满不在乎的架势,漫不经心地接我的球,像逗小孩一样。王松财的无礼触怒了我的自尊心,我暗骂一声,准备给他点颜色看看。我横握球拍,猛打猛攻,以二十一比十五战胜了他。一个小学生伸出大拇指冲我晃了晃。王松财抬脚恶狠狠地踢了他一脚,骂道,滚一边去,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小学生吓得没敢吭声,抱头鼠窜。
我跟王松财回办公室时,他指指划划地对我说,柳老师,你打球有个毛病,姿势不大好看。我谦虚地点点头,可不,瞎闹着玩就是。
我上音乐课,因一支歌学生没唱好,拖延了时间,其他两个班的学生围在门前听,有的跟着小声哼唱起来。第二节不到上课时间,王松财凶神恶煞地将他班的学生唤进教室,也高门大嗓地上起音乐课来。学的是“洪湖水浪打浪”那支歌。回到办公室,里面只程海仁一个人。见我回来,程海仁抿着嘴莫名其妙地笑。我问,姥爷,你笑啥?程海仁说,我笑王松财,这家伙真是心比天高,可惜没多大本事。我问咋了?程海仁说,咋了,他看着你上音乐课,又吸引了那么多学生,也上起音乐课来了,这家伙,啥也想戴个高帽。我说,他这节原来不是音乐课啊。程海仁哼了一声,啥音乐课,他是想跟你争个高低,真有意思,都“浪打浪”了好几学期了,还浪打个啥劲,真是老调重弹。
之后,我每每上音乐课回来,王松财都拿腔拿调地哼几句“浪打浪”啥的,哼得我心烦意乱。为了照顾王松财的情绪,上音乐课时我有意压低声音,不叫自己那自我感觉良好的浑厚歌声张扬得太厉害。后来干脆不亲自上音乐课了,找几个家里有录音机的学生轮流领着班里的同学胡唱。
王松财不住校,只有中午饭在学校吃,自带点干粮、咸菜。我和程海仁分开起灶,各做各的。程海仁做好饭,端到一边自顾自地大吃,让也不让王松财一声。王松财和我凑成堆。我把我做的菜推向他一边,要他一起吃。他摇摇头,又推过来,说他就喜欢吃咸菜,他老婆在家炒了菜,他没拿。接着开始评论我的菜。若我炒的是蔬菜,他便说现在的蔬菜没法吃,施化肥施得里面含了对人体有害的化学成分,容易致癌。上粪便的往往洗不干净,吃进肚里长虫子。还有菜叶上有虫卵啥的。若我的菜里有肉,他就说有一种五号病,人吃了这种病猪肉,要烂脚丫子。说得我胃口大减。
袁若北跟王松财闹了点小别扭。外地一户来庙岭落户的人家,家里有个正读四年级的孩子要到庙岭联小插班,暗地里请了袁若北的酒。袁若北满口应承下来。学生来校时,王松财将其拒之门外。袁若北过来解释,两个人拌起嘴来。袁若北说这个学校谁说了算。王松财反驳,四年级这个班谁说了算。我和程海仁躲在一边嗤嗤地笑。
结果还是袁若北让了步,答应再叫学生家长请一桌,全体老师都去。放学后,我和程海仁为袁若北和王松财的事好笑不已。程海仁来了兴奋,建军,今晚咱爷俩喝几盅。我说行啊。
几杯酒下肚,程海仁的情绪渐渐提升到亢奋状态。大概是我问了一句,姥爷,你在北水中学待过啊。程海仁满面红光,神采飞扬,讲起了他的一段辉煌历史。
程海仁第二次调来庙岭后,他早期的一个学生从部队转业来洼峪镇做副镇长。师徒两人在公共汽车上相遇,叙起旧情。学生问,老师,您现在从哪里教书啊。在庙岭联小。学生诧异道,都这么大年纪了,咋不要求要求调得离家近点。程海仁来了感慨,攸光,你又不是不熟悉你老师的脾气,咱一不会拍马溜须,二不会请客送礼,嘴边又没个沟沟槽槽,有啥说啥,这些年还不知得罪过多少头头脑脑,谁还知冷知热地待咱,唉,你老师也习惯了,没有那些争强好胜的棱棱了,混碗饭吃,图个清闲吧。学生不平地说,到了镇上我一定替您说几句话,您有能有耐的得弄个位置施展施展,说真的,我那点知识都是当初跟您学的哪。
下学期,程海仁被调回我们马蹄庄中学做校长。那时我们村因村干部闹矛盾,已经以一条季节河为界解体成北马蹄庄和南马蹄庄两个村了。我和程海仁都是北马蹄庄人。马蹄庄中学是两个村联办的一所中学,校址设在北马蹄庄。这里的人们把“联办中学”称为“难办中学”。有荣誉,两个村都抢破头地争,一到收交办学经费,两个村又互相推诿,把个学校孤零零地甩到一边。马蹄庄中学成了一个烂摊子,建校多年了,只有一长排房子横卧在北马蹄庄村东头。每每假期,学校都要惨遭破坏,玻璃没有了,课桌凳缺腿少胳膊,黑板被五颜六色涂抹得看不出眉目。多任校长为建院墙的事跑直了腿,磨破了嘴,都没弄出个结果。没办法,买点东西趁天黑到镇教委主任家诉苦一场,打个请调报告,避瘟疫一样离开了。
程海仁回马蹄庄中学前就有街坊邻居对他说,来吧,有你的好罪受。程海仁回之一笑,是啊,咱生来就是吃苦受罪的,前半辈子都喊咱富农糕子,后半辈子你们再捉摸个名堂吧。
来马蹄庄中学的第二天,程海仁召集各班班主任开了一个简单的碰头会,布置好几项任务后,走出校长室,在一长排教室前很气派地走了几个来回,然后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来到村苹果园里。承包苹果园的人是老姜,程海仁同他有些熟。老姜将程海仁叫进茅草屋里,很尊敬地唤了声程校长。程海仁一笑,啥校长不校长的,叫个老程散了。两个人闲聊了几句,程海仁说,老姜,你们几个人承包的苹果园?四个人啊。程海仁又问,你们一年往村里交多少钱?两千。程海仁再问,你们四个人一年到头都挺忙吧?老姜说,忙一阵闲一阵。
程海仁低头沉思了一会,仰起头郑重其事地说,老姜,我包给你一个活路你干不干?啥活路?给学校拉道院墙。老姜的头立刻摇得像拨浪鼓,可不行,可不行,又没给钱的!程海仁认起真来,咋没给钱的,不光给,还保证叫你不吃亏。老姜半信半疑,谁给?程海仁说,我给,只要你把院墙拉起来,我就把钱给你。老姜问,多少钱?两千元咋样。老姜笑滋滋地说,价钱倒可以,就是怕你说话不算话,到时弄不到钱。程海仁哈哈一笑,恳切地说,老姜,咋能骗你,咱俩当庄当院的,我真要骗了你还跑得出马蹄庄,要不咱先立个字据,到时你拿着条子来找我就是。
两个人一本正经地立了字据。
程海仁来马蹄庄中学的第四天上午,就有拖拉机突突突地运来砖石,扑扑通通卸在教室前面。老师们不解地问程海仁,程校长,他们要做啥?做啥,这不是给咱拉院墙啊。老师们糊涂了。哪里来的钱?村里的。老师们吃惊地睁大眼睛,你要到钱了?程海仁平静地一笑,要到了,活人还能叫尿憋死。
程海仁来马蹄庄中学的第十天,学校的院墙建起来了。虽然还没有安装大门,但有了院墙的学校同以前相比已经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学生们像过节一样在院子里跑跑跳跳,爱不释眼地转着身向四处看。老师们走出办公室,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谈论,不时将敬佩的目光涌向程海仁的办公室门口。
承包苹果园的老姜躬着身子远远地朝学校这边走来。程海仁来门口倒脏水时看见了,压低声音将几位老师唤进他的办公室,嘱咐道:老姜来讨拉院墙的钱了,你们在一旁坐着,必要时加几句话。几位老师愣愣地坐在挨着墙的连椅上。老姜进了校长室,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程校长,我来跟你要钱了。程海仁叫人给老姜倒一杯热水,笑嘻嘻地说,行啊,我早给你准备好了。老姜顾不上喝水,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程海仁,程校长,你真讲信用,结了账我得赶快回去,果园里忙着哪。
程海仁谦让道,喝碗水吧。老姜不坐,执意拿了钱就走。程海仁捂着嘴咳嗽了几声,和蔼地说,老姜,你拉院墙的钱,我跟村里商量好了,准备免收你今年承包果园的那两千元承包费。老姜听了,脸腾地红了好几倍,额上涌出一层细汗,结结巴巴地说,那哪成,村里根本不同意为学校拉院墙,你这不是坑我啊!程海仁站起身亲自倒了碗水,递到老姜面前,肯定地说,老姜,你别急,我咋能坑你,你问问这几个老师,我跟村里定时他们都在场。
几位老师恍然大悟,一起凑过来劝老姜,真的,村里答应了,我们都亲眼看见的。老姜一屁股坐在连椅上,沮丧着脸埋怨程海仁。程海仁一点也不恼,陪着笑脸开导说,钱还不是一样的,现在给了你到时你也得往村里交,再说拉这么道院墙能值两千元,你沾老了光了。旁边的老师七嘴八舌地好言相劝,老姜才闷闷不乐地走出学校。
老姜一走,程海仁洗把脸,穿上长袖衬衣,向老师们打听谁跟村主任关系最近。有老师说他跟村主任是姑表兄弟。程海仁说,正好,跟我到村里去一趟。到了村委,村支书听程海仁一说,雷霆大发,说简直不像话,不经村委同意擅做主张,这事你一定负责!程海仁慢腾腾地坐在沙发上,不温不火地说,负责就负责,这是给集体办事,我又没贪分文,难道还能叫我蹲大狱不成?村支书又要发作,程海仁抢先说,这事最好向上级汇报,说不定我还能得到上级表扬哪,咱学校是镇里的老大难,镇上领导恨不得咱这里盖座楼才好。村支书气呼呼地说,盖也得通过正当渠道啊,先打个报告上来,经村委研究后决定,哪有你这样做事的?程海仁苦笑说,支书,不这样做咋治?以前哪任校长不打三五回报告,解决了吗?村支书气得站起身来回踱步。
程海仁给同来的老师使了个眼色。那位老师点点头,过来劝村支书说,表哥,人家程校长是没办法啊,你看咱这学校都成啥样子了,老百姓说闲话,说你们村委会一点正事也没有,孩子念书可是以后的大事。村支书皱皱脸,气已消了大半,阴着脸说,可弄得这事……太离谱了。程海仁道歉说,支书,我做的这事是有些离谱,可我是一心想把咱这学校办好,没办法才这样做啊。
村支书软下来,程校长,这事村里不是不愿办,说实在的,村里也不缺少这两个钱,可……这学校不光是咱北马蹄庄的。程海仁站起身,殷勤地给村支书点了一颗烟,支书,你放心,这事我早想好了,院墙虽然拉起来了,不是还没有大门啊,叫南马蹄庄出,南马蹄庄在中学里上学的人少,出个大门基本就扯平了。村支书为难地说,南马蹄庄村委那些人,一滴血也不出的。程海仁笑道,支书,请放心,我有办法。啥办法?程海仁神秘地说,南马蹄庄的加工厂不是新做了一个大门啊,我去看过,还没安上,在加工厂的院里扔着,夜里咱去几个人弄来安到学校里就是。村支书摇摇头,南马蹄庄能愿意啊?程海仁咂咂嘴,这就看你的了,北马蹄庄建起院墙,南马蹄庄出个门还不行,要打架咱村的人比他们还多一大截哪。村支书一下子来了精神,咬咬牙说,行,我集合起全村的民兵来帮你们办这事,不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事情出乎意料地叫程海仁解决了。程海仁派人到锦屏县城做了面白底黑字的牌子,往校门一挂,一座像模像样的中学奇迹般地出现在我们北马蹄庄的村东头。公路上来往的人像碰到天上落下白面馒头一样驻足观望,啧啧称赞不已。
当时的镇教委主任听说后,掩饰不住兴奋骑车专门前来观看。一看看了个心花怒放。正好镇中心小学校长到了退休年龄,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拖延了挺长时间。从马蹄庄中学回来,镇教委主任乐得不得了,心血一涌就把程海仁调到了镇中心小学做校长。
倒霉蛋柳建军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喜杀手学院
- 喜羊羊在做任务中掉下悬崖,众杀手们都以为他死了。后来我在青青草原遇到喜羊羊,后续是怎样的呢?
- 1.7万字5个月前
- 竹马青梅谣
- 青梅竹马的两人一起成长
- 2.0万字3个月前
- 人生因遗憾而完美
-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个勇敢的人。作品内容都是依据个人经历呈现的,略略有改动欢迎大家留言!!!
- 4.5万字3个月前
- 原来爱也需要等待
- 双向奔赴。在各种事情下男主表明心意在一起啦!甜加虐
- 3.1万字1个月前
- 青涩恋歌
- 双女主be结局文,又甜又虐
- 1.2万字3周前
- 重生:带刺的蔷薇,明目张胆的偏爱
- 【当死亡成为重生的起点,她能否改写遗憾的青春?】18岁的林挽歌在暴雨中得知自己的身世真相,车祸前最后一眼,是暗恋七年的少年陆沉舟逆着光狂奔而......
- 2.1万字2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