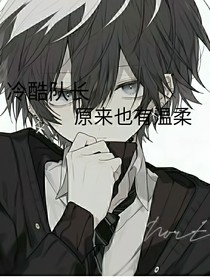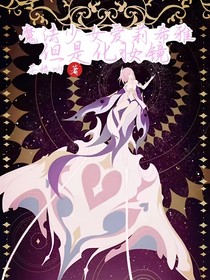提问
学堂内,学子们刚结束课间的嬉闹,见先生杨慕笙走进来,赶忙收起散漫,正襟危坐。
杨慕笙,这位年逾五旬、曾担太子少保之职的宿儒,虽已致仕返乡,但其学识与威望,让书院上下皆敬重非常。他目光平和地扫过众人,开门见山地说道:“诸位学子我们讲治国之道,今古之治,大势分合,正如圣人所云:‘治国之道,在安邦。’‘安邦’乃治国之根本,而其关键在于‘仁’。所谓‘仁’,是宽广胸襟,怀柔之德;是心怀苍生,慈爱天下;是善恶分明,忠奸可辨,公私能分。唯有秉持‘仁’,方可使百姓安康,社稷稳固。今日,便与诸君探讨‘治国之道’,望诸君用心领会,日后为国立业,以仁为基,行正义之事。”
学子们神情肃穆,杨慕笙的话语如洪钟般,声声撞击着他们的心房。
言罢,杨慕笙抬手向左一指:“青珩,且来回答,你如何看待善恶之分?”
顾惊鸿应声而起,略作思忖后说道:“先生,善恶之分,绝非简单片面之事,它涵盖观念、人性与行为等诸多层面。善恶观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整体环境及人性特点紧密相连。善恶之别,并非源自一时冲动,而是长期行为积累与心性沉淀的结果。日常为善,方能积累善念;若放纵私欲,则易滋生恶念。善恶相互影响却又相对独立,并非绝对统一。善,蕴含着善意与宽恕,如同海绵吸纳美好;但有时,看似善意的表象下,也可能潜藏着如棉花糖般难以察觉的危害。善恶之争,根源在于人心。善良本是美好品质,却常因人性弱点被利用,进而导致善恶的分化。在我看来,善恶相对而生,并无绝对高低。‘善’虽非最强,却坚韧无比;‘恶’貌似强大,实则脆弱不堪。然而,世间亦有极端之人,自认为行善,实则作恶,此类人应被称作恶徒。恶徒秉持邪恶思维与偏执信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一切,实乃可怖之极。”
顾惊鸿话音刚落,学子们纷纷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青珩所言,颇具见地,先坐下吧。”杨慕笙微笑颔首,转而看向叶临之,“临之,且考考你,如何看待重男轻女这一现象?”
此问一出,众人皆感意外,一时愣住。
叶临之眉头微蹙,思索片刻后答道:“先生,男孩女孩皆为父母血脉结晶,自出生起,便承载着生命的意义,不应厚此薄彼。若一定要论差别,我反倒觉得女孩更需关爱。溺爱男孩,易使其骄纵蛮横;忽视女孩,会致其性格孤僻冷漠。父母若能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女孩会懂事乖巧,男孩也能谦逊自强。男孩女孩的差异,并非天生注定,而是源于父母的偏爱程度。孩子皆是独立个体,都应被平等对待。女孩绝非父母的附属品或交易物,她们有独立思想,有权选择人生道路,父母不应横加干涉。男孩亦不应过度溺爱,否则将难以承担责任。父母若将孩子视为整体,给予同等的爱与尊重,孩子便能健康成长;反之,若区别对待,孩子间的关系便会疏远,各自走向极端。”
杨慕笙目光中透着嘉许:“嗯,继续说,你对龙阳之好又作何看法?”
叶临之微微一怔,稍作调整后回答:“先生,学生以为,龙阳之好,若出于真心相爱,实无过错。爱情本就无关性别,是心灵的交融与吸引。虽此种情感不被世俗普遍祝福,但我们应给予尊重。这并非病症,只是爱情的一种表达方式。相爱的双方,虽面临世人唾弃、厌恶与憎恨,但只要他们坚守初心,努力不让世俗左右自己,便值得敬佩。当他们冲破世俗枷锁,便会明白,那些偏见与阻碍,皆为虚妄。真正的爱情,应超越世俗眼光,错的不是他们的感情,而是世俗的狭隘与歧视。他们不过是渴望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这份纯粹的情感,不应被异样眼光审视。”
杨慕笙面露欣慰之色:“临之,能有此等见解,殊为不易。世间情爱,形式多样,皆应得到尊重。治国需以仁为本,为人处世,亦当以包容理解为怀。莫让世俗偏见蒙蔽双眼,要以公正宽厚之心,看待世间万象。”
此时,一位同窗举手发问:“先生,话虽如此,龙阳之好者常遭非议,困境重重,该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杨慕笙神色凝重,缓缓说道:“改变此状,需从每一个人做起。以自身言行,倡导包容理解,影响身边之人。人心的转变,非一朝一夕之功,需漫长岁月。但只要我们坚守正义,秉持正确理念,假以时日,世俗偏见终会渐次消散。”
在杨慕笙的引导下,课堂讨论愈发热烈,学子们对爱情、世俗与包容的认知,在思想碰撞中不断深化,而顾惊鸿和叶临之,经此一论,对真挚情感的坚守,也愈发坚定不移……
惊鸿遇瑾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冷酷队长原来也有温柔
- 这是一篇熠风的——洛小熠X凯风在没遇到你之前我的世界一片黑暗,遇到你之后我的世界瞬间多了一抹阳光……你是我灰暗中唯一的救赎!!!“那个你的手......
- 15.8万字4个月前
- 魔法少女爱莉希雅但是化妆镜
- 爱莉希雅和侵蚀律成为魔法少女穿越到PocketMirror帮助5位女孩消灭恶魔
- 0.8万字3个月前
- 凹凸:魂穿凹凸
- 『无签约』“圣洁纯朴的她被人拖入了泥潭,迎来的是世间的邪恶”“那她是否能拯救世界成为人们的救世主”一★★一频繁找他打架的嘉德罗斯“雷帝来和我......
- 1.6万字3个月前
- 间之楔别名爱之楔-d605
- 《间之楔》该作讲述了两个分别立于社会顶层和底层的男性之间,奇异的对抗之爱的故事。“彼此极端的身份,形成了未曾言说的爱。”预计还有六卷和一部同......
- 16.1万字1个月前
- 你的眼睛真美,像星星一样闪烁,仿佛藏着整个宇宙的光芒
- 《时光深处的温柔》我叫林悦,是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我的生活平淡而规律,每天在书架间穿梭,整理书籍,偶尔和来访的读者交流几句。直到那个阳光明......
- 1.5万字3周前
- 爵冰:冰晶川的消融
- 颜爵x阿冰
- 1.4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