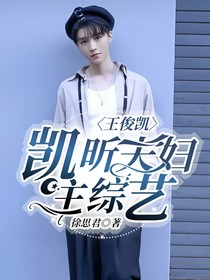第六十章:大褂里的雨与光
一、暴雨夜的抉择
后海的雨丝像扯不断的灰线,糊在湖广会馆的雕花窗棂上。李鹤东倚着后台的木柱,听着前厅稀稀拉拉的掌声,指腹摩挲着大褂口袋里的诊断书。纸角已经被攥出毛边,“慢性咽炎”四个字在昏暗的手机屏幕光下泛着冷白。
“东哥,该您上场了。”小徒弟探进半个脑袋,辫梢还滴着雨水。李鹤东抬头,看见镜子里自己额角的皱纹又深了些,两鬓新染的黑发遮不住泛青的发根。三天前在医院,医生说再这么演下去,声带小结怕是要转成息肉。
幕布掀起时,他听见前排有个老观众喊:“东哥,来段《地理图》!”那是他的成名作,贯口如连珠炮,曾让多少人拍红了巴掌。可此刻舌尖抵着上颚,却像含着团浸水的棉花。“诸位,今儿咱们换个轻松的……”话一出口,自己先愣了。底下立刻有人起哄:“怎么改文哏了?”
台上的桌布被穿堂风掀起一角,李鹤东弯腰去压,瞥见第一排坐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正举着手机录像。那瞬间他想起自己十四岁在胡同里卖烤白薯,零下十度的天,手冻得发紫,却为了多卖俩钱儿,追着放学的学生喊“热乎的”。如今这姑娘眼里的光,多像当年自己趴在天桥茶馆门缝里,看老先生们抖包袱时的模样。
二、胡同里的月光
散场时已过子时,雨停了,青石板路映着路灯昏黄。李鹤东解开大褂纽扣,任由夜风灌进领口。路过烟袋斜街时,听见身后有人喊:“东子!”回头见是发小顺子,蹲在老槐树底下抽旱烟,脚边摆着半瓶二锅头。
“听说你嗓子出毛病了?”顺子往树根上磕了磕烟袋锅,火星子溅在青砖缝里。李鹤东没接话,弯腰捡起块石子,朝胡同尽头的影壁扔去。“啪”的一声,惊飞了墙头上的野猫。小时候他们总在这儿比谁扔得准,赢的人能多吃块炸糕。
“还记得咱哥几个在胡同里说相声吗?”顺子突然笑了,“你扮老太太,我敲搪瓷盆当锣,柱子他爸拉板胡跑调儿,把街坊都逗得直不起腰。”李鹤东摸出根烟,却没点,在手里转着:“那时候觉得,能让大伙笑,比什么都强。”
顺子往地上泼了口酒:“现在不也一样?前儿我带我孙子去听你相声,那小子笑得跟个铃铛似的。”月光爬上李鹤东的眉骨,他忽然想起住院时同病房的老爷子,临走前攥着他的手说:“听你说相声,我这癌都轻了一半。”
三、晨光里的大褂
天快亮时,李鹤东回到南锣鼓巷的四合院。推开院门,看见妻子正在廊下晒大褂。月白的布料被晨露洇出小块阴影,像他当年在工地搬砖时,汗湿的背心。
“医生说让你歇半年。”妻子转身时,李鹤东注意到她鬓角也有了白发。他走过去,接过衣架上的大褂,手指抚过领口细密的针脚——这是妻子特意找苏州绣娘绣的竹纹,说是“未出土时已有节”。
“明儿去趟天桥吧。”他把大褂叠得方方正正,放进樟木箱,“我想带徒弟们看看,当年老艺人们怎么在露天地儿使活。”妻子没说话,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皮盒,里面是晒干的胖大海和金莲花。
朝阳爬上青砖灰瓦时,李鹤东站在镜前系大褂纽扣。忽然想起师父曾说:“相声这行,讲究个‘艺不压身’,可真正的功夫,都在台下。”他对着镜子扯了扯嘴角,发出一串低哑的笑声——这嗓子虽不如从前清亮,却多了份岁月磨出来的厚重。
四、角儿的背影
湖广会馆的日场座无虚席。李鹤东扶着小徒弟的肩膀走上台,看见第一排的小姑娘还在,手里举着幅字画,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东哥加油”。
“今儿咱们说段新的。”他拿起醒木,却没拍下去,“先给大伙讲讲,我当年在胡同里卖白薯的事儿……”底下传来轻轻的笑声,像春风拂过湖面。小徒弟站在一旁,紧张得攥紧了袖口,却听见李鹤东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记住,咱们说的不是相声,是日子。”
幕布落下时,阳光透过雕花窗,在李鹤东的大褂上织出一片金斑。他摸出诊断书,折成纸船,放进后台的金鱼缸。小徒弟凑过来:“师父,您真打算带我们去天桥?”
李鹤东望着窗外的胡同,槐树影在青石板上晃啊晃。远处传来鸽哨声,像极了二十年前那个追着卖糖葫芦的少年。他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晨光:“走,先去吃碗卤煮,然后咱就奔天桥——那儿的砖缝里,还埋着咱们的根儿呢。”
从胡同少年到相声角儿:李鹤东的蜕变之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r1se:助理难当
- 一个家境贫苦的18岁女孩和11位艺人会发生什么呢
- 1.9万字7个月前
- 一些乱七八糟的小文章
- 总之就是啥都有啦我会把在bcy发的转过来
- 1.3万字7个月前
- 王俊凯:凯昕夫妇主综艺
- [1.15正式签约]主要是写一些凯昕夫妇在一起后参加的综艺黄知昕:“早安,王先生”王俊凯:“早安,王太太”超甜无虐,快点来入坑吧!这里绝绝对......
- 23.6万字2个月前
- 萌学园之远古浩劫
- “远古浩劫即将重现,魔法世界与人类世界将陷入空前危机。”五星守护,净化,五行八卦阵,玄女,宇宙深渊,五族之钥,月之星能量
- 10.5万字2个月前
- 蜂蜜锈
- 0.7万字2个月前
- 请在给我一次机会
- 1.9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