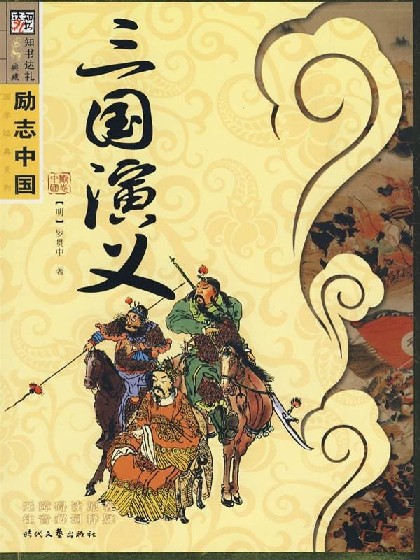第四十五章妄测天心
夏言也将身子向李春芳那边倾去,头几乎与李春芳的头凑到了一起,低声说:“你子实兄侍立朝班近三十年,位列台阁也有好几年了,如今才有此识见?当今皇上以幼冲之年即位大宝,以外藩身份入继大统,便为了故皇考、皇妣尊号一事与朝臣公开对抗,三朝元老、内阁首揆杨廷和顷刻失势;百余官员同日受杖;张熜张孚敬以南京刑部六品主事的身份奉调进京,两年位列台阁,再次年擢升首揆……这些事情,哪一件又简单了?”
李春芳摇摇头:“上尊号是尽人子之孝,树皇权之威;杨廷和致仕,则因神龛里的菩萨请是请不下来的,只有搬走;百余官员受杖、张熜张孚敬那个奸佞小人破格拔擢,则是君上凭一己之好恶干扰官制、臧否大臣。这往昔种种非常之事虽不简单,大致也能想得过去。历朝历代,雄猜多疑之主莫不如此。可那年‘宫变’之后,皇上行政理事之举措,便令人有些想不通了。你我遍读天下诗书,又身历两朝,见过民间之疾苦,享过朝堂之荣耀,尚且不敢做如斯之想;当今圣上乃是太祖血脉,一落地便钟鸣鼎食,锦绣堆里长大,他竟也能如此勘破时世、洞察先机,岂不奇矣怪哉!”
“你这话说的非人臣之礼!”夏言反驳道:“皇上膺天命为九州之主,掌乾坤权柄,心比日月还明,岂是你我这等红尘俗世凡夫俗子所能比之的!”
“公谨兄,我那话说的自非人臣之礼,你这话说的却非是朋友之道啊!”李春芳笑道:“历朝历代九五之尊,除却那些个亡国之君,哪个不是膺天命为九州之主,掌乾坤权柄?怎不见有这等识见?治政之才倒也罢了,新政诸多举措大多有形迹可寻,纵然没有,也可谓之曰‘圣心深远,睿智天纵’。难得的是天文地理、格物算学诸般学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就拿在去年那场大战之中大建奇功,今次又在徐州城下扬威破敌的御制神龙炮来说,我私下里问过何儒何老先生,皇上赐下的图谱,他们兵工总署军器局诸多能工巧匠竟无一人能看得懂,皇上亲传亲授,从原理到制造工艺技巧,无不详尽确实,火药配方也未见有任何典籍所载,皇上又是从哪里获知的?”
“皇上称其‘得之天授’,莫非你竟怀疑此说?”
“怎敢怀疑啊?非但深信不疑,先是兵工总署军器局,继而京里各大衙门上至部院长官,下到司员胥吏,哪个不说当今万岁爷是神仙下凡?”
夏言一撇嘴:“若说偶然天人感应,有诸多神物得授于天也就罢了,怎会冒出个‘神仙下凡’之说?再者,小官胥吏这么说,你这个内阁辅弼之臣也这么说?农夫工匠这么说,你这个受教于孔圣先贤,又是正德十二年状元郎的饱学之士也这么说?”
李春芳说:“非此说不足以解释诸多疑惑啊!”
夏言冷笑道:“神仙?神仙也有仙籍仙班,当今皇上于嘉靖二十一年前崇道灭佛,称什么‘万寿帝君’、‘飞元真君’,天天在大内炼丹斋醮,搞得乌烟瘴气;‘宫变’之后幡然悔悟,却连道也一并灭了,提出什么‘宗教信仰自由’之说,自家却对诸天仙佛一概不礼,寺院道观一概不敬,香火灯油钱还要按例抽税,若说是神仙,该属哪门子的神仙?即便孔圣儒家,他也取消官绅免税之优抚国策,释、道、儒三家,他到底信的哪一家?”
李春芳想想觉得夏言说的有道理,就笑着为自己打圆场说:“那便是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大罗天仙了。其实对于‘神仙下凡’之说,我也是不大信的,不过依我之见,经历宫变,兴许天佑我大明,皇上开了天眼,能洞察万物,上知三千年,下知五百年也说不定……”
夏言平生只信儒家,对于仙佛之说深恶痛绝,否则当年也就不会有拒戴皇上亲手所制、赐于内阁辅臣的香叶冠一事,因此,听李春芳这么说之后,他立即反驳道:“你这话更是荒诞不经!什么‘开天眼’,什么‘洞察万物,上知三千年,下知五百年’?鞑靼入寇、京师谋逆、江南叛乱,哪件事是先预料到了的?若能预料先机,有所部署,朝廷也不至于被搞得手忙脚乱,几有亡国之虞!”
“呵呵,你公谨兄这话说的也非是人臣之礼啊!”李春芳说:“推行新政以来,我大明开国前所未有之祸事固然是接踵而至,可事过境迁再重新审视,纵有那些祸事,哪一件令皇上乱了分寸?哪一件又真能乱了我大明江山?说句非人臣敢言之言……”
他盯着夏言,一字一顿地说:“乾坤自在皇上掌控之中,这些事或许出之天意,非人力所能挽回,却被皇上运用自如啊!”
六月暑天里,夏言竟打了个寒战:“你的意思是——”
“朋友之间,畅所欲言,若有不当之处,你就当我没说。”
“说吧,未必你还担心老朽会上疏参你妄言谤君之罪不成?”
李春芳说:“推行新政,本是为了缓解朝廷财政危局,求我大明国富兵强,你我能认识到此节,顶着天下骂名一力辅佐皇上。可朝中如你我者,能有几人?说句丧气话,寥寥无几!宗亲勋贵闹到大内,跪哭请愿;部院大僚虽不明言,却多有腹诽,若非你强力压制,他们来个阳奉阴违,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只怕就要付之东流了;更有陈以勤,还有贵门生赵鼎那等迂腐书生囿于祖制更不明事理,将王道霸道对立而论,以书生意气妄议国政,人言汹汹,天下侧目,朝野上下闹得不可开交,几成无法收拾之势,比之当日礼仪之争,有过之而无不及!适时鞑靼入寇,强敌压境,当此兵凶国危之际,什么书生意气的废话也不必提了,全国一心奋力抗战吧!朝局顿时安稳,皇上便渡过了一次难关。薛陈二贼谋逆,大概也是陈以勤那个书呆子得了失心疯出的主意,圣驾本不在宫里,却要闯宫夺门,滑天下之大稽,圣驾入城,逆贼顷刻而亡,对新政素怀不满的宗亲勋贵、言官词臣也被一网打尽,于日后新政行于天下大有裨益,皇上便又渡过了一次难关。再说江南叛乱……”
“不必说了!”夏言厉声打断了他的话:“为人臣者,岂能如此妄加揣测圣意、诽谤君父?圣德巍巍,皇上纵然要推行新政,也断不会置我大明江山社稷于不顾,行此玩凶弄险之事!”
李春芳笑道:“哈哈,我说什么了吗?我什么也没有说啊!玩凶弄险是你公谨兄的说法,在我看来,皇上可谓审时度势,运用妙乎一心。譬若今日所议的改革军制之事,时机便把握的恰到好处。圣主明君睿智如斯,乃是我大明社稷之幸,万民之福啊!”
夏言想想,觉得李春芳说的也并非毫无道理,便叹了口气,说:“时机把握的确乎恰到好处,可惜处置之法却有诸多可容商榷之处啊!”
“这便更是皇上睿智之处了!”李春芳说:“分明圣意已决,整军思路也详尽确实,却只说是个大略,责成内阁、兵部会同五军都督府商议,拿出个周全的方略来;还逐一纵论我大明一十三省的卫所军现状,决议分步实施,矛盾阻力便小了许多。即便如此也还不够,大约不放心严分宜那个老贼和我这个分管军务的内阁阁员治国理政之才,便让我来找你问计,晓得你断然不会坐视不管,任凭严分宜那个老贼和我这个庸才乱了大明军队,危及江山社稷……”
夏言摇头叹道:“子曰:‘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你子实兄是一甲进士及第、名满天下的状元郎,老朽只是个二甲进士出身,若说庸才,也只是老朽可以论之,你如此之说莫非在取笑我吗?”
李春芳笑道:“若无大小之分,缘何你公谨兄闻听此事便斥我误国误军?”
夏言哑然失笑:“好你个李子实,转了这偌大一圈,竟是对老朽第一句话心怀不忿?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累也不累?莫非要让老朽给你赔罪,才肯原谅老朽失言之过?”说着,就要站起来作势要向李春芳拱手作揖。
“岂敢岂敢!”李春芳慌忙拉住他的衣袖:“你公谨兄向来心直口快,出言无忌,若受不得你区区一句话的诘问,我又怎能与你相交几十年?皇上示下圣意,本就该内阁辅弼之臣弥补缺失,拟定方略然后再大行于天下,让我找你公谨兄这个离职首揆问计只是其一;还有其二,整军之事,严分宜那个老贼和徐阶一个也没能脱得了干系,断不能从中作梗甚或借机生事。没有他们这些朝中大员撑腰,那些军汉纵然对整军不满,又能闹出多大的事来?”
“还不承认自家误国误军?整军之事关乎社稷安危,定要周密谋划,妥善行事,且不能出任何纰漏,怎能如此掉以轻心?”夏言叹道:“老朽呈上那道《请开海禁疏》之后,便已决议不再妄议国政,可你既已在皇上面前力主此事,老朽也只好勉为其难,食言而肥了。”
李春芳笑道:“哈哈,我是奉皇上 ‘问问夏阁老对整军之事有何意见’的口谕来的,公出公入的事情,可不承你这个私情。不过,你公谨兄若要上疏还请快些,我奉旨与兵部、五军都督府拟订方略,若皇上准了你的奏议,我岂不又要重新谋划?”
“食君之禄,便要忠君之事。该是你的差事,却还抱怨什么?兹事体大,皇上且没有催我尽快明白回奏,你子实兄却催起我来了,岂不强人所难太过甚矣!”
“你公谨兄之捷才,张熜张孚敬当年可是领教过的,今日弹章今日回驳,绝不过夜,满朝文武谁不佩服?再者说来,旁人不知道,我李春芳却知道,这些年你尽管没有同意我的整军之议,却一直在考虑此事,想必也有所得,圣恩浩荡,你就不必自谦逊谢了。我还等着你‘一封朝奏九重天,暮回内阁掌权枢’呢!”
夏言一凛:“且不敢这么说!我不做如斯之想,你最好也莫要做如斯之想。睿智天纵如皇上者,是断不会让我再出山了,以资顾问便是让我老有所用,还能再为我大明略尽人臣之本分,这才是真正的浩荡圣恩啊!”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鷹王和他的女兒
- 简介:我和米藍的故事,兵王的延續....
- 116.2万字6年前
- 向胜利前进
- 简介: 当将军难,成为将军更难! 历经磨难的张青山,在战火硝烟的岁月中,是如何从平头百姓一步步成长为将军的……2016,火树倾情打造大抗战!读者群:127770068(谢绝作者)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420.4万字6年前
- 铁血佣兵
- 简介:山野小村出来的一个少年,因缘际会却被跨国佣兵组织培育成了一个狡猾凶残的“狼人”。身负“加百利”杀名的“狼人”,他身上的人性在日复一日的杀戮中正一点点被兽性所吞噬。当他终于变成一件人形杀戮机器的时候,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却遇到了自己的初恋,他会辣手摧花对自己的初恋痛下杀手吗?还是在最后关头幡然醒悟?神秘的塔罗牌占卜;杀人于无形的催眠术;狼母赋予的血瞳;世界各国的军事黑科技……且看一个山村少年如何叱咤佣兵界,成为超级战士一样的无敌存在。本书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请勿对号入座。本书数字版权由“当当”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462.5万字5年前
- 七日之约一一碧落剑
- 暂无介绍哦~
- 6.5万字5年前
- 忆过往,一缕青烟
- 简介:“战勋爵,你放过我吧”男人用着邪魅的语气说“你能逃得掉吗?”
- 11.4万字5年前
- 三国演义(白话版)
- 简介:《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原著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三国演义》原著内容是用古代文言文写成的,而且每个章节内容篇幅太长,今天读者阅读起来极不习惯,并且在原著中的迷信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的污蔑称呼,也与今天的时代的不符合。在我努力遵守《三国演义》主体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特色基础上,对原著内容进行全面翻译和改编,这样希望各位读者喜欢。
- 81.0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