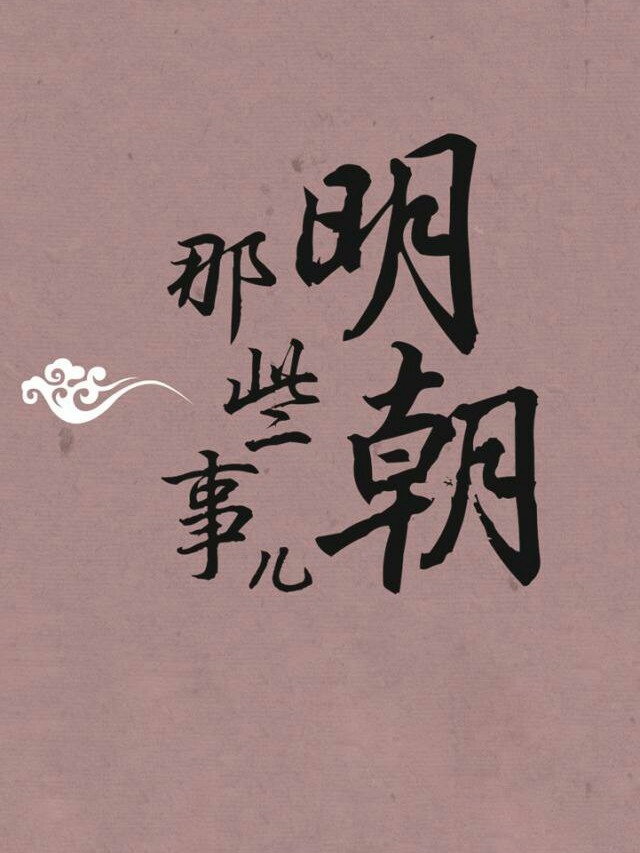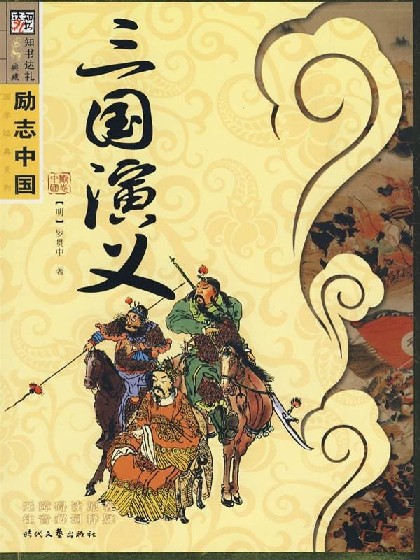第一百零六章公平竞争
朱厚熜再度吩咐杨金水和冯保起身,然后环视座下的高拱、张居正和赵鼎、王用汲四人,说:“话说到这个份上,大概你们都听明白了。沈一石愿意把自家作坊挂到织造局的名下,说穿了是想找个靠山,免得受那些把持丝织棉纺业的乡宦士绅家的欺凌压榨。为何会如此,大概还是朕当年推行的官绅一体纳粮新政还留着尾巴,仍给了那些乡宦士绅家优免恩恤,他们的田产半额缴税,家中还豢养着大量的奴仆为他们养蚕缫丝、纺纱织布,成本就要比那些没有功名的普通棉商丝商少了许多。再加上那些乡宦士绅既有钱又有势,在朝中还有后台撑腰,各级地方官府衙门轻易也奈何不了他们,他们便欺行霸市,包买包卖,逼得那些普通棉商丝商生意都快要做不下去了。那个沈一石迫不得已,才想出了投靠织造局这么个法子。”
其实,不必他把话说得如此透彻,在座的高拱等人早就已经都听明白了:皇上同意了苏州织造局与棉商沈一石联营的奏请,让宫里做他的靠山!尽管此举不免太高看了那些商贾贩夫之流,但那些乡宦士绅确实闹得太不像话,连皇上一力推行的改稻为桑的国策都敢拿来当作发财的良机,还想趁灾贱买百姓的田地,也难怪皇上会如此动怒,将他们视若仇雠,要替沈一石那样的普通棉商丝商撑腰,跟他们斗一斗……
不过,这些卓有才干的年轻官员们的心中同时泛起了一丝忧虑:皇上会否因此而完全废除官绅士子的优免祖制?要知道,当年只是对那些官绅士子按半额计征钱粮赋税,就惹出了多大的一场风波:举子罢考、朝臣论争,乃至边帅投敌、江南谋反,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和皇上的天位都岌岌可危,险遭倾覆。若是全然废除,触动了全天下的官绅士子的利益,天晓得又会闹出多大的乱子……
尤其是赵鼎和张居正,他们两人一个是举子罢考的鼓动者;一个是朝臣论争的挑头人,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脸上都抹上了一层无法掩饰的凝重之色。
果然,朱厚熜接着说道:“那些乡宦士绅自认为国之基石,又世受皇恩,享受着朝廷优免恩恤之制,却不知收敛自省,屡屡违犯国法律令,侵吞夺占百姓田产家财。朕今次巡幸江南,可谓是亲见亲历,实在是触目惊心,让朕也不胜骇然之至!”
听到皇上话语之中已流露出难以压抑的怒气,赵鼎以为圣意已决,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皇上--”
情急之下,赵鼎的声调陡然拔高了许多,显得十分突兀,在君臣奏对之时这就更是失礼。众人都把目光投射过来,高拱慌忙站了起来,抢先说道:“皇上,国朝实行优免恩恤之制,为的是向天下昭示君父崇文重教、礼待士子之心,依微臣之愚见,贸然废弛只恐不妥,请皇上三思……”
原来,高拱担心赵鼎家中富甲一方,又在江南为官,他若是出面谏止君父废除优免恩恤之制,只怕会被皇上视为为己谋私;而自己却出身贫寒,至今也没能在河南新政老家置办什么田产,完全可以说是出于一片公心,再加上自己一直在御前行走,君臣相知颇深,圣眷也非赵鼎可比,自己说出来的话,皇上兴许能听得进去。所以,他就大着胆子,抢先开口了。
不过,高拱这么做,也不单单是与赵鼎有同年之谊,想替他担当罪责;而是因为他实在担心若是贸然废除优免恩恤之制,肯定会引起朝臣士子的反对,导致朝野纷争迭起,甚或会引起天下大乱。这么做固然可能触怒皇上,但与大明江山社稷的安危相比,与皇上对自己的知遇之恩相比,个人的进退荣衰又算得了什么?
朱厚熜板着脸看着高拱,直看得他心神慌乱,低下头去,这才突然笑了起来:“呵呵,朕说了要废除优免恩恤之制了吗?亏你高拱高肃卿给朕当了七八年的秘书,也算是朕身边的老人了,竟把朕这个皇上看得忒低了!”
众人心中一怔:若说高拱君前失仪,倒还说得过去;但要说高拱把皇上“看得忒低”,这又从何说起呢?
朱厚熜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国朝以优免恩恤之制养士两百年,那些官绅士子也自视为国之基石,可真要是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可不见得会跟朕善罢甘休!当年推行官绅一体纳粮新政,只向他们计征半额钱粮赋税,就惹出了那么大的乱子,险些亡了我大明的江山,朕至今思之,仍心有余悸。若是因为废弛优免制度,再惹出一场类似江南叛乱那样的弥天大祸,朕估摸着,在我大明的数万官员、百万士子之中,固然还有崇君这样的忠贞之士宁死不肯以身事贼,也还会有不少人慷慨死国难;但同样也还会有更多的人附逆倡乱,恨不得把金銮殿给拆了,把朕这个皇上给废了!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难道朕就不会吃一堑长一智,却还要去捅那个马蜂窝?”
尽管皇上把话说得十分尖酸刻薄,让在座的四位科甲文官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这些事情都是他们亲历亲见,且去事不远,谁能否认皇上一语道破了其中关窍所在?
好在朱厚熜也是点到为止,随即就正色说道:“这些年里,朕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何当初推行新政,实行官绅一体纳粮,江南数省立刻哗然大乱,其他省份却并未群起影从,附逆倡乱?这固然是因江南乃国朝斯文元气之地,官员士绅为数众多,一呼百应的缘故,也有国朝在两浙实行的优免制度比其他地方更为优厚,江南的乡宦士绅享受着更大的免税利益的缘故。这且不说,他们还能与官员相互勾结,擅自把优免制度扩大几倍、几十倍,然后以田免粮,以丁免役,广开投献之门,大兴诡寄之事。官绅一体纳粮之制或可遏制百姓投献之势;却无法堵死诡寄之门。比如说,一个家境贫寒的生员猎登科甲,就向县令请书册,把亲戚、门生、故旧的田地记在书册上,原本只有几亩田,却能上浮到几百亩到一两千亩,每季派管家督促寄户照额完粮纳赋,由自家交到官府。官府念其有功名在身,名下田产的赋税缴纳个七八成,至多不过九成就不再追缴。一个秀才出身,就能平白享受数百亩田地的钱粮赋税,寄户越多,国家赋税流失的也就越多。至于那些乡宦,年久官尊,三族田产都能入册,其间玩法子弟就多有拖欠不交、故意抵赖者,还说什么‘官府无奈乡官何,乡官无奈我们何’。这几年里,南直隶都察院御史和锦衣卫明察暗访,搜集到江南各地乡宦士绅偷逃拖欠国家赋税的相关证据,竟有一个乡官名下拖欠的赋税折银上千两之多者。一个人便拖欠了这许多,更何况拖欠赋税的乡宦士绅又何止十个百个?真不知有多少国家赋税,都是从这些看似细小的口子里流失了!长此以往,国家赋税开支还得再压到那些无权无势的百姓头上,百姓终将一贫如洗,不堪重负,国库也将一空如洗,仍会走回到豪强兼并土地、国家失田败亡的千古兴衰更替的老路上!”
说到这里,他突然叫了一声:“崇君!”
赵鼎正听得心情无比沉重,慌忙站了起来:“臣在。”
朱厚熜说:“其实,朕把你从松江请到苏州,不单单是要处理齐汉生开衙放告一事,还有另外两层用意:其一,松江织造局亦可效法苏州织造局,遴选有实力有信誉的棉商联营合作,需要你从头到尾都要加强监督,既不能让那些无良商贾钻了国家政策的空子;也不能让李玄他们欺凌商贾、虐民自肥。还有其二,无论棉商丝商愿不愿意与织造局联营合作,他们都照章给国家缴纳赋税,国家就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做到这一点,遏制乡宦士绅以投献诡寄诸法侵占民田、偷逃国税就是首要之务。国朝优免恩恤之制,以江南最为优厚;江南优免恩恤之制,又以苏松最为优厚。那么,堵塞赋税流失的漏洞也该当从苏松而始。”
这么做,无疑是要把自己置于官场士林千夫所指、万人痛骂的境地,即便赵鼎激愤于松江徐家等乡宦士绅仗势欺官虐民等诸多恶行,已开始责令他们退田,此刻心中仍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朱厚熜却不管他的感受,自顾自说了下去:“朕的意思,你们可以三管齐下:一是依律勒令那些骄纵不法、夺民田产的乡宦士绅退田;二是追缴乡宦士绅家积欠的钱粮赋税,用以治理吴淞江;三是苏松甫遭大灾,临江临湖地区地界漫灭,亟待重新丈量田亩、核定地界,可以借这个机会,大力清查乡宦士绅之家投献诡寄的田地,把那些隐身暗处,侵吞国帑民财的国蠹都揪出来。”
朱厚熜正在兴致勃勃地说着,忽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奏报:“启奏王先生,前面的奴才来报,言说苏州知府齐汉生求见杨公公。”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谍战精英
- 简介:一个身经百战的高级特工,一项独一无二的艰巨任务,一份充满真情的爱情故事,一场逆天行道的大型规模运动。一个他,一个她,他们之间,身份悬殊,双重身份的他,是否真的能够把持住这场逆天行道的战争?微信公众号:名剑天涯,群号:346615578,欢迎加入哟!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26.1万字6年前
- (明朝那些事儿)
- 简介:《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故事。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语言幽默风趣。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 0.9万字5年前
- 三国演义(白话版)
- 简介:《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原著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三国演义》原著内容是用古代文言文写成的,而且每个章节内容篇幅太长,今天读者阅读起来极不习惯,并且在原著中的迷信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的污蔑称呼,也与今天的时代的不符合。在我努力遵守《三国演义》主体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特色基础上,对原著内容进行全面翻译和改编,这样希望各位读者喜欢。
- 81.0万字5年前
- 六玺传
- 授六玺者继位为皇帝,面对大司马霍光,手握皇帝六玺的刘贺将如何面对?“大行皇帝早弃天下,遣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衰,行礼仪,居道素食,至大行前,立为皇太子,录入皇帝宗谱,受皇帝信玺、行玺!”
- 3.8万字4年前
- 世界将染上英雄的颜色01
- 一个潘多拉盒子引发的长达80年的斗争,现在还仅仅是开始。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宇宙。不一样的时间。是进化还是创造,是改良还是变革?一切从1934年开始。
- 5.3万字4年前
- 我们终将迎来最终的胜利
- 手举红旗,和这个吃人的世界对抗,未来必将是赤旗插遍全球。欢迎大家评论指点,同好交流群953227533。
- 9.0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