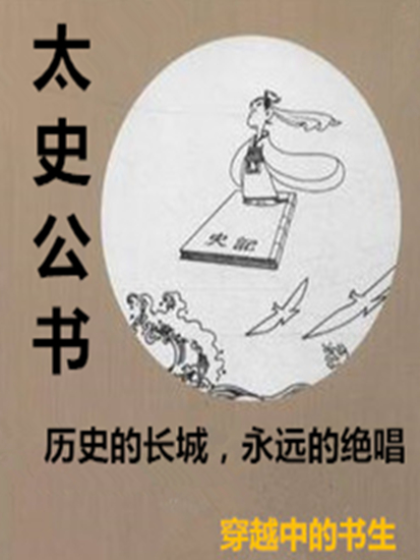第一百零七章潜位窥伺
眼下已是傍晚时分,齐汉生这个时候来拜访,不用说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杨金水小心翼翼地说:“主子,兴许是齐府台找人做证的事情出了什么岔子,奴婢去听听他怎么说,免得坏了主子的通盘部署……”
“不必了。神仙下凡问土地,苏州的事情离不开他这个父母官,朕正想听听他怎么说呢。”说着,朱厚熜站了起来,对杨金水说:“我们都到内室去,你让他进来就是。”
其他人都见惯了皇上这样随心所欲的作派,但赵鼎这个方正君子却有些不满了:“请皇上恕微臣放肆敢言。潜位窥伺干犯大明律令,当以国**处。皇上既为一国之君,自应有一国之君之威仪,行止也皆有法度,潜位窥伺之举,更恐非人君所为!”
众人心中都是一哂:大明律法的确严禁潜位窥伺,情节严重的要处以大辟之刑。但跟其他许多律令条例一样,都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一纸空文。原来的厂卫、现在的镇抚司都负有监督文武百官之责,行事是何等的横行无忌!毫不夸张地说,哪个朝廷勋贵重臣家中没有安插有眼线?哪个官员的一举一动能这个赵鼎却跟皇上说什么大明律令,岂不迂腐可笑之至!
见皇上醇醇地看着自己,不象是龙颜不悦的样子,赵鼎又说:“微臣还要斗胆劝谏皇上一句:古人云,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云,君臣之间,以礼相交,不可言戏。戏则不敬,不敬则慢,慢而无礼,悻逆将生!皇上不可以此不信不礼之举待臣下……”
给皇上当了七八年的秘书,高拱深知皇上最讨厌别人在君前奏对时掉书袋,更不用说赵鼎的话还是这样直白无忌,当即吓得魂不附体,忙厉声喝道:“大胆……”
朱厚熜笑着摆摆手,阻止了高拱,对赵鼎说:“崇君啊,你这话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朕还要问你一句:前日在松江,你和王润莲若是知道朕就在内室,还敢跟高肃卿那样说话,把你松江府的实情和盘托出吗?”
“这……”赵鼎无言以对了。他虽说自问刚直敢言,也打定主意要把松江之事面陈皇上,但能不能象那天和高拱争辩之时那样直言无忌,连他自己都不敢保证。
“既然如此,朕潜位窥伺一次又何妨?”朱厚熜叹道:“其实,朕又何尝想这样做?可是,为人君者,最怕的就是满耳朵都是颂圣之言,却听不到半点真话。嘉靖二十三年鞑靼犯境,北直隶、山西百万难民涌入京师,若非一位国子监生员向朕敬献了一块荷叶米钯,朕竟不知道京城市面的米已卖到了二十两银子一石!九门之内尚且如此,更遑论万里之外的江南!朕是让下面的臣子给瞒怕了啊……”
赵鼎羞愧莫名地离座跪了下来:“罪臣迂阔执拗,不能体念圣心深远之于万一,请皇上责罚!”
“责罚什么?朕深知你是方正君子,向来以正道事君。让你跟朕一道潜位窥伺,确实难为了你。不过,正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做事只要问心无愧,就不必拘泥于虚礼小节,如此方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赵鼎又要叩头认罪,朱厚熜笑道:“快快起来吧。织造局在人家的地盘上开府建衙,许多事情都少不得要苏州知府衙门协助,岂能让堂堂的知府大人在外面久等。”
赵鼎心中苦笑一声:看来,要劝谏君父言行举止遵循礼仪法度,断非朝夕之功啊……
恭送皇上进入内室,杨金水这才吩咐将齐汉生请了进来。一见面,他就笑着问道:“齐府台,这么晚了来找咱家,可有何吩咐?”
齐汉生满脸愧色:“吩咐不敢。下官冒昧前来,是有个不情之请,还望杨公公再助下官一臂之力。”
“怎么助你?”
齐汉生说:“今日下官去了杨公公所示下的那几处人家,奈何那些百姓虽身受许、郑两家凌虐,却慑于他们多年所积的淫威,都不敢出头投状控诉。杨公公昨日也曾提醒下官,许、郑两家已暗中派人监视着下官,想必下官今日行止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线。下官以为,他们势必要不利于那些苦主,故此想请杨公公派出织造局的上差暗中潜伏在那几户苦主家中,一来防备他们狗急跳墙杀人灭口;二来拿下他们的刁奴恶仆,便能拿到他们虐民罪证了。”
杨金水心中暗赞一声:原来,这位齐府台今日出府暗访,其实不只是为了说服那些百姓出头告状,还给那些乡宦士绅埋下了一个陷阱,等着他们上钩!果然不愧是探花,心思慎密,难怪主子要宽恕他的罪责,留下他来对付那些为富不仁的乡宦士绅!
不过,他即便有心答应齐汉生的要求,却又考虑到圣驾今夜要下榻织造局,不管是随行护驾的那些镇抚司校尉,还是苏州织造局的差役,都要留下来护卫圣驾,责任何其之大,哪里还能抽出去人手保护那几户寻常百姓?
“不是咱家不想帮你。这是你们苏州知府衙门的事情,咱家可不敢越俎代庖啊!”杨金水假装为难地苦笑一声,推辞说道:“齐府台有所不知,嘉靖二十四年,吕公公出任平叛军监军,皇上便下过圣谕,告诫我们这些宫里的人,出京只带耳朵和眼睛,不能对地方衙门的差事指手画脚,更不得随意干预地方政务。咱家把那些罪状告知你齐府台,已是违了皇上的圣谕。还要让我织造局的人去拿人,这可触犯了宫里的天条了,咱家可担罪不起啊!”
“杨公公,下官也知道不该劳动宫里的上差,但这么做,实在是没有法子……”齐汉生说:“许、郑两家盘踞苏州多年,与官吏多有勾连,那些苦主奇冤多年不得昭雪便是明证。下官若是调用府里的差役,等若是在给他们通风报信,不但万难拿到他们虐民罪证,只怕那些苦主还会惨遭他们的毒手。”
杨金水敷衍他说:“齐府台过虑了。朗朗乾坤,天日昭昭,苏州也是我大明的苏州,堂堂一府治所,有官有法,他们岂敢那样猖獗?”
齐汉生沉痛地说:“杨公公有所不知,苏州乡宦士绅之猖獗,断然出乎常人常理想象,实在令人闻之不胜骇然之至!昨夜得杨公公指点之后,下官便调来往年的案卷细细查看。查知嘉靖二十七年,苏州城中曾发生过一起命案,有位名叫刘华文的秀才,其女刘月娥聘于府学生员李正泽为妻,尚未过门,一次郊外踏青之时被许子韶看中,强抢入府,欲加**。刘月娥抵死不从,触柱而死,尸体被抛于城外荒野。刘华文连同李正泽愤然投状于苏州府衙,控状上分明写着许子韶强抢刘月娥时,有刘家丫环在场,还有不少街坊邻里亲眼目睹,时任苏州知府的王恩茂却以并无旁证为由,拒不受理,将刘李二人乱棍打出府衙,刘月娥之死也以遭遇强盗,**不从自杀身故而草草结案。其后不久,刘华文和李正泽两人便没了踪迹,一说是被逼走他乡,但下官以为,十之**是许家唆使恶仆或买通强梁,将两人暗害。刘华文的老妻因女死夫亡,诸般惨祸接踵而至,竟致疯癫;李正泽的寡母也因之染疴而不救。两户诗礼之门,接连家破人亡,至今沉冤未雪,凶犯却仍逍遥法外。前车之鉴,下官万不敢视百姓性命为儿戏!”
略微停顿了一下,齐汉生接着说道:“杨公公,下官已草具一疏,向朝廷请罪。即便皇上天恩浩荡,容留下官性命,下官也断无颜面苟活世间,已备下了鸩酒,一俟朝廷新委知府到任,便仰药自尽,以尽臣节。惟是苏州百姓多年深受那些乡宦士绅凌虐,民生之苦,已是苦不堪言,更不能因下官之故便惨遭杀身之祸。杨公公素怀仁者爱人之心,还请施以援手,帮助下官保护那些苦主。至于此事始末,下官亦会在奏疏中将详情奏陈皇上,以皇上之天聪睿智,断不致因此怪罪杨公公及织造局有干政之嫌。”
听到齐汉生说得如此悲痛恳切,杨金水不禁怔了一怔,随即叹道:“想不到苏州那些乡宦士绅骄纵不法竟一至于斯!不过,齐府台也不必自责过甚,苏州之事到底是谁的罪过,朝野自有公论,皇上更是睿智天纵,断不会听信旁人的一面之辞。只是……”
“只是什么?怕担干系,还是怕得罪那些乡宦士绅?”内室传来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打断了杨金水的话。
杨金水和冯保两人赶紧跪了下来。齐汉生还在诧异之中,就见“呼啦啦”一下子从内室走出一大群人,领头的那人,不是大明王朝嘉靖皇帝朱厚熜,更是何人!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红色家族
- 简介:以主人公史大鹏家三代人为主线,描写近一个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风云变幻。
- 新书6年前
- 逆袭唐末之枫羽帝国
- 简介:普通大学生醉酒乱晃,不小心错踏老爷爷仙界领地,被打开的时空之门为他开辟了唐末新生活。乱世朝代,兵荒马乱,为求生路人们费尽周折。少年虽初来乍到,却懂得人民疾苦,为救苍生,铤而走险。临危受命,他从此投笔从戎,为兄弟两肋插刀,为天下血染满襟。绝境逢生,殊死一战。建枫羽帝国,与唐势力楚汉两分。且看穿越后的屌丝如何逆袭唐末,震撼天下!历史为骨,艺术为翼。兄弟情深,儿女情长!枫杀一出,所向披靡。枫爷一现,天下莫敌!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285.3万字6年前
- 中华武将召唤系统之大晋
- 简介:刘代的讨代路······
- 1.3万字5年前
- 从贝加尔湖到大汉长安
- 古老神秘的贝加尔湖,广袤无垠的泰加林,是中原王朝从未涉足过的秘境。伊洛,一个来自未来世界的穿越者,他和同伴们将以贝加尔湖水系为地理中心,以原住民和流落草原的中原人为核心力量,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度,与南方的西汉帝国、西方的罗马帝国遥相呼应,并驾齐驱。
- 12.1万字4年前
- 天山南北1933
- 21世纪20年代的新疆,集体穿越到了1933年4月,沿着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和铁路的所有城镇,所有有机场的城市,建设兵团下属的城市和农场,都跟着一起穿越了过来,会在这个世界产生怎样的碰撞?QQ群号:479296162(一群)QQ群号:956766219(三群)
- 34.3万字4年前
- 水煮《史记》
- 简介:如何水煮?如何将历史与现实,来一番有趣的关照呢?历史,其实很有趣,可以正经地解读,或者不正经地另读?有什么不可以?历史从来都是一个小姑娘,扮成花,弄成云,如果你的想象够穿越,真的,所有的历史,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不过是还在发生的现代史。太阳底下无新鲜事。那么,水煮一番《史记》,也许,别有一番滋味呢
- 4.2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