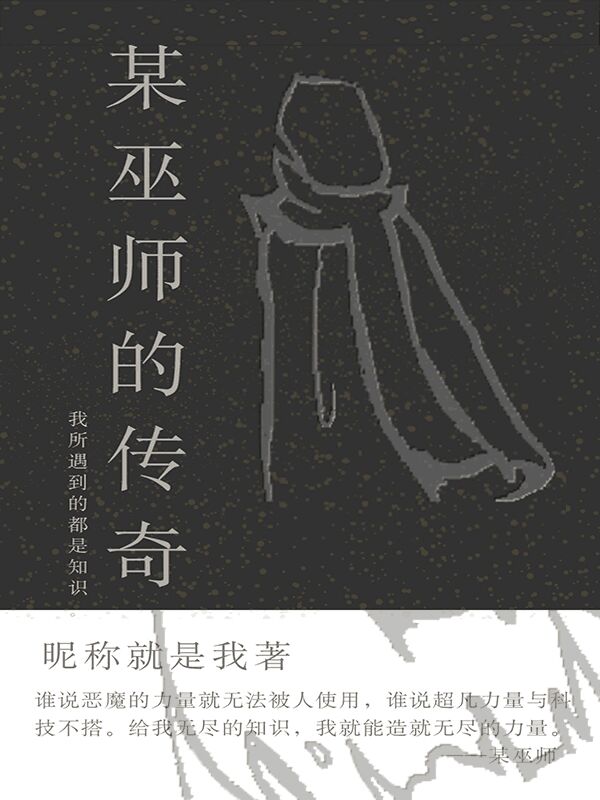夏日的恋爱综合症(上)
死寂,空洞。
只有孤独的黑。
对于失去记忆的人来说,做梦是一种奢侈的行为。
他们没有足够的经历去支撑大脑皮层的活跃,犹如刚出生的婴儿,纯白无暇,也乏味如一杯沸腾得过久的白开水。
凡夫俗子大多善于隐忍,那些在阳光暴晒下不得生存的阴暗思绪潜伏在角落悄然生长,开出的荼蘼之花斑斓绚丽,深夜,梦深,她人无所涉足,自然能肆意生长,究竟是毒是药,疯狂还是良知,全凭个人喜好。
若是没有梦,便没有色彩,也没了欲求。
司无命知道自己没有做梦。
她也知道自己正在沉睡。
这是种玄妙的状态,一定要比喻,就是灵魂脱离躯窍,天眼乍通,收不住手脚,泼猴离了五行山,动动念头就能翻出十万八千里之外。
她看到自己躺在沙发上,盖着那个名为西蒙的男人的斗篷,大衣放在一边,仅着一件白衬衫,也不知道冷不冷。
为了书写方便,西蒙将衬衣袖口挽到了肘后,司无命能清楚的看见他握笔的手指骨节分明,那上面还带了些薄茧,她的纹身不自觉烫了起来,仿佛已经感受到了被触碰时的痒。
茶凉了个通透,西蒙也不讲究,一饮而尽,喉结的律动极有规律,一上一下,那处的皮肤在手臂的衬托下显得极其白皙,青筋若隐若现。
有些许水珠仍残余在唇角,西蒙舔了舔,他的唇极薄,沾染了水光后显得尤为性感。
不太妙。
少女对自己说。
胸膛里那个跳动的雏鸟羽毛状的器官依旧冰冷似铁,失去一切的她无赖得像个地痞流氓,百无禁忌,没有牵挂也不用虚与委蛇,脱离了现代社会的条条框框,仁义道德皆为废纸,心动一词好似上辈子的事,丘比特也好月老也好,闲的没谱也应该轮不到自己身上。
可是现在她躺在另一个男人的房间里,盖着他的衣服,身上刻着他的名字,并对着他的唇,有了亲吻的冲动。
我他妈没毛病吧?
司无命迷茫地看着墙上的钟。
兀自走动的秒针滴滴答答,并不屑于回答区区一个人类的问题。
少女开始纠结了,造物主赐予人类一个精妙的脑瓜,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奇迹,某种意义上人类确实做到了,他们心怀爱与梦想,干出的事儿大多叫人想要把他们折吧折吧扔回娘胎退货重造,灵活的思维通常带来的不是一条康庄大道的举世传奇,而是山路十八弯的曲折连环。
我们的sinner冥思苦想,左思右想,奇思妙想得好不快活,魂魄在空中转了个圈,竟胆大包天的凑近了西蒙,企图趁着这人不知鬼不觉的天时地利操作一番。
西蒙的唇形优美,嘴角向上抿出自然的弧度,金属色泽的眸子微合着,在少女能够细细数清他每一根睫毛的时候倏地转了方向。
司无命炸了毛。
他在看着我。
带着些玩笑意味,亦或者是自己的错觉,不,他确实看着这里,看着自己的方向,眨了眨眼睛,唇角上扬——
骤然传来的引力拖拽着灵魂灌入躯体,这一觉睡的极沉,以至于短时间内使不上力气,慌乱中掀了斗篷,却连着靠枕一同滚下了沙发。
头着地,真疼。
低声埋怨着的少女扑腾了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斗篷落了大半,那张苍白但精致的脸杵着眉头,一副恨不得用犬齿咬点什么泄愤的神情。
“醒了?”男人好整以暇。他单手撑着侧脸,略微抬头,脖颈至下颌形成一个优美的弧度,“我以为你要到明天才会醒,还打算让应徐直接送饭上来。”
“你以为我是什么?树懒吗?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里有十八个小时都在睡觉?”sinner平白无故生了一肚子的火气,她都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面对自己的顶头上司犹如炸了膛的枪管。这仅仅是他们的第二次交流,但西蒙总能在一句话内叫她愤慨得想要踩她一脚。
这个男人抓住了自己所有的把柄,她了解自己,看透了自己的内心,活像给她装了个电波感应器,一闪而过的小心思都逃不开他的眼睛。
真是让人不爽。
可是西蒙愉悦极了,他笑得很开心,是猫儿被人抚摸舒服了后的反应,从喉咙里低低地发声,拖着长长的气,砂纸样摩挲着司无命的耳膜。
她不由自主地缩起了脖子。
“去吃饭吧,然后从明天开始工作。”兴许是笑够了,院长大人总算是说了两句人话,“白烬——你的搭档——今晚会回来。”
“给我一个把你留下的理由,戎娜应该说过,我们不收闲人。”
他站起身,舒展着身体,白色布料下,肌肉线条清晰可见。
少女揉了揉眼,一瞬间,她觉得西蒙的眸子变得又细又长。
像猫,不,像豹,磨牙吮血,散发着迷人的野性。
男人向着司无命走过去,脚步不快,两人擦肩而过,西蒙拿起斗篷,拍了拍并不存在的尘埃。
他是故意的,与sinner肩膀相靠,转过头就是少女的耳尖,凌乱的黑发长时间没有修剪,已经蓄了不少,用手指勾起一缕,帮她束在耳后,露出黑曜石般的,唯独瞳孔泛着湖绿的眸子。
“还有,我不是猪。”
少女虚着眼,面颊憋的通红,她摇头躲开西蒙的手,逃也似的走出了房间。
这家伙有病。
司无命告诉自己。
然后我也有,因为他碰我的时候我她娘的竟然希望他摸摸我的头。
绝望的少女气的双手发抖,开始认真的考虑起夏日与思春期的学术联系。
神经病院并不日常的日常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圣女大人请不要缠着我好吧
- 「快点签,不就是个卖身契吗?」『你这卑鄙的恶魔!』「怎么说都好啦~签完你就要全身心的侍奉我了」『我…我才不会!』「那算了,我走了」『等,等下!别走!我签还不行吗!』「圣女大人果然懂事~」『你要按照约定,把我的……』
- 1.5万字5年前
- 转生零级猫耳少女
- 咱是一只可爱的银色小猫咪~咱喜欢吃鱼~咱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猫猫~哼哼哼...要是欺负咱所重视的人...[白雪酱(猫猫作者):好好好...你是最可爱的...不对是最厉害的~](啊呜)哼~有你好看喵!咕...喵喵喵!(..
- 26.9万字5年前
- 黑与白的死或生
- 作品标签:变身、百合、无敌、末世听说过要用魔法打败魔法吗?那魔王呢?当魔王被勇者杀掉后,被神作为棋子再次投入到了一个世界,要求他到那个世界解决掉那里的魔王。但这身体怎么回事啊?十多岁的身体,还是个女孩子的,玩我呢?如此,新生的魔王..
- 0.6万字5年前
- 斗罗大陆之桐浩
- 简介:霍雨浩和童童在斗罗大陆里发生的爱情故事。
- 1.9万字5年前
- 校园之麟娜恋
- 简介:唐舞麟,这个史莱克学院的大哥大,遇上了学霸古月娜,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坚持日更,不喜勿喷
- 9.8万字5年前
- 某巫师的传奇
- 神秘的世界,神秘的巫师。这是一个探索世界追求知识的巫师的故事
- 11.1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