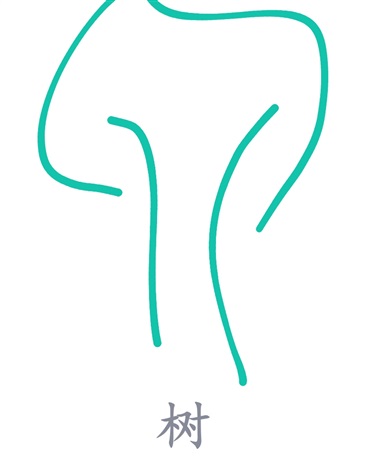第五章:泥拳坷垃蕾(2)
这个年轻人与电视里的那个胡子拉碴的碎灭者不同,他胆小、单纯、羸弱不堪,但这恰恰是我抛弃原本想法的原因所在。想起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自己对目标的那阵强而有力的抗拒感,我不禁感到可笑:这样一个普通到随处可见的男大学生,怎会给我们带来预想中的那些危害呢?
即便他没明说,我也能猜个大概齐:成为碎灭者并非是他原本的意图,换句话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它,也没想变成它,和喷涌者、马里斯那些家伙不同,他更像飓风,是在某种机缘巧合之下拥有了超乎想象的能力。
可我该告诉他飓风的秘密吗?不,不行,现在还远不是时候。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哈,当然了,我也还年轻,不过算不上这类“年轻人”,他们憧憬暴雨侠,因为他那些无人不知的经过了重重包装的英雄事迹,和浩如烟海的虚假故事的情节。是啊,他们都被洗脑了,想想看那些电影吧:暴雨侠1/2/3/4/5/6,十几个小时,近十年间连续不断的狂轰乱炸式的雄伟篇章,这谁能顶得住?那些图谋不轨的编剧、导演和帅气凛然的马克·赞德文把一个自私自利的超能力混蛋活生生地塑造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伟大英雄,谁又能为他证明呢?是用特效堆积的海啸那般的水幕,还是声线优雅的配音演员照本宣科念出来的自白?改编自真实事件,是啊,他们总是那么说,就好像“改编”两字根本不重要似的,记住,改编自真实事件不是说它就是真实的,只不过是说它也有其灵感来源而已,与所有那些虚构故事一样,什么都有灵感来源,什么都有原型,只不过它们的原型更形象具体,它们的思维加工也更简单明了。暴雨侠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吗?
想到这,我气不打一处来,只好在比起以往我带过的那些孩子来,碎灭者还算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这让我对他的好感度提高了不少。
看得出,他对暴雨侠的憧憬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根深蒂固,但我的那一番自白似乎感化了他:他明白我的感觉,明白恶徒们的无奈,明白暴雨侠是个多么恶心的家伙……也许这还算不上,但至少也明白他有着令人恶心的一面。我大胆猜测是变成碎灭者的那段经历让他能直视我们所面临的现状:这不是一个正恶分明的世界,人们也不能简单地用英雄和恶徒来定义、分辨他人,即便这让他们更觉得心安理得。可是当然了,这种狭隘的认知方式实在是太荒谬了。
招募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不得不承认拳手确实有看人的眼光。我们不仅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战力,也许,我还得到了一个知己。
我渴望知己,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
在思考了很多关于正义与邪恶、英雄与恶徒的宽泛而复杂的问题之后,我这才弄清楚自己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我的手机还在学校。”我说,心慌到难以言喻。
“啊?”看她的表情,坷垃蕾应该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
“你先给你在学校的朋友打个电话,然后再给你家长打。”说着,她从制服的上衣兜里掏出一台屏幕巨大无比的智能手机,“赶紧!”
“我该说啥啊?”
“就说你平安无事啊!”
“那我在哪,去哪了,什么时候回去?”
“你确认要加入我们了吧?”
“虽然还不确定,可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加入我们很好的,你不用干什么,也不用交会费,有时候还有能赚报酬的活动和工作,如果你愿意的话……”
“嘿!”她怎么突然开始夸耀起来了。
“啊,噢,你和学校说你回家了呗,因为家长担心。”
“那他们要是去和我爸妈确认呢?”
“提前和你爸妈说学校封锁了,你很安全,已经和其他同学一起被保护起来了!”
“这说法漏洞百出吧!”
“你先说,完事儿组织会帮你解决!”
“好吧。”真奇怪,我居然会如此相信这个神通广大的“组织”,这算是件好事吗?如果我觉得它是的话,那仔细想想,似乎还真有点可怕。
在拿到手机的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只冒出了一个人和一种声音,与坷垃蕾那冲劲儿十足的说话方式不同,她的声音温柔沉稳,仿佛充满了抚慰人心的力量,然而每每听到、想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我就会不自觉地感到失魂落魄,那是种深厚而难以琢磨的蕴藏在满足背后的悲伤。究起这份悲伤的源头,我害怕自己会将她的自由与我的痛苦联系在一起:她不属于我,不只会和我一个人讲话,不只会与我一个人外出。她的生命中有我,也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与那些人相比,我尤其害怕自己并不特别。
于是我一门心思地准备给她打电话,就好像任何一个特殊情况都是我用来联系她的挡箭牌。我发现自己不择手段地想和她说话,不管借口是碎灭者的失控,还是其他任何糟糕的其他人的苦难。焦躁和渴望中,我清楚地明白,这是个自私的想法。
可是……在按亮坷垃蕾的手机屏幕之后,我才在惊叹“她的手机怎么没有解锁密码”的同时意识到自己并不知道她——我心心念念的同班女生的手机号码。
无奈之下,我只得打给了总体上来说不那么招人烦的室友吉舒。
“喂,您好?”他礼貌地说。
“吉舒,我,禾尽,我的手机在宿舍吗!”
“禾尽!”他叫了一声,接着声音便变远了,“老师,禾尽来电话了,他应该没事。”
“喂?”你先跟我说啊,喂!
“禾尽?”电话那头传来了陌生而熟悉的尖细女声,我瞬间便猜到她是我的班主任,也明白此时她的心里一定在想:这混蛋小子,居然差点就让我担责任了!
“啊,老师,老师好。”
坷垃蕾在一旁撅起嘴唇,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撅起嘴唇:“我是禾尽。”
“你在哪呢,你怎么样?”班主任的话里充满焦急,在这之中我竟寻不到自己预想中的那种焦躁和怨恨。
“老师,我很好,我看到学校发生的事了,我今早回家了,我爸妈说应该和您汇报一声,所以才给您打了电话。”哦不,我忘了自己打的是室友吉舒的电话。
好在她没注意到这点:“真是的!今天发生了那么大的事,私自回家怎么不跟学校请假啊!你爸妈在旁边吗?让你家长接电话!”
“啊,啊?”我向坷垃蕾投去求助的眼神。
找我爸妈,我用唇语说,我爸妈。
她上前一步,一把夺过电话:“喂?您好,哎,我是禾尽的姐姐。”
你是我的什么?你是谁的姐姐?
“哎,哎,对。”她笑着说,“是的,对,哎,很抱歉。”
天哪,真可怕。
“好的,好的,您放心,哎,好,嗯嗯。好,再见。”
我看着她,她回过头。
“搞定了,快给你爸妈打。”她把电话丢给我,和班主任通话时脸上那快要溢出来的笑容立马就消失不见了。
“你真绝了。”我说。
“明明俩小时前还是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她又露出另一种笑容,我看出那是对我的嘲讽。
我拨通家里座机的号码。
“喂?”是我妈接的电话。
“喂?是我。”
“啊,怎么了?”
“我用同学的手机打的电话,我的手机被摔坏了。”
“啊?不是刚买的手机吗,怎么又给摔了,那怎么办啊,之后用什么啊?”
“哎?”我纳闷起来:为什么她只担心手机,难道他们不知道碎灭者的事件吗?
“我跟您说一声,我没事,现在学校封锁了,不用给我打电话了,我完全没事。”
“封锁了?为什么啊,出什么事儿了?”她的语气变了,变得快而强烈。
“看新闻吧,不用给我打了,这边非常忙,反正我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过几天就回家。”
“快开电视,小尽说学校……”趁她对我爸发布起指令的这段空档,我连忙挂掉了电话。
“搞定了?”坷垃蕾问。
“差不多吧,不过一会儿估计还得打过来。”我说。
“没事儿,你姐姐帮你接。”她笑着说。
“我爸妈能不知道我有没有姐姐?”
“噢,对哦。没事儿,那你的新班主任帮你接。”
“行,行。”我懒得再说话,只是结束了话题,随迈开了脚步的她继续前行。在几乎横穿了整个鹅县景区之后,坷垃蕾停在了一个矮小的储物间前。
“你能随时变身吗?我是指,变成那副满身肌肉的模样?”
“不能。”
“你能控制自己变身的时机吗?”
这问题和刚才的有什么区别?
“不能。”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变身?能自己主动变回来吗?变身之后能控制住自己吗?”
为什么她会突然间问我这么多问题?
“不能。”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今天一起来就突然是那个样子了,我好像和你说过。”
“啊?噢。”我猜她没听,即使听了应该也没过脑子。
“怎么了?”
“在进入总部之前,我们必须先确认你是否稳定。”
“啊?那刚才那么久都干什么了,非到现在才确认。”
“那也算是在确认了,不过……抱歉啦。”
为什么要道歉?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发问,一阵强而有力的眩晕便从后脑袭来。在逐渐变黑、变模糊的视线里,一个高抬铁棍的男人像万变不止的万花筒那样时而变宽,时而变扁,他的身体随着日光的影子闪亮,手中的铁棍却始终处在同一个位置。
“带他到酒馆去,海报。”坷垃蕾的声音越来越小,很快便消失在耳畔。
暴雨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妙手圣医
- 简介:野路子出身的医术高手秦帅,来到雾都成为美女医生的首席助理,原本只想着救救人,顺便泡泡妞的他,却每每被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阴谋之中,惹了一堆强敌,杀手组织、毒术唐门、苗疆巫蛊、东南亚降头术,以及境外黑白灰各种势力组织……且看医武双绝的他,如何在敌人的包围中纵横捭阖,如何破灭碾碎所有的阴谋阳谋,最终怀抱众美,逍遥都市。10月1日-10日,每日三更,求一张保底月票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280.6万字5年前
- 星海幻艺
- 简介: 寻找梦想的归宿,寻找约定中的谎言,他......能否找到梦想的约定?
- 22.3万字5年前
- 有个美少女怪异一直想吃掉我
- 你见过七岁的吸血鬼吗?我见过,而且还很可爱!这样的吸血鬼我要养十个!!!如果她不吸血的话那就更棒了!!!
- 23.6万字5年前
- 无尽满月谭
- 清晨时,走过薄雾笼罩的街道,街上一个人也没有。究竟是为什么会看到月亮?又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超脱常理的事?我已经感觉不到我的内心了,漫步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这一切不是梦,却比梦更像梦。
- 1.1万字5年前
- 发个微信去三国
- 简介:手机被雷劈中,微信与三国演义取得联系,命运从此改变,三国历史也由我来谱写,天晓得是谁统一全国。曹操、孙坚、董卓、袁绍……大财主们的竹杠不敲白不敲。看上貂婵肿么办?娶她呗,打得过吕布?我表示不用亲自动手;看上甄宓肿么办?抢她呗,袁熙放过你?我很淡定;看上小乔肿么办?撬她呗,周瑜不发狂?很有难度,但我有诸葛亮。公司谁是技术人员?当然是华佗。技术主管呢?保密哈。贴身保镖又是谁?有几个,其中一个是拿青龙偃月刀的。当上商界大亨,四面树敌肿么办?好办,兵来将挡,美女来了自己挡。(读者QQ群:523176470)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207.4万字5年前
- 从天而降君临世界
- 我是林鹿,林深时见鹿的林鹿。(ps:没有大纲,没有思路,什么都没有,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所以更新可能不稳定,当然于此对应的人气大概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笑。不过无所谓了,我只想写一点我想写的东西,无论有多烂。)
- 1.5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