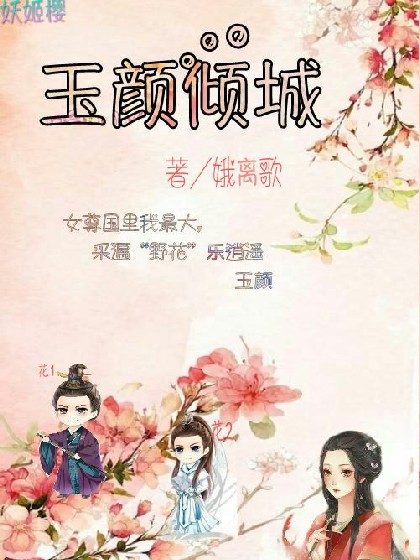第七章 听雨(1)
元叔一脸错愕,万万没想到这位最护女儿的陈大夫,竟然能够主动将她扔给官家人——出来胡闹。
月下料想他也该吃惊,故而没去解释。她将手中的桃花香囊捏了又捏,直接甩给了元叔。
趁他慌手慌脚时,月下侧脸道:“叔,帮忙留心着你说的那二位姑娘,如果她们再来,遣人去找我。”
“找你作甚?”
“你没看见啊,”月下翻了个白眼,赤裸裸地无奈,“那是官爷要找的人。”
她朝沈大人离去的方向瞥了又瞥,心下里不禁暗暗叹息一声,便摆手告辞。
北镇抚司·诏狱
昏暗的四角刑房,唯一的小窗口只能透出一团朦胧不清的月光。剩下的,不过是尘埃、血腥以及无休无止的挣扎。
桌上的一点昏暗烛光,微微跳动几下,苟延残喘。
哗啦——
木盆里的水兜头迎面而来,力度刚好将他泼醒,刺客动了动手指,一时间却有撕心裂肺的痛蔓延至全身。他猛地咬住下唇,一丝丝鲜血沁出。
抬起头,在模糊的视线下,他看见身着飞鱼服的青年。
刺客挑衅般地轻笑一声。
沈淮景把玩着一把小利刃,寒光瑟瑟,映出他凛冽的半张脸。
“还是不想说?”沈淮景开口,语气平淡十分、不冷不热。
刺客将头向后微仰,换了个稍微舒服的姿势,揶揄地反问:“说,谁派我来杀你的?”
沈淮景微微蹙眉:“只怕你要杀的不是我。”
刺客闻言,眼底闪过几不可察的惊诧,旋即闷哼两声:“我也只怕,你现在自身难保,中了毒,还有心思来审我。”
他说的不错。沈淮景自来时的路上,心口便隐隐作痛,只是暗隐自忍,始终不曾外露。
那张薄唇,早已苍白无血色。
幸而来的路上,服了些药,大概可以支撑一会。
——他怎么能够,在这些人眼中示弱。
沈淮景眼底掠过冷光,朝刺客身后的差役颔首。行刑者当即会意,利索地手气刀落,斜斜削去刺客中指上的皮肉。
“啊——”他哑着声音,犹如困兽般嘶吼。
“这叫剔骨,”沈淮景指尖划过刀刃,面无表情,“倒不会让你死的痛快,只是一点点的折磨你。”
刺客急急喘几口气,嗓子里已有血腥味四处蔓延。他阖了阖眼,竟然还能冷笑一声,只是粗粗喘着气,说起话来跟着断断续续:“我……听说过,东厂的刑罚……可是?”
沈淮景蹙眉,等着他继续说。
“沈大人……不是最厌烦那群宦官吗,怎么,拿他们的东西来用了?还是因为,你那位好义父……”
逞一时嘴快,此人不曾看见,这“义父”二字方落,沈淮景手中的利刃便像他掷去,顿时嵌入刺客的肩膀。
寒意森森,他底哑道:“他——也是你能够提的?”
刺客早已耗尽力气再也吼不出,只能口吐鲜血,强忍疼痛,直直看着他,挑衅之意,不言而喻。
沈淮景拧眉,心口突然像是被撕裂一般。
他招手,边示意下属把人带下去,边转身出门,穿堂风稍稍掀起他的一侧衣角。血腥的气味环绕在舌尖,他的喉头微微下划,须臾闷咳一声。
连着几日都是小雨天气,氤氤氲氲的一层,分不清是烟还是雾,只朦胧地,裹住视线稍远的地方。
药堂前偶尔有行人路过,踢踏着水花声,也不见进来。月下百无聊赖地躺在竹塌上,向左翻个身,随后又翻回来,一副恹恹地神色,明显是心神不宁。
“怎么了,滚来滚去的。”陈大壮斜斜地瞥她一眼,手下整理药材的活并未因此停下,“一大清早就见你这样,累不累?”
“什么叫滚来滚去?”月下轻啧一声,没好气道,“我这是在想爹爹。”
“哦?”陈大壮草草表示疑问。
她起身,拉了拉身上天青色袖衫,探头道:“你说,如果沈大人那天听我的,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肯定是没人能医治好,所以要亲自来请爹爹。”
陈大壮轻笑,没奈何道:“你这哪是想爹爹,分明就是在想沈大人。”
月下鄙夷地冲他做了个鬼脸,一本正经地解释:“什么话,他们家,那是何等有权!他爹是都察院左督御史,义父江彬是锦衣卫指挥使,万一咱爹爹没办法,那二位生了气,咱吃不了兜着走!”
“非也。”陈大壮缓缓摇头,将筛子里的白芷放回药柜,“爹尽力而为,他们也不会为难什么的。”
“你不懂……”
各占各理,月下不服,还要继续反驳,却见陈义生打了把竹青油纸伞踩着水花急急赶回来。他才一进门,月下便“蹭”的蹦下竹塌,凑去忙问道:“爹爹,如何,他们没为难你罢?”
陈义生边递了个方子给陈大壮,边摇头叹息,欲言又止,却就是不解释一句。
他这副样子颇是不饶人,月下低头一猜,旋即向后退几步,捂着胸口作惊诧状:“爹,他不会是快死了吧?!”那她不得愧疚死。
桌上的一盏茶是陈大壮替自家爹爹随时备着的,陈义生捞起紫砂茶壶,缓缓朝哥窑瓷杯里添水。那里面泡的乃是江南地区新运来的春茶,绿盈盈的一柱水流出壶嘴,只看看便觉十足沁人心脾。
陈义生喝了口茶,才淡淡道:“沈大人的毒,我可以解。”
听他这么道来,月下长出一口气,拍了拍胸脯,颇埋怨道:“爹,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沈大人真让那贼人……”她伸手,狠狠抹了一下自己的脖颈。
“还是急性子,医者最忌讳的就是你这般急躁。”陈义生责了她一眼,又捻须道,“可是来得有些晚,我怕解了毒,他的身子也会不如从前。”
陈月下一摊手,重新卧回竹塌上:“那咱就管不着了,他这是后果自负。”
二人正说着,门外掀起一阵水花声,紧接着便是三个粗布褐衣的男子踏进门槛,手中的骨伞旋即收起,抖落下一片雨滴。
月下警惕地看过去,总觉来者不善。
其中一藏蓝衣男子倒也不废话,跌着脸色扫视一圈药堂,便直截了当地问道:“哪个是陈大夫?”
月下咳了一声,揶揄道:“你看看,哪个像?”这男子真不懂规矩,晓不得又是哪家商贾或是官家的家仆,进门便如此嚣张无礼,她心下腹诽。
藏蓝衣男子瞪她一眼,显然不悦。一旁的陈义生怕无事生非,放下哥窑瓷杯,淡然回道:“我是。”
“我家大人找你。”
“你家大人是哪位?”陈义生反问。
那男子眉尖一扬,甚是倨傲:“江彬大人!”
月下几乎要跳起来,嚷道:“谁?!”
陈义生按住她的肩膀,依旧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只道:“不知江大人找我,所谓何时?”
“你去了便知。”
料得他们也不会知道是去作甚,月下腹诽道,不过是家奴,能遣他出来寻人就已经算是恩赐了。
陈义生显然也琢磨不到,江彬怎的突然要找他,绝不会是为沈淮景的事。他朝月下瞥了一眼,接着吩咐:“月儿,你去把药给沈大人送去,按着我的方子先煎一副给他喂下去,切记路上莫要贪玩。”
“爹,哥哥去不行吗……”这下雨的鬼天气,处处潮湿,她才懒得动弹。
陈义生却不容她置疑:“哪里这么多事情,让你兄长留下来看着药堂。”
见他不松口,月下又可怜兮兮地望向陈大壮,眼底流露出求助神色。陈大壮则无可奈何地耸肩,表示爹爹的命令,他也没有法子。
她去便她去吧,月下不悦意地吐了吐舌头。
“陈大夫,请吧。”藏蓝衣男子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陈义生意味深长地回眸,也不知是看陈大壮还是月下,然而他最终也没有多言语,撑起油纸伞,径直跟着那三名家仆出了门。
“过来,我给你说说方子。”陈大壮见她仍在发呆,不由得叹气,伸手唤她,“煎药的时候,七叶莲三钱,仙白草两钱,我都已经给你包好了。”
“嗯,知道知道。”月下草草敷衍,低头思量一下,迟疑道,“都是解蛇毒的?”
“是。”他点头,又拿出个润如玉的瓷瓶,“里面的药丸,服两粒。”
月下颇好学地发问:“作甚的?”
“去热。”陈大壮一并给她收拾好,再次嘱咐,“不要贪玩,你自己也说了,官家人咱们怠慢不起。”
月下一把抓过药包上的系带,小鸡啄米似的点头:“我知道。”她拿起门口的竹青骨伞,闷闷撑开,看也没看陈大壮一眼,便急匆匆地朝门外的雨幕冲去。
像他们这种平民百姓配不得坐软轿,月下只能不辞辛苦地踮脚提着衣摆,尽量避开一路上的坑坑洼洼,生怕泥点子溅到自己这身姜黄色褶裙上。她倒不是说真的爱惜小心,反而是因为要去枢密使大人的府上,怎么着也不能让自己万分狼狈地出现在人家面前。
自己丢人也就罢了,可是爹爹的脸,她可丢不起。
一路万分艰辛,她终于来到沈府门前。眼角一抬,却见他家门前倒是挺朴实,同上官府相比,甚至还次些。
月下两三步上了台阶,站在屋檐下,这才能喘上口气。她一手将药包揽在怀中,一手抖了抖伞上的水珠,末了,才收伞准备敲门。
回头一瞧,那朱红漆楠木门扇,竟是虚掩着的。
山河月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重生之俏夫人当道
- 简介:前世,庶妹、姨娘与心爱之人谋划的一场大戏,污她清白,夺她性命。看着最爱之人与她的庶妹情意绵绵,是何等的崩溃;被挑断手筋、脚筋扔在茫茫雪原之上生生冻死,是何等凄惨。老天垂怜让她重活一世,手持寒星玉令,统领星涯阁,且看她如何复仇! 这一世,她本不该再轻信任何人,他的爱却让她步步沦陷,再逃不出他的怀抱。四目相对,她信了,她信他许下的一生一世只你一人。 她是夏国的绝色王妃,她是青葛部落的尊贵郡主!无论何时何地,她的身后永远都有一个他。 (欢迎加入晨晨小窝,群号码:495079813欢迎亲们进群扯扯)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80.8万字6年前
- 相思赋予谁?
- 简介:那年京城的繁华相遇……这一世,我没能保全你……下一世我定护你周全。
- 1.1万字6年前
- 江河映日月
- 简介:更新随缘文是原创,禁止抄袭,overQQ群:947782633
- 3.9万字6年前
- 女尊:玉颜倾城
- 简介:刚刚穿越到女尊国就被“上”了?耻辱!天大的耻辱!宝宝表示十分不满!从此采遍天下野花,逍遥欢快却惹了一屁股情债!“女人,你占了我便宜还敢不娶我?”——夜雨“玉颜,小雨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东方雨“喂!我本来不喜欢你的,要不是因为哥哥们。”——夏芷雨“说好的两个条件,一,再给我一个条件;二,你爱我;三,你娶我;四,你要我”——洛潇“童姐姐,你好吃吗?我想吃你!”——顾倾城“不可否认,我好像真的爱上你了,猫咪~”——冷逸尘“玉颜,我带你回家。。”——雪御天“哈哈,美男们!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把你们收下吧!”——童玉颜无耻的笑到爱这个文的宝贝记得打赏哦~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收藏~希望宝宝们可以分享一下文~在评论里给予小小的鼓励哦~最爱你们了记得分享收藏哦~无特殊原因绝不弃坑~欢脱甜宠文,微微虐一点,若出现玛丽苏,中二病等情况,勿喷。本文原创禁止私自转载,否则后果自负!
- 10.4万字5年前
- 清宫记:陆皇贵妃传
- 简介:前有李氏恶虎拦路,后有年氏步步紧逼,还有福晋四处放火,想要安安逸逸的过日子,简直是难如登天。论想要杀出重围,安稳度日,怎么破?❤️一三五更一章❤️——❤️节日加更❤️——❤️花花加更效应开启——❤️
- 6.2万字5年前
- 师尊无尊
- 简介:嗯…女徒弟和师尊的故事,不是耽,原创,名字封面都是外面找的如果撞了麻烦告知,这个文主要讲的是女主比较强,如果不喜欢请绕道,比较无厘头,没什么文采,自己开心就好,也希望你们喜欢,原创,禁止转载二改
- 5.5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