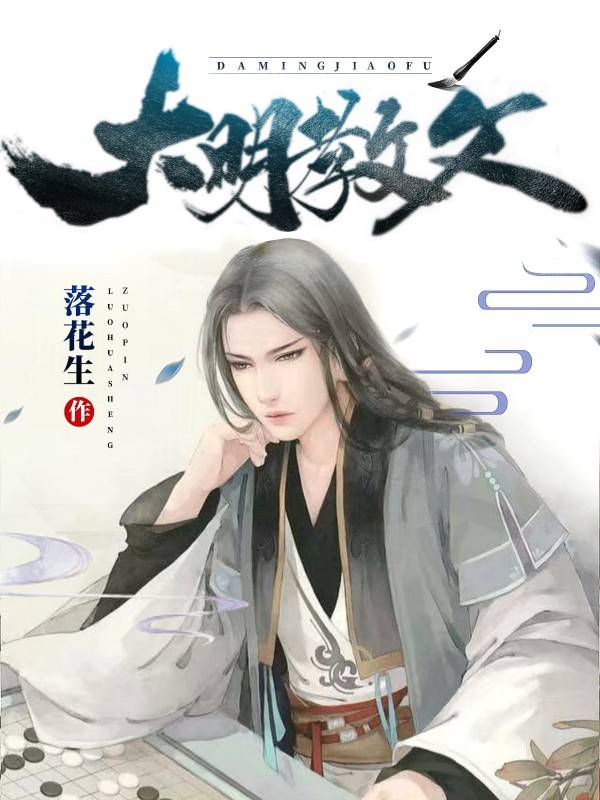第140章 传旨天使
钟敬是一个老成的小官,早已经修炼得古井不波,可在遇到这个朱姓骗子之后,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发了癫狂病,不单单一惊一乍,还轻易喜怒。
按说这朱姓骗子在睦州再怎么大捷,也不过是分润一些功劳给他,多赏他一些钱财罢了。升他钟敬的官?不可能的!朝廷给朱姓骗子的所谓“便宜从事”特权,也默认仅仅限于赏赐文官中不入流的底层小官小吏,或者临战有功的低级武官。钟敬已经是从七品下之宣奉郞,是文官,朝廷绝不愿意看到朱汉旌封赏文官。若是朱汉旌要封赏文官,他钟敬必然要出言制止,明白告诫朱汉旌,文官只能由朝廷来封赏。
那他还为朱汉旌高兴什么?
钟敬冷静坐下来,心中苦苦思索:我究竟为了什么?
片刻之后,钟敬突然也想起自己入仕之初,也曾经踌躇满志,发愿要为社稷立下不世之功。多年选海沉沦,磨砺了棱角,冷却了热血,曾经风度翩翩的青年士子成为老气横秋的底层小官,可就是在这朱姓骗子到来之后,钟敬内心被他温暖起来,又随着他收复杭州而热起来。今天,钟敬心中曾经的抱负都被这场大捷点燃起来:我,钟敬,不是那个风尘俗吏,我也是助力天选之人补天裂的名臣!
钟敬想的心潮澎湃,胸中所有才学就被激荡出来,一气呵成,写下一篇五百字的报捷奏章。
钟敬写完奏章,自己打着扇子,将墨迹扇干,也审视了一遍,合上奏章,收入一个檀木盒子中,再将外面等候的小吏唤进来,吩咐道:“速速送往潇洒先生处,请先生润色。”
小吏应了一声,捧了木盒,躬身退下,就要走。
钟敬又喊住他:“沿途尽管一路大叫:王子在睦州城外大捷,击破乱军一万人!”
那小吏是杭州商家拨过来补充的管事出身,家在本地,也受过乱军祸害。听闻上官说前线睦州大捷,喜得眉开眼笑,捧金凤凰也似的捧着木盒子,一路喊着出去了。
之后,就是钟敬召集各位僚属商议大捷之后,如何快速公布消息。
听闻大捷,僚属们人人都是喜形颜色。在场众人已然将自己利益与王子捆绑在一起,王子取胜,自己便多获利。特别是王子战果越大,推进越快,收复失地越多,未来朝廷犒赏越惊人。
朱汉旌有言在先,为政要正大光明,不让胥吏们有钻营漏风的缝隙。那么钟敬就放手让说话人、《杭州日日报》的听记们来衙门听记捷报,再传播出去。
一个时辰之后,消息通过街头手写告示、说话人等方式传遍全城。市民各个阶层富人人欣喜。在上次杭州之乱中,士绅阶层遭到血洗,在城内的官员多数被杀,胥吏损失惨重,满门遭到屠戮的不知道有多少!至于普通市民,也有被裹挟参加,也有被杀戮者,即使侥幸全家无恙,对这场祸乱也是心有余悸。故此,全城市民听闻睦州前线捷报,人人欢喜。还有人拿出元宵节舍不得用完的烟花,在大白日里放了起来。
一个时辰之后,潇洒先生的回信也到了州衙。信上只有三个字:写得好。钟敬当即令书吏誉写清楚,确认该避讳的字都避讳了,全文无错字,才正式以朱汉旌的个人名义上报朝廷。
钟敬在奏章上署名“朱旗”时候,不禁面露苦笑:国朝办事拖拉,如今天使未来,圣旨未到,仅仅依靠王黼私下的通知书札,朱旗朱汉旌还只能以个人名义书写奏章。
钟敬掷笔哀叹道:“国事纷乱若此!谁堪挽此天倾?天公,天公,为何不早降天使?”
早前王黼书札发出之后,朝廷也拟好诏书,接下来就要选派传旨天使。
当内侍省押班张承恩点名小黄门李昂为传旨天使时,小黄门李昂乐得几乎要翻过去:传旨,特别是传封赏恩旨意,一定会有大笔的好处费。不过,很快李昂就隐隐有些不安:这么好的事,为何指派要给我?
李昂九岁时因为家贫被阉割入宫,在宫中倒也伶俐,可内宦谁不伶俐讨好?李昂也求过内侍高班多次,高班只说有好处就会记得他。不过他孝敬高班的礼物微薄,连他自己都不指望有传旨这样的好事能派出来。
果然,前来派事的张高班很关切地说:“此番去杭州传旨,沿途不靖,须得小心……”
小黄门李昂的脑子里嗡地一声,后面的话就听得不真切了!果然不是好事!听说杭州还被方腊贼兵攻占过,全城烧杀劫掠,官员胥吏都被杀死,依靠一个叫作朱汉旌的番邦王子才夺回来,去这种险地传旨,能回来吗?江南之乱,可不止杭州一处。宫中早有传闻,说江南白莲教起事,到处刺杀官吏,连那个万里蹈海骑鲸来归的朱汉旌都被刺杀未遂!咱家作为传旨钦差,一路穿州过府几千里地,可不知道在哪里就被一箭射死了?
小黄门李昂嘴一瘪,带着哭腔小心翼翼问道:“禀高班,可否换人去?”
张高班把眼睛一瞪,恶狠狠地说:“你求过咱家多少次,说要有好事须得派你去。如今有了好事,你不去,是不是要等有孬事派你去?”
于是小黄门李昂就被哄着被撵着出了皇城。随行的只有两个更加倒霉的没有品秩的阉人。
丹朱一般的晚霞堆满西方的天空。如血夕阳下,三个小内宦都是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仿佛是去报丧,而不是去传旨封赏。
马车走着走着,小黄门李昂突然兴奋起来,对着那两个手下开导道:“莫要丧气,你等想想,这一去若是平安无事,总有几十贯入腰!回来时一路采买些江南货,也让他们眼馋!”
李昂想了想,又说:“江南富庶。听人说,杭州当地时鲜果蔬要好过汴梁许多,当地还有诸多海货,入口鲜美,是汴梁子无福享用的。这一去,咱家以‘道路不靖’为名,一路慢慢走,慢慢看,走一路,玩一路,好不容易出得一次京城,须得享用些!”
两个手下,一个充当车把式驾车,一个坐在车把式身边,听得都有些心动。赶车的小内宦冯良突然有些领悟,问道:“那俺们出了京城,就放慢些?”
李昂笑道:“那可不成的。京郊左近都太平,走得太慢,落人把柄。过了大江,再慢慢走吧!”
三名小宦不疾不徐地赶着马车到运河码头,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在码头登船,沿着汴河往东南航行。船出码头,过陈留、应天府、宿州,进入洪泽湖,过泗州,进入淮水,向东过淮阴,再向南转入里运河,过楚州、扬州,到达瓜洲。运河浪小,行船平稳舒适,时值冬季,多数时候刮西北风,官船挂帆,呼呼地顺风行驶,既稳又快。
李昂负手挺胸站在船头,志满意得:这一路,真是太平顺畅!早前心中那点不安,已经被北风吹散,了无踪迹。
临近瓜洲渡,不知道怎么的,一路飒爽的北风突然就停了。在纤夫一路呼号中,官船慢慢爬行到瓜洲渡口。在船上郁闷好久的三个小内宦上岸休息,住进驿站之后,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江南所有大江船,突然都没有了!
李昂心中那点不安突然像火一样腾腾地燃烧起来,焦灼得他坐立不安。整整一天,他都在驿站中纠结:出事了?要不要南下?
李昂想要多付些钱文,令船夫南渡。
船夫嗤笑道:“隆冬时节,江里风大浪高,江面上说起风便起风,吹翻江船都不少见。更何况这内河游舫一样的官船。想要南渡,须得换大江船!无论给多少钱文,这官船就是不能南渡!”
李昂张口结舌道:“无论如何,都得南渡,咱家身上背负诏书,江南诸州县等得望眼欲穿呢!”
船夫只是摆手:“俺一介船夫,不晓得什么军国大事。上官说了,俺也听不懂。俺只晓得此等官船若是硬要过江,便叫江龙王收了去!”
话说到如此,船夫拱了拱手便走,头也不回,似乎觉得这朝廷内宦是尊瘟神一般。
空荡荡冷清清的驿站庭院中,李昂跌足长叹:“这可如何是好?咱家难不成要在此处长留?”
驿卒在一旁听了,讪笑道:“怕是要长留了。”
李昂瘦削的身子抖了一个激灵,忙不迭问道:“却是为何?”
那个矮小猥琐的驿卒看了看左右,耷拉下眼睛,欲言又止。李昂忙摆手说道:“左右都是咱家心腹,最是信得过,但说无妨。”
那驿卒还是低眉不语。李昂身边的小内宦冯良经常赶车出入,对于驿卒贪钱多少有些了解,赶紧从怀中掏出一小串铜钱,塞在驿卒手里。李昂急不可耐地追问道:“却是为何?”
驿卒微微拱手,故作神秘说道:“俺听得一些传言,也不真切,中贵人听听便过了……码头上传说有白莲教中妖人,将这渡口上下上百条大江船都裹挟了,驶去富春江投奔方腊乱贼!”
李昂吃惊地长大了嘴巴:“此地真有白莲教妖人?”
李昂突然背后一寒,打了一个冷战,和两个手下都是神色慌乱,不安地左右看看,仿佛这空荡荡冷清清的驿站庭院中就会突然冒出来白莲妖人一般。
那个驿卒笑得见牙不见眼:“中贵人却是不知,这驿站左近,白莲教妖人是不来的。中贵人且宽怀,在此多住十几日,等待上游来船,方可过渡。”
李昂奇怪问道:“为何驿站左近没有白莲教妖人?莫非尔等勾结白莲教中人?”说道这里,他心头一凛,警惕地后退一步,拉开了距离,手中暗暗蓄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他若是白莲教妖人,咱家就拼死一搏!
那个矮小猥琐的驿卒笑得脸上皱纹更深了,说道:“中贵人有所不知。这驿站名义上吃的是朝廷饭,可那点钱养不活俺们。俺们自然要有些营生,接待些江湖客。来往的朋友多,自然会有人照应着,那白莲教也是江湖中人,看在江湖豪杰体面上,不敢来滋扰。中贵人尽管在此安居,驿站之内,万安的!”
听到这里,李昂和两个手下面面相觑。他们都是北地人,莫说要游泳,就是风浪大一些,自己都要晕得吐了。要是雇佣小船过江……嗯,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李昂就此在驿站住下来,连驿站大门都不敢出。每日只敢蜗居在驿站中,偶尔到庭院里面走一走,就算是疏散了。这一住,原本以为只要等三五天,上游就会有来船。一旬之后,听那个驿卒说,上游的船也投奔方腊乱贼去了!这上下游数百里江面上,是稍微大些的江船,都被方腊裹挟走了!
李昂气急败坏地指着驿卒说道:“休要信口胡言!那上下游少说有几百条江船,哪里能都投奔了方贼?”
驿卒被手指着鼻子,唾沫星儿溅到了脸上,依然是一脸猥琐笑容:“中贵人却是不知。这白莲教妖人,确实有些蛊惑人心的手段。听说,也是听说,做不得数的……码头上传言:那方贼犒赏颇大,之前有船家去投奔,来一条小船;便有一个都头当;来一条大船,便有大都头当;来十条船,便有一个将军当!船家争着去投奔呢!”
李昂张口结舌,久久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这方贼果然会鼓动人心,什么都头大都头将军的,还不是乱军官衔?当不得真的,怎生得这些愚民偏偏就信了?
李昂纳闷了好一阵子,才小心翼翼问道:“若是雇佣一条小些的江船呢?只要能够过江便成!”
听李昂说要雇佣小船过江,冯良等两个手下都脸色青白,连连摆手哀求道:“使不得!是不得!这几日风大,如何能过江?”
那个驿卒还是脸上挂着猥琐笑容,对着冯良等两个小内宦拱手道:“两位中贵人明白!这冬日风大,小船经不得风浪,要翻的!”
李昂还不死心,伸长脖子追问道:“那不大不小的江船,总该有吧?”
驿卒把头要得拨浪鼓也似的,说道:“俺早说过了,方贼蛊惑人心,但凡去投奔的,都有封赏,本来还有人将信将疑,不敢去投奔。熟料回来之人,穿着锦衣玉带,见人就撒钱文,大坛子喝酒,炫耀得让人眼红!就在这一两日之前,稍微大一些的江船,哪怕不曾冬日出海的,都奔向方贼去了!”
李昂还是不死心,说道:“那小一些的江船,如何经得起风浪,如何能投奔方贼?不怕中途翻沉了?”
驿卒比划了一下,说道:“那大江船系带着小江船,如母鸭子带雏一般,拖走了!过日子,俺们这处渡口,怕是连澡盆子都被拖走了!”
李昂犹自不死心,还问道:“那就不能新造船么?”
驿卒嗤笑道:“造船?新造一条船,便是要一年,哪怕是急造应急,也得半年。如今江南纷乱,人人自顾不暇,哪里会新造船?罢了,罢了,要是方贼打过来,某也要逃走了!”
驿卒说完,自顾自就走了。
李昂呆着一张脸,久立在庭院中,不知道如何是好。
两个手下在他身后,轻轻地问:“黄门,该回转了!南北交通断绝,也是大事,也该回报禁中才是!”
李昂犹豫道:“诏书未传,擅自回返,也是大罪啊。不如在此多观望两日?你们两个,且去码头打探些消息。快去,快去!”
那两个手下是没有品秩的小内宦,不得已听了黄门李昂的驱使,战战兢兢去了码头。
李昂就在驿站庭院里踱步,转着圈子,一圈两圈无数圈……
过晌午还不见两个手下回返,李昂心中有些不安,到了傍晚,还不见两个手下,李昂心中大惊,就去寻找驿卒说话。不料,寻遍了整个驿站,原来偌大的驿站,三四个驿卒都不见了踪影,连厨子等下人都平白消失了。李昂心知不好,立即收拾起行装,就要出门,走到大门口,远远听到外面人声鼎沸,又有脚步杂沓,显然是有一群人奔这里而来。
李昂惊呼:“有反贼!”返回那驿站中,急急寻得一张竹梯,手脚并用爬上去。在墙头,还不忘记把竹梯先翻过,刚刚想要爬梯子而下,就听见那庭院里面被闯入人来,有人大喊:“都快些!抓了那贼,献与圣公!”
李昂大惊,慌乱中从梯子上顺溜下去,还好没有摔伤。他又是一个谨慎的性子,还不忘记将梯子翻过,放躺在地上,这才背起行囊,飞也似地跑了!
宋时儿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三国之极品董卓
- 简介:平边地、讨叛逆。霸京师、拥新帝。乱宫闱、焚金阙。掘皇陵、立新都。骑貂蝉、筑郿坞。魂归天、止凤仪。没有无敌的勇武,没有绝世的智谋,没有凛然的正气,没有超卓的才学,却偏偏成为了汉末一朵奇葩,一生功过,尽在此言之中,而这一切,在来自后世的董林穿越成为董卓之后,又将变换如何?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25.7万字6年前
- 巨匪
- 简介:新书重回三国,更精彩内容,即将登陆,希望继续关注四关的新书《三国之刺客帝国》!!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18.4万字5年前
- 制霸水浒之我是天魁星
- 简介:你是否认为水浒里的宋江太窝囊?主人公穿越至水浒代替宋江,不再招安。天罡地煞一百单八将成为了济世救民的大英雄,一起来不一样的水浒世界吧!
- 1.4万字4年前
- 大明教父
- 理学工学双料博士陈恪穿越到明朝崇祯年间,成为一名寒门士子。由贩私盐白手起家,纵横在黑白两道,一步一步成为大明的教父。
- 1.9万字4年前
- 长安西行七千里
- 距离长安七千里的地方,有座城池叫龟兹,有个地区叫安西都护府,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 7.8万字4年前
- 我要做列强
- 刘般和网管小妹在网吧触电穿越时空来到了一个与地球相似的世界,这里也有列强在用坚船利炮征服着一个有一个落后的国家,也在掠夺着无数本该不属于他们的资源财富。看刘般如何与网管小妹如何利用系统帮助,使一个东方大帝国变成列强们的噩梦。其实就是猪脚利用系统大大的帮助与网管小妹笑傲新世界的过程。
- 4.5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