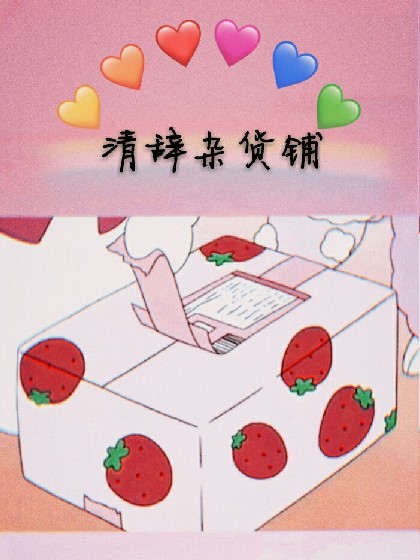第十章 入湘
初冬,长沙城东大宅尾巷。
男人沿着墙根靠着坐下,手里抱着那柄还沾着血的钢刀。落寞的眼神孤寂的看着苍老破败的巷子口,嘴唇上尽是干裂的沟堑,满是胡渣的脸上,尽是大西北瑟瑟寒风留下的印记,瞧不出年岁的苍老。不清楚这是哪里,也不知道往后还能做什么。
没了刀头的刀客,就如丧家之犬一般破落,身上的棉衣已有几处破败,露出里面的棉絮。虽说是暗黑的袍子,但是沾了血气,也是看上去明显的腌臜。紧了紧领口,蜷缩起身子抹了一把脸,刀队没了,兄弟没了,主子没了,怀里的这把刀就是自己唯一认识的,脸颊靠着刀柄咽了口水。饿……
没有目的不知道去哪里,只是冲着鬼子来的方向一路杀回去,杀到什么时候自己也撑不住了,就去找兄弟们。西北客走异乡,不指望什么叶落归根,有刀头有活计,有口饭吃,就成。没头没脑的就进了这个城,破布裹了刀口,见鬼子刀口才见红。寒刀饮血煞气重,夜里门口过都能惊着八字弱的伢子。
古城僻静老街,大宅子后院偏门角落里,这一靠下便卸了精神头,几日未歇的疲累让身上的筋骨都在疼。吸吸鼻子顺着墙沿卷起身子躺下,如着乱世之中的乞子一般。鼻尖与地面一指的距离,细末的土气吸进鼻腔,黄土地的味道,稍有缓释的喘口气,闭上眼,累……
后半夜宅院后门咯吱一声开启,眼瞅着管家似的男子,把一打扮妖艳的,不知是哪家楼子的妓子半哄出门外。随手还丢出了一个小包袱,轰然关门,不留一点情面。妓子也是无奈,骂骂咧咧又能如何,捡起小包袱拍拍,转身便见到墙角蜷缩着的黑影。
“哎呀妈呀,臭要饭的,吓死姑奶奶了。”自己拍拍心口嫌弃的掩鼻,如今乱世哪里不见路边饿死病死的乞丐,以为是死人。
静了静才听见黑影发出的呼噜声,这才松了口气,一记白眼丢过去,从小包袱里拿出个馒头塞到黑影怀里。“不是死人就赏你口吃的,姑奶奶我今天生意也不好。”捻起手帕擦擦手,瞥一眼,扭着腰肢便回了楼子。
男人睡了一会儿,忽然怀中多了个馒头,饥饿感胜过了奇怪,他一口吃掉,细细品尝着馒头在口中留下的一丝丝香味,便有了一丝力气,抬头,看向熙熙攘攘的各色人群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风景。
这条街便是自己的主儿。
解九回长沙的时间预计慢了三个月,一路渡洋乘船,虽坐的头等舱,但也不免这世道荒唐,大概在民国二十三年中旬,一辆叫顺天轮的轮船被土匪劫了,绑了好几个外企的外国人,英国日本法国媒体要求还人,最后劝降了绑票的土匪才得以收场。
这只是特例,不见得每个歹人都有顺从之心。但也不见得绑票的那些匪徒是否像孙美瑶那样“变相招安”。
货轮今早靠了岸。解九收拾好随身携带的东西,便走下楼梯。
他身着高领衬衣,手上拎着皮箱,步伐稳健下了甲板,那几辆像黑皮箱子的皮普早已恭候多时。
再回到长沙,倒显得有些陌生了。解九只记得两个朦胧的场景,连同这样的朦胧都是几十年前了。
甲午海战冬秋之交,左宝贵战死之后,解九的几个本家忧心忡忡聊着国事,那时变法的苗头还没出来。但凡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被这场战争深深的刺激到了。谁愿意又承认自己国家的的弱小呢?而事实就这样惨痛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解老爷有远见,那时大多还是以科举为重的,但倘不能在技术上改革,背再好的文章又怎么应对得了洋人的火枪?便送他独自一人去往英国留学。
送别他的那十年前的那个下午,解九记得很清楚,解老爷与父亲一同望着,解老爷,身材比较佝偻的老头子跟他挥手道别。残阳似火把湘江渲染一一片血色。一面烈火,一面汹汹。五年以后,另一番血色笼杂着血与肉则呈现出另一种骇人的场景。
解九望向车窗旁边轰隆作响的斗车,便又拉上了车窗,长沙经过辛亥革命之后,城墙的作用微乎其微,于是决定拆除城墙上挖下来的土,掩盖便河。此时之便河已逐段淤塞,潺潺流水已成为臭水沟,且成为长沙城发展之大障碍。
拆城开始,沿城墙自西向东铺轻便轨,用斗车运送自城墙上拆下之废砖泥土,填于便河中。当时日夜有斗车来往轰隆不停,并逐段向前延伸,城墙逐渐无有,便河亦渐平夷,成为现在环城马路。
穷苦人民在沿江一带搭起了无数间棚屋栖身,这便是当时长沙有名的贫民窟——沿江棚户,而东、北向所谓环城马路,除左文襄祠,即现在的工人文化宫,铺了一条仅可驶一辆汽车的柏油路。他所行驶的这条路,多数是军阀的专用通道。而解九一路上畅通无阻。
车开了一会儿,便到了解家的外宅。解家老宅,前门临闹市,偏门通街巷,是长沙城内几所年代久远的老宅之一。兴建时按照古时的制式,讲究的是院落纵深,前堂不闻买卖声,后寝龃龉声不闻。合当是住着一堂四世,热火朝天的过着兴旺日子。可是只有住过那里的人才知道,那所宅子的空荡幽寂,穿梭在回廊与别院之间,都感觉自己被这所房子里的一草一木监视着,无论在每个角落,你所做的一切都会被人知道。
他拿着提包下了车,正推开门,一个人迎面走了过来。差点撞倒自己。那人眉宇间带着某种锋利,但却又不像是一个桀骜之人的飞扬跋扈,很内敛的锋芒。
“你是?”
“你是?”
那人揣摩了自己许久,僵了一会儿,缓缓的猜出他的身份来,嘴角也微微的翘起,“哦,我想你是解家少爷,鄙人张启山,前来拜访尊祖,此次前来说些生意的事情,改日来访。改日再与你喝上几杯酒。”
张启山拱手作了个揖。
解九回礼。
他见张启山乘着一辆皮普远去。快步向中庭走去。
在前面正中央摆了一个水台,顶上的屋檐将整间房子连接起来呈一个方形。屋顶都是斜坡形式,坡面斜向院内,下雨时节,雨水自屋檐滴落,在地面形成汇流环绕的格局,四方之财如同天上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入院墙府内。既是藏蓄之所,也是财禄象征,因此被称为“四水归堂”。现代建筑学也有过涉及。
最旧的宅子大概是在1887年划分到解家名下的,宅子原先是一个提督住着,后面被那个倒霉的提督被新军斫掉了脑袋,当时解家因帮助新军起义有功,新军的统领举荐下便让解家当时一个小小的当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长沙城政商界两方忌惮的势力。
老人身着黑棕的棉衣,双耳架着黑铜查色的玳瑁眼镜腿。眼镜底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颔肌下面一把山羊胡子。带着深用来搀扶的拐杖放在另一边的椅子缝隙里,右手擎着紫檀木的金少山(烟枪),在左手膝盖下面放着银质的烟盘,
老人正要吸,解九立刻毛了,直接把脏话飚了出来:“你妈妈个嬲!福寿膏是他妈的好东西吗?!有多少人抽这玩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抽的犹如行尸走肉。”
解老爷还是稳稳的点了抽着,“连阔,你回来了?”
“嗯,回来了。”
解九见他对自己置若罔闻,愣神了一会儿,走了过去。
“我这个老头早就快将行就木,还在乎少吸点多吸点的区别?”
“可是…鸦片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了,刚才我在宅子外面碰到一个叫张启山的。他找您什么事?”
“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他向我们买了一批军火。说是货物押送要用,毕竟时局总不是那么太平。统领叫我们商界几个大人发粮救急流民,恐怕也是杯水车薪,这不,前几个月又闹。”解老爷又缓缓吸了一口,顿了一下,"城东道台张府你应该也知道,张启山也不是生人,他的外公算是我一个故人。大前年驾鹤西去了,加之他动之以情,我实在没有什么理由拒绝。"
军火交易也只是解家另一门副生意,一般这种生意比较少,而一出手基本上都是大单,一般只有老客户才敢轻易对交。毕竟这门生意受到一些限制。对于解家来说福祸相倚,不敢锋芒太过于显露。
解九觉得解老爷所言即是,当然不只走私军火,解家还有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都共同藏匿于这座阴森的房子每一寸。
“张启山这人不简单。”解老爷没有继续抽下去,很反常的没有抽完。
“何以见得?”
“他大前年来了长沙,年景才过一半,他一个外乡人就成了统领的秘书官,你不觉得他发展才顺坦了吗?"
“您的意思是有人在帮他?”
解九不难猜出张启山幕后的帮手,因为如果不是那个人,光是长沙都不可能有一寸三亩地,更不用说当上什么要员身边的人,可是为什么他要帮他呢?
“所以我说他不简单,我听探子又说,张启山和二月红恐怕这月底有一次夹喇嘛,他在我们这购的那些枪或许就是为了这个准备。”
“霍家那边会不会出面?”
解九虽不知他们下斗淘沙具体的的地方,不过恐怕是西郊那边,而西郊那边的矿山是霍家的地盘。
“等着马盘的消息,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会提醒我们的。”
“不过,那些是不重要的,眼下北京盘囗私下蠢蠢欲动,解家一个老字辈被人毒害,宅子里五纵六横,凶手还尚不知道是谁,连阔,需要你出面一趟了。”解老爷不由自主叹了一口气,“我已经老了。”
解九沉默的看着沉默的老人。
“我以前是赞成康梁变法的,可是呢,见过张勋复辟,见过袁世凯称帝,又见过二次革命,还见过东北,北平天津的沦陷,见来见去……”老人指着自己的脑袋,又把手慢慢滑到心窝处,“不是脑子的坏东西,是心不齐啊,中国人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小日本人,那是胡话啊。心不齐啊。”
“我看过***下令对于共产党人格杀勿论的字报,报纸上不能出现共产两字,否则报社的编辑也是脑门上刻了个“**”两字,就足以去枪毙了。这其中又有多少无辜的?”“以前听过叫贺龙的无名小卒好像是杀了几个当兵的,谁能料想到全国都在通缉他。”
“可谓时势造英雄。”
“咱们商贾之家,照理来说不应该对国事评价一通,可我真的过意不去,我们毕竟是去过外面见识过的,国家乱成这样,不是你我的责任,是大家的责任,蒋先生还有“攘内不必先安外”一番言论,”我还真不见得共产党有什么不好……”
老人又连连叹气,扶着拐杖,起身,望向四方的天空,又即刻闷雷滚滚,转身对解九说:“要变天了。”
九门后续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穿越我是江厌离——啥子情况?
- 简介:金凌:阿离,你跟我娘亲的字一样,会不会跟娘一样啊!江厌离:不会啊,我有你守护着我。
- 5.7万字5年前
- 查理九世之再次出发
- 简介:【开学时不定期更新】心脏又是一阵剧痛。又过去一年。我的时间……又少了啊……我只是一个努力想活下去的人……为何苍天对我如此不公?DODO冒险队……我的伙伴……聪明如你们,也应该什么也没发现吧?还有翼之冒险队……叶白痴,熙雯,华元,林煊……新一代的冒险队啊……可惜,我再也没时间看到他们成长了……【欢迎各位加群鸭!群号:609164995】
- 5.7万字5年前
- 范丞丞:向来缘浅,奈何情深
- 简介:不喜误喷.这里诚意高冷学霸校草X伪高冷学霸校花吴怼怼VS范毒舌某男某女大型真香现场皇城:到头来还是你当然,我可等了你五年注意⚠️:请勿上升真人,纯属虚构【陌殇文社】
- 4.5万字5年前
- 清辞杂货铺
- 简介:清辞杂货铺,不定期更背景图,头像,壁纸,语录,书摘,句愿喜
- 1.0万字5年前
- 斗罗大陆之刺客恋
- 暂无介绍哦~
- 4.0万字5年前
- EXO之女尊王者
- 简介:本文女尊文,男人生孩子,不喜勿入,不喜勿喷。男主EXO一位女强人职业白领,英年早逝,睁开双眼,竟然穿越到了古代。嗯?女尊?嗯?身份还挺厉害?在现代桃花运就很好的女主到了古代依旧是,桃花朵朵开
- 3.4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