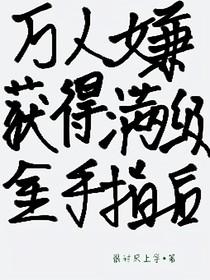玄学
1、正始玄学:名教本于自然
有无之争,是魏晋玄学的第一大问题。那么名教与自然则是他们哲学的落脚点所在。所谓本体论思想,真正去论证的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来自于老子,指的是自然而然,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以排斥人为干预为主要特征。而名教,则是儒家认为,名分。不同的名分有不同的责任和权利,人们要守名分,把合乎礼节的行为,称之为合名教,否则为越名教。
王弼的哲学,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在社会中,就是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故而称之为崇本息末。
崇本,就是任自然,即遵循事物的自身规律而不违背。如果说,被浮华、情欲所迷惑,把真正本性隐藏起来,借助于虚假的纲常名教,就会陷于“末”,而远离其本。
所以,崇本,则要息末,即止息虚伪名教之末。
王弼说:
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玄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在乎不尚,不在善听。故不攻其為也,使其无心於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於欲也。谋之於未兆,為之於未始,如斯而已矣。
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存诚、去欲、才能让社会真正地息淫、绝盗。只有崇本,才能息末。
但是,他所说的任自然,并不是放荡不羁,而是说仁义礼智,不是外在的虚伪规范,而是真正的自然流露。
同时,他又主张崇本举末。举末和息末从表面上来看,是完全相反的概念。
但是,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
因为,发自真情流露的仁义,不是刻意作为而成,而是出乎自然而成。只有崇本,才能使得仁义显现出来。如果仅仅是舍本逐末,失去了真正的自然流露,仅仅在外在上追求仁义、只会走向反面。
因此,崇本举末是互为补充,崇本即任自然,而举末的末,不是虚伪的礼教,而是发自真情的仁义流露。因此两个末字,是由于概念的不同一造成的,实际上两者所指不同。
在名教和自然的关系,就显示出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名教本于自然。
2、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
由于王弼提出崇本息末,这一点被竹林七贤所发挥。
公元前249年以后,正始玄音开始消除,因为此时司马氏政变,王弼、何晏都去世了。政治环境极其凶险,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于是,嵇康、阮籍,由于受到司马氏的迫害,对于名教产生了绝对性的批判态度。他们把正始玄学的崇本息末,向息末的极端化发展。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名教,就是冲破固有的政治观念、儒家的纲常名教的束缚,不为名利所诱惑。任自然,是顺乎人的自然欲望。
六经以抑引为主, 人性以从欲为欢。
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然欲望,只有从欲才是合乎自然。相反,儒家思想都是抑制人性,是虚伪的。因此他们批判儒家六经,比如说阮籍把礼法之士,视之为虱子。
任自然发挥到极端,就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倡导一种精神颓废,行为放荡,纵欲主义。
3、郭象:名教即自然
王弼以崇本举末来调和名教和自然的关系,而郭象以崇有的无因论思想,导向顺性之说。
郭象时期,玄学已经从老子之学,转向了庄子之学。他主张一种玄学心性论,
1、自足其性。他认为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与自身同一,与外部无关,他称之为性分,即自性,也就是事物的本质规定性。性分是自然而然,不能被人所左右。因此,对于个人来说,生来如何,便是如何,不能改变。
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终,思音抱思以至死, 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因此,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增损。称之为性各有分。
所以说,既然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么只能顺性无为。
其次,达到顺性无为,就会到达无待自由的境界。
2、足性逍遥。
他认为,人各有性分,在性分范围之内活动,照样能够达到自足为大的逍遥境界。只要能够自足其性,解放了思想,就得到了最大快乐。人要正视自己的价值,无需自傲和自卑。
3、无心顺有
现实的一切都是合乎自然的,理想社会并不在社会之外,而是应该各顺其性。不去超越自己的本分,也不去压抑自己的本性,就能做到因任而性。人人在性分内获得,就能各自安然,社会就能井然有序。
这样一来,名教的作用就自然而然实现了,这就是名教即自然。因此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只要满足了性分,那么精神就是相同的,也就获得了相同的快乐。
进而,他把名教也说成是合乎自然的东西,仁义道德也是人性所固有的。
于是,从王弼的崇本举末的名教本于自然(名教的根据在于自然),到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最终统一到郭象的名教即自然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永远停驻于那个夏天吧
- 请关注四千时谢谢喵【自留oc向】第一次在话本写东西!这是纯oc向的小说てす!一起去鬼屋探险吧!杂乱剧情注意‼️多结局注意❗️男频剧情️,女频......
- 0.7万字6个月前
- 恋与伤
- 玄幻+虐恋+权谋+命相系+一本坏人泛滥的小说。讲述了四个大陆之间的感情纠葛。长篇小说!在欺骗,利用,谎言,杀戮,绝情中渲染虐的爱恋。每一次相......
- 78.0万字5个月前
- 修罗女君,终入怀!
- 千万幽怨,已难渡万般情。最后的最后,那血发女子也成了帝上,掌管天上人间,威仪八方。而那扯下别人发带的少年同是帝上,与女子同渡万年,也将女子爱......
- 25.1万字4个月前
- 虚假的象牙塔
- “当我让他的画享誉世界时,我将取走他的生命——毕竟伟大的作品,是不可再生的,不是吗?”这是理想的象牙塔,也可以是一本充满欲望的故事书贪婪的饕......
- 0.3万字4个月前
- 清风拂过叶林间
- 四个人一起进入副本,探寻案件。案件一:拼凑娃娃案件二:泥墙母亲案件三:火锅男孩案件四:疯子父亲每一个案件都惊心动魄……“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我......
- 1.8万字3个月前
- 万人嫌获得满级金手指后
- 许念珠苦了半辈子才得知是因为被人夺走气运,且看她获得金手指后爽翻天的日常。
- 2.1万字6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