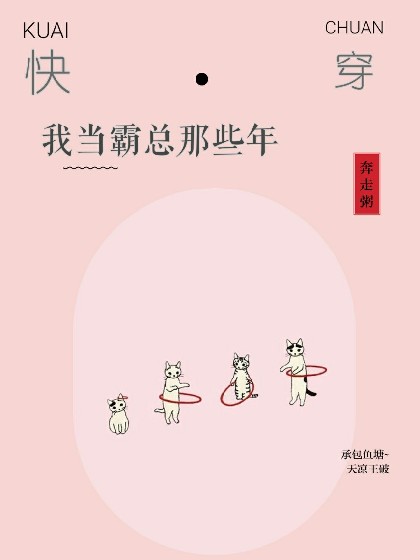第258章苦儿
明天后,她就要呆在家谁都不能见,等她三朝回门后,那时见了面也只能低着头不咸不淡地说两句,不能有半点亲昵举措。
想着小时候两人青梅竹马,光着身子滚一块都无所故忌,心里没来由的一阵酸。
唐叔见我答应去赴宴了,便唉呀一声,捶胸顿足。
我不知道他为何会有这种反应,还以为是恨我该当不断会反受其乱。
其实我在遇上小姗后,对小莲的那种情愫就已经渐渐看透了,无所谓斩不斩断,跟本就没有我对小姗的那种情愫。
待黄小毛走后,唐叔仰天长叹一口气,说:“天机如此,该来是还是要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我没听明白他说什么,他也不解释,跟四爷一个德行,两人聊了一会后就将我赶出去,说:“去去去,去喝你的喜酒去。”
被唐叔赶出来后,老黑居然蹲在门口向我挥挥抓子,这老狗越是越老越通灵性了。
“老黑,我给你带只肥鸡腿回来。”临走时对老黑说道。
老黑舔了舔舌头,滴下一行哈嘛子。
唐叔骆着背,背着双手站在义庄门口目送我远处,那感觉总有点怪,就像一只阎王爷盯着一只小鬼看。
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我身后,是不是被什么东西跟着,让唐叔如此眼神盯着。
以前没觉察唐叔的眼神如此阴森可怕,就像一只千年老鬼的那种阴森而无半点人味的眼神。
大码头对面的朝天门下的崖壁上搭满了吊脚楼、棚窝,华灯初上后,就如点点繁星。
而大码头旁的河滩陡崖上同样建了一大片吊脚楼、木棚窝。这都成了老巴渝的特色了,在别处是看不到的风景。
若是有点儿钱,都不会住这受苦,常到受河风灌吹,许多人还没到四十,就落了一身风湿病痛,有些人风湿严重的,不到五十,全身的骨头都变形了。
绝大多数住河边吊脚楼的都活不过六十。
小莲家就住在大码头旁、嘉陵江畔的吊脚楼里。
所谓吊脚楼,只有十步见方,一家五口就窝在这里面吃住拉撒。现在再次来到小莲家,发现原来的吊脚小楼已经拆了,改建成一间大棚窝。
看来是嫁女收了点礼金,住也住得好些了。
要是以前,吊脚楼地方窄,想摆几桌宴席得摆到河滩上,风一吹来就得吃沙喝风,搭了棚窝后,在里头摆几桌没问题。
进到小莲家后,正好看见四爷撸起袖子在搭出河边的阳台上炒菜,李大锤在帮忙端盘子,嘴角边上还留着点偷吃的痕迹没擦去。
四爷厨艺好,跟他相熟的,谁家有事喜要摆宴席,几乎都想请他来露两手。
“哟,小阎王来了,快里边坐。”小莲他叔树生见我进屋了,热情地迎了上来。
姑娘家出嫁,从接礼的那天起就是准新娘,要呆在房里不能出来见生人。
目光搜寻了一下,没见到小莲,到是看见她爹黄狗生扶着一个瘦色枯黄的蓝衫妇人出来,放坐在主家席正席的一张轮椅上,正好离我不远,一股子药味、尿骚味、屎臭味混合成的气味扑鼻而来,顿时让人大倒胃口。
这妇人正是小莲她娘杏花婶,五年前到镇上卖咸鱼,回来时遭到一群地痞抢劫,钱就是一家人的命根子,她不给,就被地痞给打断了十几根骨头,其中有四节脊梁骨、六根肋骨,就连盆骨就被踩裂了。
这几年要不是有四爷免费给她治病抓药,早就没药治了。但她吃喝拉撒全得要小莲去照顾。
要是一般人,早就受不了这罪,不是自己想办法解脱,就是被家里人遗弃自生自灭。
此前我去湖南时,她还有能力说几句话,再见杏花婶时,只有眼神在游戏,动动眼珠子看人,想对我说些什么,抖动着嘴皮子,似始终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只能断断续续有气不力地念叨着:河……河……河生。
她的手想抬起来,最终只能颤抖着手指。
狗生叔连忙抓着我的手,位到她面前,红着眼睛说:“河生,你杏花婶想和你说说话呢,她现在……她现在已……就倍倍她吧。”
有些话狗生叔想说,却是没勇气说出来,比如‘时日无多’。
富贵人家盼妻死,贫贱夫妻死难离。
狗生叔以前虽然一直反对我和小莲,而且对我很凶,心中是有过怨气,怪他势利。
但此时却怨念全消,四爷给杏花嫂开的那些便宜药,喝多了早就效力不大了,若不是有好人家看中了小莲,提前下了重礼,给了几支千年老参吊着命,早就走了。
有时候,活着要比死更需要十倍百倍的勇气,但这需要一个目的支撑,只要达到了,将一泄千里,油尽灯枯。
不用狗生多说什么,我抓着杏花婶的手,说:“杏花婶,我都明白,你们不必自内究,我和小莲终究没有缘份,只要她嫁好,一切都好。”
这话并没有半点自欺欺人,自打白帝城回来后,在码头上再见小莲时就已释然,可杏花婶更激动了,我又安抚了几句。
干我们这行的晦气,不是命格低贱,谁愿意干?而且三餐不稳、小命朝不保夕,就算狗生叔和杏花婶都同意,我也不会取小莲过门。
过了半个小时,所有菜都上完桌,该来的人也来了,我首先敬了狗生叔和杏花婶一杯,由衷祝愿小莲幸福美满、早生贵子。
当我说到早生贵子两字时,在座的好些人目光诡异地看向狗生叔。
而狗生叔则嗨的一声,举杯一饮而尽,像喝了一杯苦酒似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正疑惑时,李大锤将我一把位到凳子上,小声在耳边嘀咕道:“你知不知道新郎是个傻子?命根子在小时候逗狗玩时被咬掉了,没那本事!他家取小莲过去,完全是找个人贴身侍候傻子终生。”
这不是毁了小莲一生么?我听完这话后,‘唰’的一下再次站了起来,手中的酒杯重重磺在桌子中间,眼红欲裂地盯着狗生叔,片刻后指着他怒道:“你倒底有多缺钱?是嫁女还是毁女?”
狗生叔可是出了名的爆脾气,以前和小莲腻在一起玩时,没少被他追着揍。此时却一声不吭地别过脸去不敢看我,眼睛里顿时布满血丝,伤如滴血。
他没有了往日的半点脾气。
现在的气氛仿如凝固,空气稠如糨糊,每呼吸一口气都是如此艰难。
四爷轻咳一声打破僵局,对我厉声说道:“臭小子,你懂什么,坐下。”
我不懂的事情是多着,但明事曲直的分辩能力还是有的。
有些事情,违抗不了天,难道连心中一口冲动之气也不能宣发出来么?
片刻后,我便坐下来一个人喝着闷酒。
这场酒席变了味,所有人吃起来都不对味,就两口就放下块子喝酒。
就在此时,盛饭回回来的黄小毛偷偷地递了一张纸给我,然后低声道:“看窗口。”
小莲认识的字不多,都是我教她的,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愿家安稳,愿君安好。
这八他字就像一把刀子般插进我的心。
客厅的则屋是小莲和她奶奶睡的房间,房门紧锁着,窗却开了一道拳头大的缝,侧头看去,正好看见静静坐在桌边上的人儿。
鬓角带花,两边马尾。画眉粉黛,红妆花衣。
小莲穿上新的花衣裳真好看,一时间让我有些失神。如此俊俏的姑娘竟然要嫁给一个不能人事的傻子?
她就静静地坐在那儿看出来,并有半点悲伤,却也没有半点笑意。
酒是狗生叔自家烧的刀子,好喝会上头,李大锤喝高了之的就满场劝酒。
而我则自顾自己地怼着闷酒,偶尔偷偷地透过窗缝看向小莲,越看越糟心。
最后将酒倒满牛皮水袋后,就醉熏熏地离开了。
屋子里的人,十之**都酒劲冲头,晕乎乎地倒在地上呼呼大睡。
“今夜月朗星明,谁解我愁!”
我坐在河边的一处高崖是仰天长吼。
也不知是否喝晕头了,身后忽然有风袭来,我顿时打了个哆嗦,酒醒了几分。
就在此时,听闻高崖下的河滩上传来一阵嚷叫声:河生哥,你在哪,河生哥……
这不是黄小毛的声音么?借着月光,依稀看着那小子正在河滩上四处寻找着我,便扔了一小块石下下去,砸在他身后的消滩上,说:“你大爷在这,快上来倍我喝会酒。”
黄小毛立马寻路爬了下来,抓起我的手焦急地说道:“河生哥,快跟我来,快!”
他这么急着拉我走,想干什么?
我正感莫奇妙时,黄小毛就将我拉到了河边一船摇橹前,船狭窄的船舱里坐着一个白衣女孩,正是小莲。
他将我推上船后,然后扑腾一下跪了下来,苦求道:“河生哥,求你带姐姐私奔离开这里吧,**宝一家不是人,是畜牲!若姐姐真的嫁过去了下半生就苦了。”
“河生哥,求你带姐姐走吧,带她走上一条活路,有多远走多远,求你了!”
说罢,他就将船推离了河滩,船顺着水漂远了,不一会功夫就漂到了嘉陵江心。
北洋捞尸档案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末穿今,穿越六十年代当军嫂
- 简介: 末世双系异能陈晓,带着空间重生到六十年代成为一名下乡知青,在这个饥饿的年代陈晓只想吃好、喝好顺便赚点小钱。至于老公那是什么东东,陈晓表示直接无视掉。 要是遇到极品亲戚怎么办?当然是揍你没商量。 那要是再遇到一个圣父老公怎么办?当然是甩甩甩,不能为了一颗歪脖子树而放弃整片森林。 方云皓重生回来了,正在自己努力的攀向人生的高峰时,忽然发现自己的第一任知青小妻子既然没有死,还给自己生了个漂亮的女儿。不过自己的这个小妻子,好像很不一般。韩磊狂妄自信,不过在遇到陈晓这个小妖精后,唉!一切尽在不言中………。本书数字版权由“龙阅读”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75.1万字6年前
- 快穿:我当霸总那些年
- 简介:穷困潦倒的阮醒报名参加了一个脑域开发的有奖活动——活动人员根据自己所选择的人设然后随机匹配世界。阮醒在白莲花女主、逆袭女配、虐渣女主的人设里毅然的选择了霸总人设。每个世界的她要么地位超然、要么家世显赫、要么位高权重,每天不是当霸总就是走在当霸总的路上,简直爽到爆!初次开启副本,听说有任务:阮醒:呸!有钱人的日子是人民币不好花,还是包包不够换?阮醒:拿钱做投资!天凉王破!后来——阮醒:哦!这男人竟然该死的如此甜美!阮醒:我要为这个小可怜承包一整座鱼塘!是!一!整!!座!!!副本一:《全民首富是她爸》副本二:《是冷艳的霸总啊》……剩下副本待定。小贴士1:男主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待定,但是女主她肯定是一个人哒(≖‿≖)✧小贴士2:第一个世界是适应性世界,不走霸总风,第二个世界开始走!另:霸总是女主是女主是女主!小贴士3:禁止盗梗!禁止盗文案!违者必追呦~
- 4.5万字5年前
- 鞠婧祎:我恨你
- 简介:因为一场车祸,她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她不想记起那个曾经伤害他的男孩儿,但是他又出现在她的生命里了,这让她十分的熟悉,可是她永远记住,她一直都是恨他的
- 2.3万字5年前
- 轻轻的到来
- 暂无介绍哦~
- 17.2万字5年前
- 农家小妇女
- 简介:周家的四哥赌输了钱,母亲病重,赌场的人还想让满宝卖身偿债。村里人都说周家的宝贝疙瘩好日子到头了,老娘也握着满宝的小手哭唧唧。满宝却手握系统,带着兄弟嫂子们开荒,种地,种药材,开铺子……日子越过越好,嫂子们却开始忧心满宝的婚事。“小姑,庄先生的孙子不错,又斯文又会读书,配你正好。”“小姑,还是钱老爷家的小儿子好,又漂亮,又听话,一定不会顶嘴。”满宝抿嘴一笑:“我早就想好了,就选被我从小揍到大的竹马白善宝。
- 3.1万字5年前
- 小狼狗和黑月光
- 简介:作为一个心黑手狠玩弄了数人感情的女流氓,申知一最近被一个所有人眼中天真善良又心软还爱她到骨子里的小弟弟给甩了,申知一很受刺激,深深的怀疑自己是不是老了,没魅力了,所以当这位小弟弟喝的醉醺醺再次站在她面前说要和她睡觉的时候,申知一决定睡一次保本,睡两次就赚了。 小狼狗:“申知一,你就是馋我身子!” 申知一摁住扑上来亲她的小狼狗:“到底谁馋?”
- 4.0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