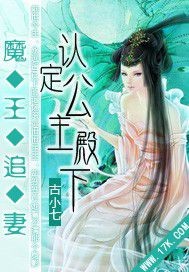第055章别问君心
“朕当然认得它,只是你想过没有,一旦用了,月家便再无免死的特权了。”唇边漾开一丝若隐若现的笑意,玄寂离似提醒,又似嘲讽,“广陵王还是要用它吗?”
“是,本王还是要用。”广陵王月惊枫毫无迟疑地将它交给随侍一旁的李莲成,后者看了皇上一眼,见他未置可否,待要接过,猛听得一声:“皇上——”
“怎么,爱妃有建议?”
那淡淡的一瞥,与淡淡的口吻,却令安景凉心中陡然一寒,便自觉地闭上了嘴巴。
“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着革去窦涟漪皇后头衔,于宫中浣衣局当差思过。”
旨意在男人轻移的步伐中一个字一个字地飘出来,他上了车,向着呆立在原地的高贵女人伸出手,唇边浅笑若狸:“爱妃,不想回宫了吗?”
安景凉从怔忡中惊醒,小碎步跑上前,将手递于车上的男人,踩在跪伏在地上的小太监背上,也登上了马车。
今天发生的一切,安景凉仿佛做了一场梦,宽敞而豪华的御用马车围得严严实实,雪光映过代表皇权威仪的黄色帷幔,是以车内光线明亮,男人坐在正中闭目养神,英俊无匹的脸上不现半分波澜。
她轻轻地移动脚步至他身畔,伸出一双一看便是养尊处优惯了的手,放至唇下哈了哈,又搓了两搓,这才轻柔地搭在男人太阳穴上,按摩起来。
男人一动不动,俊脸无波,猜不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良久,他蓦然张开眼睛的同时,抓过她的一只手,放在视线下细细端祥,肌肤细腻,纤纤十指涂了大红色丹蔻,艳丽而妖娆。
“爱妃的手真好看。”好看的薄唇轻抿着,男人一点不掩饰眼里的欣赏之色。
他从来没夸过她好看,这是第一次,虽然夸的只是手,但一点也不影响她狂喜万分的心情,何况,老话不是说女人的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吗,既然有因三寸金莲痴狂的,便有为一双柔荑而神魂颠倒的,不是吗?
“皇上,您干嘛盯着臣妾的手一直看,看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她的身子因为欣喜而微微颤抖着,加上如娇似嗔的语气,极是妩媚。
他似乎兴致极好,笑着,言语间有一种回忆的味道:“朕记得你名号中的贤字是德安太后亲拟的,是吧?”
这突兀的一句,令安景凉怔了好一阵,心思飞动,不知道皇上这个时候提起旧事是何用心,便字斟字酌地答:“是,皇上好记性。”
“德安太后是觉得合宫中只有你最稳重贤惠,是以拟了这个字。”他捏着她的一根手指,仔细地欣赏着,指尖却在一点一点地加力,温柔的语气依旧一副闲话家常的口吻:“如今孝仁太后也非常喜欢你,常在朕面前夸你。”
闻言,安景凉一喜,正要不胜娇羞地谦虚一句,挫骨一样的痛感便在这时自被他捏着的指头上传来。
“唔——”
她不由自主地低吟一声,那股仿佛要断其指挫其骨的力道却一下子消失了,他松了她的手,从她的斜襟上抽出绣着白玉兰花的丝帕,漫不经心地擦拭着之前施以力道的两根指头。
“站着不累吗,坐吧。”
安景凉浑身沁出了一层细汗,惴惴地在他旁边坐下,“皇上,臣妾哪里做错了,您要打要骂都行,只是别让臣妾不明白。”
她一边说一边仔细地察看着男人的神色,脑中极速转动,莫非,自己买通狱卒拷问窦涟漪的事被他发觉了?
汗一炸,从额头上细细密密地沁了出来,可是那几名女狱卒当场毙命,应该不会牵扯出自己,安景凉这样一想才略略放了心。
“奇了,你很热吗?”男人一边好奇地问,一边用丝帕温柔地搌过她的发际。
如此难得的温存,安景凉的心里却一阵阵发冷,抓住他的手,上牙齿磕着下牙齿,以至声音都在发抖,“谢皇上体贴,臣妾不敢劳动皇上,让臣妾自己来。”说话间从他手里接过丝帕,擦去额头细细密密的汗珠。
“人人都说贤贵妃温凉恭顺,今日一见,果然是一点没错,朕前朝事多,太后还有后宫你以后多替朕照看着点。”
安景凉一听,这话里明显有托付的意味,翻身跪倒,伏地长声:“臣妾一定谨记皇上的旨意,为皇上分忧。”
“嗯。”
男人点着头,将她从地上扶起来,女人顺势依偎进他的怀中,像只温顺的猫儿一样,沦陷在他一时的宠顾里……
半个月后。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即将来临,整个皇宫到处都是一派忙碌的景象,浣衣局也不例外,主子们应酬多了,自然衣服也换得勤,洗衣妇们的活便总也干不完。
偌大的院子里,十几名洗衣妇一人面前一只大木盆、一只小水桶、一只衣篓,外带衣篓里堆积的衣物,都是上好的料子,也不能像普通人家一样用搓板,甚或用木棰敲打,只能用手一点一点地细揉慢洗,若是不小心弄破了,或是挂了纱,便会受到惩罚。
“小姐,你去歇一下,这些留给我做。”
不知道该感谢哪一个,她是戴罪受罚之人,宫中竟安排秀珠依然跟着她,算是有个照应。
窦涟漪浑身酸痛,却咬牙坚持着:“那哪行,你也有任务。”
“小姐,奴婢干惯了,一点也不累。”
秀珠看着主子的手,旧伤还没好,又添了新伤,寒风刺骨的大冬天,成天泡在冷水里,手背上起了冻疮,破了皮,红肉露在外面,看上去触目惊心,便跑过去将她身边的衣篓提了过来。
“哟,这浣衣局还时兴带丫头,真是奇闻,你这么好心,不如帮我一起洗了吧。”一个长相有几分娇俏的洗衣妇早就看不顺眼了,呼地起身,将自己的衣篓抱到秀珠身边。
秀珠眼一瞪,挑脚将那家伙的衣篓踢开去:“自己的任务自己完成。”
“李司服大人,这里有人大不敬,竟然将主子的衣物踢在地上,您管不管。”衣篓翻倒,里面的衣物有几件掉了出来,那名洗衣妇一看,竟兴奋地扯着喉咙大叫起来。
窦涟漪一看,心道不好,赶紧过去将衣篓扶了起来,一边捡一边央求:“别叫了,你的衣物我帮你洗便是了。”
“谁,窦涟漪,你好大的胆子,这些衣物可不是衣物,它们就是一个个主子,你踢它,便是踢它的主人,那可都是天皇贵冑,岂是你大不敬的,不惩戒你只怕不长记性,这里有一算一,给我都洗完了才能休息。”
不想还是惊动了浣衣局的管事李司服,跑过来吊梢着一双三角眼,不分青红皂白便下达了惩罚令。
秀珠跳了起来:“什么,这十几盆都让我家小姐洗,你这哪里是罚,分明是要人命。”窦涟漪在一边扯她的袖子,给她使眼色都不中,“这是我踢翻的,要洗也是我洗。”
“你想跟着受罚,那就一起罚好了。”李司服耸耸肩。
秀珠将手中的衣衫往盆里一扔:“不干了。”
“秀珠,你太放肆了。”不管李司服存了什么心,但有一点她说得没错,动主子的衣物便是动主子本人,弄得不好掉脑袋也是有可能的,窦涟漪先喝止住秀珠,然后转身冲着从前的奴才,如今的上司,陪笑道:“秀珠不懂事,您大人大量,原谅她一回,您的指示我们一定照办,不洗完不吃饭,也不睡觉。”
李司服鼻孔朝天哼了一声:“算你识相。”
“嘻嘻,这下可以休息一天了。”那些洗衣妇们欢喜雀跃,方才挑事的娇俏洗衣妇更是得意非凡,掐着水蛇腰指着两人:“从前是主子又怎样,现在还不是跟我们一样,趁早老实点,不然有你们好果子吃。”
“你。”
秀珠气得说不出话来,窦涟漪却像没事人似的,坐在寒风里轻轻地揉搓着一件桃红色的衫子,她记得那日行刑时,皇贵妃便是穿着它去观刑的。
“小姐,您就一点也不怨吗?”秀珠回来,抢着洗了起来,一边洗一边发牢骚。
窦涟漪笑笑,轻言细语地:“皇上正在气头上,我多苦一分,他的气便会多消一点吧。”他说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所以明知她的手受过重刑,却将她发落来浣衣局当差。
“可是您太苦了。”秀珠的眼圈红了,怕她看见,低下头狠命地搓洗起来。
所有的活干完后,已是半夜,两个人又累又饿,那些衣物本是上等的料子,并不刺手,可是实在是太多了,又在冰冷刺骨的井水里泡了十几个小时,十个指头都磨破了,流着血水,却也感觉不到疼痛了,它们早已经冻僵了。
而且,人一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可是到了早上一醒来,浑身的骨头似散了架不说,十指倒是不僵了,却是钻心的痛。
“小姐,您不如请一天假吧。”秀珠提议。
窦涟漪瞄了她一眼:“你觉得可能吗?”
秀珠便不作声了,权当方才的话压根没说。
这一天,昨日挑事的娇俏洗衣妇见占了便宜,又带头起哄,通过这段日子的相处,精明一点的人已经看出来了,李司服也存了心折磨两人,所以,她们宜发投其所好,挑衅起来更是肆无忌惮。
倾城废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叶罗丽之爵冰的倾城时光。
- 简介:冰公主其实是玉馨公主,是世界上最历害的。
- 0.5万字6年前
- 魔王追妻:认定公主殿下
- 简介:前世今生,永远留存下的记忆滚过世世生生,却独独让她看不清那个身影,一抹刺眼的红色,霎时绽放在那如丝白袍之上,墨色长发似要抓住那些许的什么,却还是,理不清,理不清。。。。。。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79.8万字6年前
- 邪王的独宠医妃
- 简介:大婚当日,不仅未等来心上人的花轿,反而被抬入宫中替老皇帝冲喜。然冲喜失败,老皇帝驾崩,心上人踩着她继任皇位,而她作为谋逆罪妃,被灌哑药挑断手脚筋脉陪葬于地下皇陵之中!以她一人之死,换得所有人鸡犬升天!等她再次醒来,时光竟倒流回三年前,她仍是弱质少女,父慈母贤,亲妹可爱,心上那人依旧一副谦谦君子模样,对她轻声软语恩爱有加。霍明珠在心底冷笑,所有和睦慈爱都是假象,她已糊涂一世,再不会相信他们的花言巧语,上辈子我死,这辈子只能你们亡!
- 1.9万字5年前
- TFBOYS之皇后逃婚行走江湖
- 简介:(古代言情小说)古代,在柳尚书府有两位千金,一个能文,一个能武!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大小姐柳佩婷温柔淑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二小姐柳菲雨从小喜欢当女侠客!柳菲雨有一次出来打猎时,救了一个人,没想到这个人既然是当今的太后!太后为了报恩,就赐婚她柳菲雨和当今圣上王俊凯成亲,在成亲的那天,柳菲雨逃婚了,然后…………。
- 47.8万字4年前
- 乾隆,永生我是你的长女
- 简介:“班长,他们来了”“大家准备战斗”“是”................"报“”敌军从西边杀来“”撤退,掩护好自己“.................."主子,听说四皇女回来,还听说皇上认了一个义女”“知道了””主子,你不去看看吗?““采荷,你要是想去就去吧”“主子,你真的不好奇?”........................“三皇子出嫁了”“三皇子?”“谁娶三皇子了?”“好像是富察大人家的长子。”
- 2.4万字5年前
- 这个妻主有点渣
- 简介:楚叶原是22世纪的全能女杀手,却因身中蛊毒而死亡,意外穿越到了女尊时代。在这里,女尊男卑,一个女子可以拥有许多夫侍。男强女强/女主冰冷妖艳,智商情商绝对高,三观正/不喜勿喷网编勿扰,见一个举报一个,旦见抄袭者,抓到必究!
- 2.4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