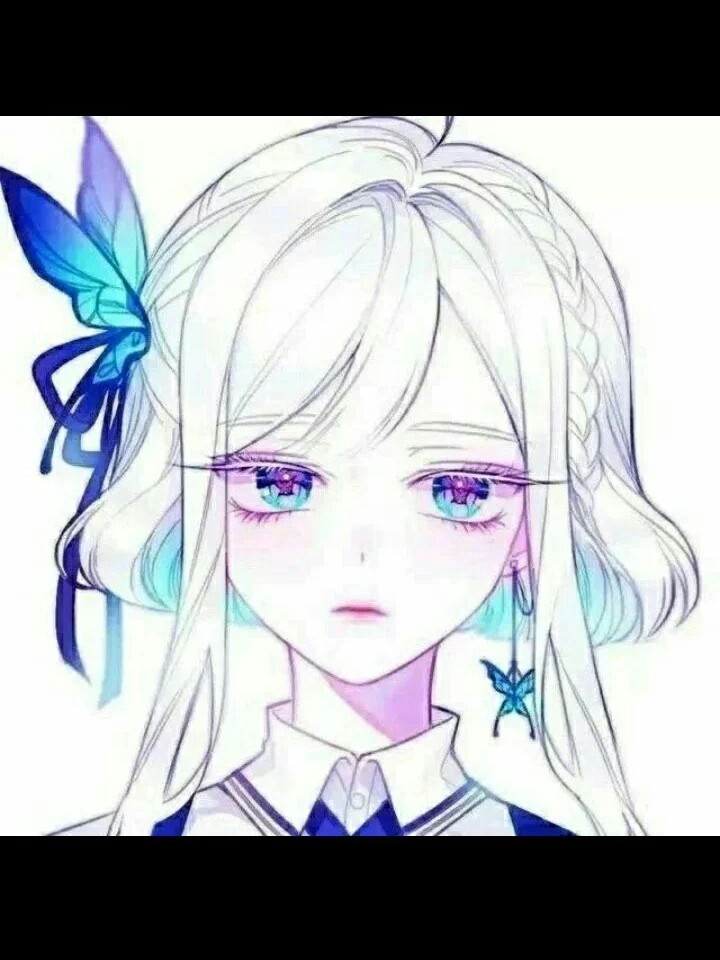第一百八十章尔虞我诈26
我想过自己会残疾,会成植物人,甚至会死。但我没想过有一天我会不能说话。
医生们查不出什么,做出了和若水一样的判断,说我这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简单说就是我自己受了刺激,所以不想再说话了。
笑话,我自己不想说话,我能不知道吗?
但他们说这可能是潜意识的想法。
我不说话了。
嗯,我也不会说话了。
司云虽然也每天守着我,但一直郁郁寡欢,若水是想陪我的,但那个陌生的女人把她拉走了。
已经两天了,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按道理我车祸后,官方应该联系的只有司云和志成云,而我通讯录里压根没有若水,她和我隔着十万八千里,根本不可能知道,难道是司云通知的她?
可瞧瞧司云这态度,摆明了不欢迎若水,又想想她之前煞费苦心地帮助若水离开这里,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能让她去在这个时候通知若水。
但如果不是司云,难不成还能是志成云?
这个男人的心思我总是猜不透,说不定他又在打什么算盘。
我的心思忽然疑心起这次的车祸来。但我去找冷仔和阿毛的心思是临时起的,所以回来的路上我意志消沉,车都是七拐八拐乱开的,应该不存在什么人定点埋伏我的事。
设计车祸这件事其实我是懂一些的,无外乎两种,一是在车里事先做手脚,二是用外力造成意外的假象。
我明显感觉这次事故是我的错,况且交警和保险也来和我接触过,说另一个受害人也伤得不轻,判决要等到我们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起码要能起身对质一下当时的情况,所以现在责任在谁还不好说,但交警和律师也明白告诉我了,他们看视频,责任不出意外地话就是在我身上。
所以基本可以排除被设计的思路。
想来还是我经历了这些之后变得疑神疑鬼了,明明自己该负全责的,这会儿又搞起阴谋论来了。
“老公?”司云端着热水走进来,看我发呆,叫了一声。
我扬起眸子来看她,因为不能说话,所以显得冷冷清清。
大概是看出我的失意,她加快了脚步坐到我的身边,然后递水给我,说:“医生说这应激反应不是身体上的毛病,所以说不定哪天就好了,你别往心里去。”
司云对我不能说话的事情介怀到看她一眼就能完全体会的地步,竟然还安慰我,也难为她了。
不过我心里比谁都不好受,所以当下也回应不了她什么积极地东西,只是呆呆地接过水来喝,眼睛盯着下降的水位,脑袋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司云可能受了冷落,没消一会儿,她就又借口拿药出去了。
我想,她可能不喜欢医院这种地方。
如果是若水在这儿……
心烦意乱,唯有周公能慰藉我的心灵。
可能是药剂的缘故吧,总是觉得睡不够。
晚上我醒了一会儿,其实也不算醒,是朦胧地那种意识,知道自己没睡,但也没有起来的意思,模模糊糊的。
隐约间听到一声叹息,然后有个宽厚的手掌拂过我的脸,这时我确定是有个人坐在我旁边,我下意识地没有动,假装熟睡。
但此后再没有动静了。
难道是那人看破了我的伪装,所以离开了?
但很快,屋子里响起的窸窣声打破了我的猜测,那个人还在。
我隐约猜到是志成云,因为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哪个男人会半夜潜入我的病房唉声叹气。
只是,他已经和我不止一次撕破脸皮,从来在我投入“父子情”这戏码中的时候让我一次次认清现实,却又总这样给我错觉,让我捉摸不透。
明明可以不来叹这一声,明明可以不在乎我受伤的脸,他为什么要来这里“表演”?这么晚了,还有观众在场吗?
我忽然心惊,他半夜都不放过演戏的机会,专门演给我看的吗?
他根本知道我是醒过来的吧?
不不不,太阴谋了。我宁愿相信他是良心发现。
“没有谁是完全可信的,也没有谁是完全不可信的。”
他突然说了这样一句没头脑的话。
他到底知不知道我醒了?
这口气又像是自言自语,难道他是在告诉自己可以相信我?
他已经把我玩得晕头转向,就差说牵着鼻子走了,他还不信我?
后来屋子里彻底安静了。
晚上仔细听的话都是会有噪音的,但有时候独处的时候听到的那种“安静”和这个是不同的。那是一种“没有声音”的状态,静的可怕,你自己都忍不住想说两句。
我现在就处于这个感觉,但却不能说话。
他走了吗?
我在心里问自己。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一切如旧,司云站在桌子边,打开保温的饭盒,然后端出菜来给我一点点地说她怎么早起,怎么为我学做饭的光荣事迹。
我这两天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但还是乖乖坐起来准备听她的“演讲”。
但等了半天都没有开始,我不禁好奇地看她,难道是我昨天没打招呼就睡了,所以她不高兴了?
她刚好要把饭放在我升降的桌子上,转身对上我瞧过去的目光,“怎么了?”
我确定我从她嘴巴的开合认出了这三个字。
但我怎么没听见呢?
我皱起眉头,挑了一下眉梢。
她强颜欢笑,用眼神询问着我,然后说了一句什么,我的心瞬间凉了一截。
我听不到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表情,但我只觉得动一动嘴角,抬一抬眼皮都是十分费劲的事。
我见有只手在我眼前晃啊晃的,我觉得很烦,但也没动,过了一会儿,手就停了,轮到我肩膀遭殃,被人晃动了半天,司云惊恐的脸一览无余。
接着就是那群白大褂上场的时间,围着我又是测血压又是看瞳孔、摸脉搏的,最后竟然消失的若水也来了,只不过这次她没带那个短发的女人。
若水站得最远,但不知怎么,她一出现,我的心就没那么慌了。
若水说我身体指标都正常,不能说话应该是受事故的刺激,说我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让我放松放松,说随时有可能恢复。
我想我这耳朵可能也是这个状况。
但若水的表情渐渐变了,显然是那堆白大褂们说了什么,紧接着就是司云跌坐在床边的一幕。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我直觉不是什么好事,甚至糟糕透了。
白大褂们面面相觑,然后离开了病房,司云看了我一眼,哭着走了。
我正莫名其妙,手心就传来一阵温热,我偏过头,是若水。
若水握着我的手,用很慢很慢地速度对我说:“你会好起来的。”
她说的很刻意,应该是为了让我读她的唇。
我虽然看懂了,但我心里更沉了。如果若水有把握,她就会用那种语气对我说:“少爷,没关系的,很快就好了。”
但她恰恰用了最沉重的鼓励,还忘了俏皮的微笑。
看来我是病得不清。
好了,一周不到,自己就变成了聋哑人。
帮会还需要这样一个人吗?
我还能坐到东城会会长的位置吗?
呵,当然不能。
这比死了还可笑。
世界静悄悄的,如果不是我看着若水,我恐怕想象不出身边还有个人。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接下来的日子我全都忘记了,如果非要用个词来描绘的话,可能是绝望。
因为聋哑的症状来得突然,医院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治疗的方案来,所以身子骨好的差不多,我就出院了。
没有人来看我,若水每天会给我做饭,司云则不知道上哪去了。
虽然古语有云“患难见真情”,而且我和司云本来也不是因为真爱在一起的,她的消失我不应该感到难过才对,可事实证明,我的内心深处并不这么认为,我很失望。
饭突然放在了我的面前。
可能因为没有声音的缘故,这几天不管眼前出现什么,我都感觉是突然出现的。虽然渐渐习惯了,可偶尔还是会吓一跳。
若水替我摆好餐具,我没有看她,等我吃了一半抬起头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她这几天总是会出去,不过到了饭点她都会回来,所以我也见怪不怪了。
冬至这天我睡到了中午,不是自然醒,而是被手上的针刺感弄醒的。
“你干什么。”我用无声的唇语说。
那边若水显然没有听见,抽了我半管血,站起身的时候才对上我的眸子,愣了一下。
“你干什么?”我又问一句。
她蹲下身来,用一双坚毅的眸子望着我,“少爷,你放心,我一定会治好你。”
不等我说什么,她就吻了我的额头,出去了。
这种种感觉都让我以为自己是个废人。
我“痛恨”她们。
一个弃我而去,一个形影不离。偏偏我希望她们角色调换,如此若水不会看见我的狼狈,司云的存在会让我的自尊心得以保存,起码,我还有魅力。
然而现实却无情地扇我耳光,让我无力反抗。
少爷请用餐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天才宝宝:爹地追妻很疯狂
- 简介:“粑粑!宝宝终于找到你了!!”某小只冲上来就抱大腿!“抱歉,我儿子认错人了。”沈瑾汐吓得心肝脾肺肾都在颤抖!麻溜的跟某人撇清所有关系!!顾云琛眼眸微眯,“害羞?5年前的那个晚上,你胆子可是很大的。”老婆恨不得一脚把他踹老远?呵呵……门边儿都没有!!!本书数字版权由“奇文”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78.2万字6年前
- 小白兔乖乖
- 简介:老婆,吃一口,好不好?我不吃!吃一口吧~要好好吃饭~我不要!你不吃?那我就吃了你!本书很纯,很暧昧哦~我的群376800104大家来玩啊~
- 54.5万字6年前
- 限时妻约:暴君总裁狂宠妻
- 简介:“不……不要。”新婚之夜,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她身上留下烙印。厉司琛,Pt·U集团掌权人,权倾凰城,果决杀伐;传闻他高冷禁欲,不近女色,然而只有顾薇茵知道,传闻都是他喵骗人的。老公太凶猛,唯恐小命不保,顾薇茵只能——逃!深夜,他将她逼至角落,边解纽扣边问,“宝贝儿,敢带球跑?可是要付出代价的……”本书数字版权由“龙阅读”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61.1万字5年前
- 狼王陆少强势宠
- 简介:【打赏15金币加更,花花50朵加更,评论50加更哦】沐知夏,轩夏集团千金,与父亲吵架离家出走,想到自己无处可去,给好姐妹打电话,两人跑去了夜总会,在这里,沐知夏得罪了大人物,谁知这大人物竟然是她未婚夫,,,,预知后事如何,请深入了解~高甜文,从头甜到尾,甜而不腻哦
- 2.7万字5年前
- 厉小姐,你看起来很攻
- 简介:女强男弱文+同人文男主沐若希超级奶女主是冷面女王,而且极其易怒,心狠手辣,霸道占有欲厉桀星,正如她的名字,潜伏在暴君的阴暗下,却拥有那一丝温柔的星光,那星光属于谁呢?
- 7.5万字5年前
- 重生之恶毒女配是影后
- 简介:别名(女配家人痛哭流涕赎罪的日子)上一世,木晴可谓是看透了人情冷暖。父亲偏爱白月光生的妹妹,哥哥也是不时帮着那个小白莲说话。就连她暗恋并且有婚约的学长也是喜欢上那个小白莲。自己顺风顺水的娱乐圈生活被说成陪睡上位,小白莲就叫做深藏不露。众叛亲离后的木晴得了抑郁症,最后孤独长眠。但是木晴死后发现自己竟然是一本烂尾小说的恶毒女配的时候果断表示自己不能忍。获得重来一次的机会,还有剧情加成,嘿嘿嘿,果断走上人生巅峰。重生一世,她看透一切。亲人离心,她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看看这一世的木晴怎么吊打渣渣,走向人生巅峰!但是这位病娇小哥,放下你手里的作案工具啊!(家人都要重生,男主嘛嘿嘿嘿,有私设)第一次写这种文,我还是个宝宝,有什么建议评论区见,但是不喜勿喷。对了,还有一个可可爱爱的系统,它也要有cp哦!
- 0.5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