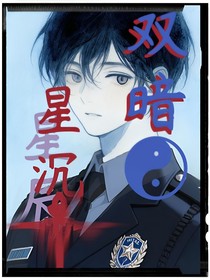心灵时间的数学原理(一)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兼精神病学家,我发现我很难跟人讨论有关意识的问题。最让我看不惯的是,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在提出那些问题时,总是把心灵看做一个物体,可以由它具有的属性和它实现的目的来确证它的存在。
但在物理学领域,认为物体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存在”都是不谨慎的。这背后其实有更深层的问题:怎样的过程让我们认为(或者误认为)一物存在?例如,牛顿在解释物质世界时,论述的是有质量的物体如何对力做出反应。而在量子物理学产生之后,人们发现,测量的本质及意义才是根本问题,因为质量和力的概念都依赖于它。 但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这些问题迫使我把意识当做一种有待理解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有待定义的物体。简而言之,我认为意识仅仅是一种自然过程,与进化或天气一样。为了更好地说明“意识是一种过程”,我很喜欢这么做:把一个问题中的“意识”一词替换成“进化”,然后看看它还能不能成立。比方说,把“为什么要有意识?”这个问题换成“为什么要有进化?”按照科学的说法,进化当然没有任何目的。进化没有任何功能,也没有任何理由;它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只能依其自身而被理解。既然我们都是进化的产物,意识和自我同样能够作这种‘是一种自然过程’的理解。
我对意识的观点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观点相似。丹尼特整个学术生涯都在探寻心灵的本源。他很在意这个问题:无意识的、纯粹的“起因”(A导致B)如何演变为我们所了解的有意识的“理由”(A发生,所以B能发生)。丹尼特的结论被他称为“达尔文的危险思想”:可以存在没有设计者的设计、不源于理解的能力、和无人提出就自己产生的理由(或者说“无根基的根据”)。一个甲虫种群如果超越了另一个甲虫种群,我们一定能从中找出某种“理由”来。比如一个有利的变异增强它们的隐蔽色。在 《从细菌到巴赫:心智的进化》(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中,丹尼特写道,“自然选择是一个自动寻找理由的机制,在跨越很多个世代的时间内‘发现’各种理由、‘选用’一些理由并‘专注’于发展它们。我之所以打引号,是要提醒人们:自然选择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它本身也没有理由,但它却能胜任完善设计的‘任务’。”
我希望能让各位读者明白,大自然本身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产生出理由来。我接下来想说的是,事情不是因为某种理由而存在,但某些过程确实相当于在找理由。我说“找理由”,是指通过推理或溯因找到解释,也就是为观察到的现象寻找潜在的原因、规律或原理。
用“推理”的视角来理解“过程”,我们就能优雅地解释心灵为何存在,不过这个解释可能会让“心灵”的内涵贬值。推理的过程近乎万物至理,可以解释进化、意识乃至生命本身。推理的过程,就是一路溯因到底。我们呱呱坠地时,已经是一个正在运行的过程了;而任何过程都只能根据极少量的信息来推断外部的世界,前提是那些信息还必须选对了。这一观点消解了心灵和物质、自我与世界、表征主义(我们如实把握现实)与涌现论(我们在溯因推理中接触世界,在此过程中涌现出现实)这几组常见矛盾。那么,推理是如何先于推理者而存在的呢?最终产生了意识的那个过程,是如何被无生命的物质开启的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关于过程的一些基本规则,然后我再逐渐阐明。我们只关心构成复杂系统的过程。这些复杂系统,整体大于各组成部分之和。为了方便各位理解,不妨对比一下此类过程的相反面:如果你在打靶,物理学家能根据子弹离开枪膛时的角度和动量来确定子弹在靶子上的落点。这是因为射击过程是一个近乎线性的系统。射击过程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单向决定着射击过程整体的行为。相比之下,你却不能确定一个围绕原子运动的电子具体在什么位置,也不能确定纽约明年会不会受到飓风侵袭。这是因为飓风、原子、以及一切自然过程,都不完全由其初始条件所决定,因为系统整体的行为会反过来影响其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称其为复杂系统。
物理学家们认为, 复杂系统可以通过其状态来表征;状态由一些变量和取值范围来表述。比如说,在量子系统中,一个粒子的状态可由包含了其位置、动量、能量和自旋的波函数来描述。而对于宏观系统,例如我们自己,我们的状态包括身体各部分的位置和动作、大脑的电化学状态、器官的生理活动,等等。系统的状态对应于它在可能状态空间中的坐标,每一个变量形成该空间的一个坐标轴。
一切都应该随着时间的推进,变得更加随机、更加分散、更加混乱。为什么没有变成那样呢?
事物在状态空间中运动的方式取决于它的李雅普诺夫函数(Lyapunov function)。该数学量能够描述一个系统在具体条件之下有怎样的行为。它表达的是有多大概率作为某个具体状态的函数处于那种状态(即:系统在状态空间中坐标的函数。可以类比气压——气压是空气分子被测量时的密度的函数)。如果我们知道系统每一个状态的李雅普诺夫函数,我们就能得出从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的流(flow),并通过这个流来表征整个系统的存在。这就好比知道山地每一点的高度,以此推知一条小溪如何流过这一地形的表面。李雅普诺夫函数就好比那座山的地形,而系统随着时间的发展过程就好比水的流动方式。
复杂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似乎根据各自的李雅普诺夫函数向更加可能的状态演变。也就是说,函数的输出值越来越小。这意味着,复杂系统通常只占据很少量的状态,并且那几种状态被反复占据。如果接着用山与溪流的比喻来解释,就是水向下汇入大海之后,会蒸发、形成雨云并最终通过降水返回山上。你也可以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例子:你的体温总是维持在恒定范围内,你的心脏有规律地跳动,你有规律地吸气、呼气,而且你大概还遵循某种每日或每周的时间安排。
此类周而复始的 自组织行为与宇宙通常的行为间有着强烈反差。一切都应该随着时间的推进,变得更加随机、更加分散、更加混乱。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一切都趋向于混乱,而熵通常会增加。为什么没有变成那样呢?
复杂系统能够自组织,是因为它们有 吸引子(attractors)。吸引子是那些能够相互加强的状态形成的一种循环:它会使过程达到稳定点,但这不是通过损耗能量而最终停止运动,而是会达到动态平衡。 稳态就是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如果你被猛兽吓到了,你的心率和呼吸频率都会加快,但你会(在“战或逃”反应之后)自动做出一些反应,让你的心血管系统恢复平静。每当偏离了吸引子,就会引发思想、感情和行动的“流”,最终将你拽回你所熟悉的吸引循环。就人类而言,我们身体和大脑的一切兴奋状态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在靠近吸引子,也就是靠近我们最可能的状态。
这样来看,人类不过是“奇怪的循环”(哲学家侯世达的说法)。我们都在一个巨大的、高维的、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状态空间中流动,但我们的吸引子迫使我们在闭合圆圈内运动。我们就像一片秋叶;在湍急的溪流旋涡中打转,画出一个永无止境的轨迹,并把那个小小的轨迹当成整个世界。把我们自己描述为这种 调皮的循环,从目的论的角度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但它对于理解任何具有吸引状态的复杂系统(比如你、我),有着深远影响。
每当遇到新的体验,你的生理系统都会进行推理,试图将正在发生的事情套入某种熟悉的模型。
小结:只有当复杂系统(包括我们自己)的李雅普诺夫函数能够精确描述其过程时,复杂系统才能存在。并且,如果我们要存在,我们的全部过程,我们的全部思维和行为,都必须降低李雅普诺夫函数的输出值,让我们进入更加可能的状态。那么在实际操作中,这是怎么样的呢?(了解这一点的)秘诀在于理解李雅普诺夫函数的本质。如果我们能理解它,我们就能知道是什么在驱动我们了。
事实上,李雅普诺夫函数有两种很有启发性的表述。第一种表述源自信息论。按照这种表述,李雅普诺夫函数就是意外度(surprise),也就是处于某一具体状态的不可能程度。第二种表述源自统计学。按照这种表述,李雅普诺夫函数就是(负)证据(evidence),即边际似然(marginal likelihood),也就是对某一状态给出正确解释或模型的概率。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存在,我们必须要增加自己模型的证据(或者增加它不证自明的程度),同时最小化我们的意外度。有了这两种表述,我们就能为“存在性动力学”赋予意义和目的论了。
我们现在可以探讨“推理”的问题了。推理的过程,也就是找到最合适的原理或者假设,来解释“世界”这个系统中的现象。严格意义上来说,推理意味着为解释世界的模型找到尽可能多的证据。由于我们总要让证据尽可能多,我们实际上就相当于用自己作为模型,来对世界做出推理。因此,每当你有了新的经历时,你就会作出某种推理,来把这种经历套入某种熟悉的模式,或是调整你的内在状态从而使这一新情况也被考虑在内。与此相同的是,当一名统计学家在考虑要不要引入新的规律来解释某场疫情的传播,或是衡量自己需不需要因为某家银行的倒闭而修改自己的经济模型时,她也是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吸引子至关重要。吸引状态的意外度低、证据多。因此,复杂系统总是进入熟悉而可靠的循环——只有这样的过程才能维持它们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吸引子会促使系统进入可预测的状态,从而强化系统为自己所处的世界建立的模型。如果这样一个总在降低意外度的不证自明的推理行为失败了,系统就会衰变,进入令人意外的陌生状态,直至形神俱灭。过程通过推理来为自己的存在“招魂”,便产生了吸引子。换句话说,吸引子就是生命之源。
如果你能够接受上面的解释,你就拥有了一个关于一切复杂系统(包括生命体)的极限收缩论。任何一个反复占据特定状态的过程(包括你我),只要存在,就一定在进行某种推理。
但真的是这样吗?怎么可能把进化或者自然选择的过程理解为推理呢?难道真的可以?事实上,这种解释真的就是理论神经生物学给出的最新解释。例如,自然以生存和繁殖能力来“选择”生物体,就是基于推理。以一个螃蟹种群为例,并以即个体的表现型为“状态”:这群螃蟹可以有大小不一的钳子、或软或硬的壳;有些螃蟹的眼睛在水下看得更清楚,有些螃蟹的眼睛在水面以上看得更清楚。有众多的表现型,就相当于假设了众多的可行性方案。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一个假设或者模型,该模型可用来推测(具备哪些表现型的)个体适合占据这个生态位,以及(具备哪些表现型的)个体必须在环境压力下为了生存而竞争。
由于进化也是一个复杂系统,它就也必须是不证自明的。也就是说,进化总是会“选择”那些越来越有可能站稳各自生态位的生物体。大钳子有利于螃蟹捕食,因此该性状很有可能会流传;坚硬的壳能帮助螃蟹抵御捕食者;水下视觉能让螃蟹在食物最充足的地方更容易找到食物。于是,适应性就等价于能在某一环境中找到某一表现型的边际似然(marginal likelihood)。换句话说,它的生存完全等价于能作为其生态位优良模型的证据。
一个病毒具有推理过程所需的全部的自组织的动力学性质;但它不具有一个人具有的性质。
把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意识的问题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意识也应当是一种推理过程。意识的过程就是推理知觉状态起因的过程,并以此在世界上生存,回避意外事件。自然选择通过筛选不同的生物来进行推理;而意识则是通过筛选同一生物(特别是其大脑)的不同状态来进行推理。这种观点有大量的解剖学及生理学证据支持。如果把大脑视为一种进行不证自明推理的器官,那么它的每一个解剖学和生理学特征都似乎都能够降低意外度。例如,人脑用不同的脑区来运算某物在哪里和某物是什么。这不难理解,毕竟知道一个东西是什么,通常并不能让你知道它在哪里;反过来也一样。这种对外部世界因果结构的内部化,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若想预测自己的状态,你就必须有一个内部模型来描述这些知觉的生成。
可是,如果意识就是推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所有复杂的推理过程都是有意识的呢?比如从进化到经济体到原子的这一切?未必如此。一个病毒具有推理过程所需的全部的自组织的动力学性质;但很显然病毒不具有人具有的性质。那么差别在哪里呢?
有意识的生物与无意识的生物之间,区别在于它们如何作出关于行动与时间的推理。我的这一论点,部分基于系统与世界之间的互补关系。世界作用于系统,提供感官上的印象,从而提供推理的基础。同时,系统对世界作出反应,以改变知觉流,从而符合它所对世界推断出来的模型。这只是有关行动与感知的循环的另一种解释。例如,我们去看,我们看到,然后以此决定接下来往哪里看。
如果行动依赖于推理,那么系统必须对行动的后果做出推理。你不推测事情的可能结果,你就没法决定该做什么。然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如果一个生物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形成一个模型,那么它就无法推测行动的结果。它需要知道自己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分别该有怎样的预期。比方说,我需要知道(或者下意识地模拟)当我分别往左看、往右看、合上眼时我的知觉会有怎样的变化。可是由于时间总是向前运行,除非一个行动被执行,否则就无法在感官上知道这一行动的后果。
时间的箭头,意味着凡是能够预测自身未来行动的系统,都必须拥有时间的厚度(temporal thickness)。它们必须对自己和世界有着内部的模型,才能对尚未发生和有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做出推测。这样的模型或厚或薄、或深或浅,取决于它们能向后预测多远、向前“马后炮”多远——也就是取决于它们能否推断如果自己采取不同的行动,事情有怎样不同的结果。具有更深时间结构的系统,能够更加有效地推测自己行动带来的反事实的后果。神经科学家 阿尼尔·赛斯(Anil Seth)称之为“反事实的深度”。
那么,如果系统具有一个在时间厚度上很厚的模型,它会推测出或者选择哪些行动呢?答案很简单:它会尽量减少行动中可以预期的意外。证明过程用到了归谬法,从我们已知的这件事开始归谬:若要存在,就必须尽可能降低意外度、增强不证自明度。那么系统具体是如何让预期中的意外度降至最低呢?首先,它们会采取行动以减少不确定性,即避免未来可能遇到的意外(例如受冻、挨饿甚至死亡)。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可视为减少不确定性的机制:无论是受到有害刺激(例如滚烫的盘子不小心脱手)时本能的躲避行为,还是看电视或者开车时为了获取重要信息的那种“认知觅食”(epistemic foraging)。第二,上述这类系统对世界采取的行动似乎有某种目的,也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意外。
这样的系统可以算作一个主体,或者一个“自我”,总之它能够用有厚度的时间模型,对自己的未来作出积极的、有目的的推理。时间模型的厚薄之间存在的差别意味着病毒没有意识。尽管病毒能对外部环境采取推理式的反应,它们却既不能深刻理解自己的过去,也不能长远规划自己的未来。因此,它们不能采取行动防患未然,降低未发生之事的意外度。与此相反,人会积极地、有目的地采取行动来降低意外度、增强不证自明度;而在行为的决策过程中,主体未来的状况是重要的指标。比方说,假如我们像病毒一样活着,我们可以本能地调动自己的葡萄糖储备来抵抗低血糖症状。但是人类可能会做出更长远的规划:开始做饭。类似地,我们一般也不会说进化有意识。自然选择的过程确实会尽可能降低意外度(也就是尽可能增强适应性),但不会降低不确定性,也不会减少整个系统的预期中的意外度(也就是另类的,非达尔文式进化历程下预期的适应性)。
所以说,意识活动与更普遍的自组织行为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选择的规则。在无意识的过程中,选择是在“此时此地”完成的。例如:多个相互竞争的系统(例如进化中的表现型)之间的选择,或者条件反射的触发(例如简单生物具有化学趋向性,它们会靠近或远离某种化学物质浓度更高的区域)。相反,与意识相关的选择过程虽然也是并行运作,但它们都在同一系统之内——该系统同时模拟多种未来、多种不同场景,最终选择采取的行动会使意外度最小。有意识的自我仅仅是这样一种途径:以能够促进主动推理的方式,获取这些反事实的未来。
从进化到意识活动的一切生物学过程都可视为是在进行推理。
“意识是主动推理”这种说法真的有现实意义吗?我认为有。对精神病学家来说,意识状态的改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意识程度的变化,例如睡眠、麻醉和昏迷状态。另一类意识状态的变化则与精神病症状、精神药物、致幻剂等相关。意识程度不同,就会对行为有不同的影响。简而言之,意识减弱的人,通常会缺少反应。请想象一个无意识的人,她如何对刺激作出反应。她仅有的反应就是一些条件反射,只能降低此时此地的意外度。相反,等到她清醒了,她就能调动起来推测过去与未来的能力了。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间的厚度或深度会随着睡眠觉醒周期波动,而我们的意识程度与我们推理的厚度正相关。因此,当我们的模型失去“厚度”,变得与病毒的模型一样“薄”时,我们就会丧失意识。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梦回山海
- 本是青梅竹马,却了天意弄人。梦回过去。你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 3.1万字10个月前
- 双暗星沉
- 万物皆缘,只有惜缘才能续缘……想什么呢?怎么可能?“毒舌是本性,温柔是本性除外的附加品~”“哥…这件事过后,带我去看看海吧…”“你看这片花海......
- 1.5万字6个月前
- 痛的编织袋
- 世界不偏向一方,于是便便有了多种多样的人类“这世界灿烂美好,为何……不让我幸福一点……为什么,我……命该如此吗……若这天下不公,那我便扰乱这......
- 1.6万字6个月前
- 我的短篇小文……合集
- 短篇小文,主要人物炽风、影时等自创人物,自创小说,希望你们喜欢不喜欢也没关系,我很喜欢(虐文)
- 1.2万字4个月前
- 果宝特攻(山海传)
- “不管刀山火海,不畏风雨阻挡,不服天地命运,只愿跨山海,灭世间。”——菠萝吹雪“人生自古都无虞。只怕,跪下屈服。”——橙留香“我的钱不是我的......
- 0.8万字4个月前
- 余妄—春篇
- 《余妄》第一册,主角二人初遇,掀起了一场校园拉锯战
- 0.9万字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