е“ІеӯҰпјҲдёҖпјү
ж‘ҳиҰҒпјҡз»“еҗҲзӣ®еүҚеҝғзҒөе“ІеӯҰе’Ңи®ӨзҹҘеҝғзҗҶеӯҰзҡ„з ”з©¶пјҢжҲ‘еҜ№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иҝҷдёҖдәәзұ»ж„ҸиҜҶе’ҢжңәеҷЁж„ҸиҜҶзҡ„вҖңйҡҫй—®йўҳвҖқиҝӣиЎҢдәҶеҲ»з”»гҖӮеҜ№дё№е°јзү№дёҺжҹҘе°”иҺ«ж–Ҝеӣҙз»•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жҖқжғіе®һйӘҢдәүи®әзҡ„иҖғеҜҹпјҢиЎЁжҳҺеҜ№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е…ЁйқўеҗҰе®ҡеңЁзӣ®еүҚзңӢжқҘжҳҜж— жі•е®ҢжҲҗзҡ„д»»еҠЎгҖӮ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еҜ№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вҖңз§ҒдәәжҖ§вҖқзү№еҫҒзҡ„жҺўз©¶еҲҷиЎЁжҳҺпјҢи®ӨзҹҘиҖ…еҜ№ 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и§үзҹҘдёҺеҘ№еҜ№иҮӘиә«зҡ„и§үзҹҘдёҚиғҪеӨ„дәҺеҗҢдёҖдёӘж„ҸиҜҶжҙ»еҠЁдёӯгҖӮз”ұдәҺ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并дёҚе…·еӨҮвҖңз§ҒдәәжҖ§вҖқзү№еҫҒпјҢиҖҢиҝҷж„Ҹе‘ізқҖ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жңүиў«д»Ҙе…¬е…ұзҡ„ж–№ејҸжөӢзҹҘжҲ–вҖңеҶҚзҺ°вҖқзҡ„еҸҜиғҪ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 и®әжҳҜдәәиҝҳжҳҜдәәе·ҘжҷәиғҪж„ҸиҜҶзҡ„вҖңйҡҫй—®йўҳвҖқе°ҶжҲҗдёәвҖңжҳ“й—®йўҳвҖқгҖӮ
е…ій”®иҜҚпјҡж„ҸиҜҶвҖңйҡҫй—®йўҳвҖқпјҢж„ҹеҸ—иҙЁпјҢз§ҒдәәжҖ§
дёҖпјҺеҜји®ә
и®ҫжғіиҝҷж ·дёҖз§ҚеӯҳеңЁиҖ…пјҢд»–е…·жңүе’Ңеёёдәәж— ејӮзҡ„зӣёиІҢпјҢе’ҢжҲ‘们дёҖж ·дјҡеңЁиў«еӨёеҘ–ж—¶еҫ®з¬‘пјҢеңЁиў«жҢҮиҙЈж—¶еһӮеӨҙдё§ж°”пјҢ并且иғҪз”ЁиҜӯиЁҖйҖӮеҪ“ең°иЎЁиҫҫиҮӘе·ұзҡ„вҖңж„ҹеҸ—вҖқпјҢеңЁдёҺжҲ‘们зҡ„ж—ҘеёёдәӨжөҒдёӯеҜ№зӯ”еҰӮжөҒгҖӮжҖ»д№ӢпјҢд»–жҳҜдёҖдёӘеңЁз”ҹзҗҶж–№йқўдёҺжҲ‘们дәәзұ»е®Ңе…ЁзӣёеҗҢзҡ„вҖңеӨҚеҲ¶иҖ…вҖқпјҲвҖңreplicateвҖқпјү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з”ұдәҺзјәе°‘еҝғзҒөжҲ–зҺ°иұЎж„ҸиҜҶпјҢд»–зҡ„вҖңеҶ…йғЁе®Ңе…Ёй»‘жҡ—вҖқгҖӮ [1]жҹҘе°”иҺ«ж–Ҝе°Ҷиҝҷзұ»еӯҳеңЁиҖ…з§°дёә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пјҢ他们еңЁеҫ®и§Ӯзү©зҗҶеұӮйқўдёҺдәәзұ»е®Ңе…ЁдёҖж ·пјҢеҚідҪҝжҳҜжңҖдёәдё“дёҡзҡ„иЎҢдёәеҝғзҗҶеӯҰ家д№ҹд»Һж— жі•д»ҺйҖҡиҝҮеҜ№еӨ–еңЁиЎҢдёәзҡ„и§ӮеҜҹпјҢе°Ҷ他们дёҺжӯЈеёёзҡ„дәәзұ»еҢәеҲҶејҖжқҘ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иҝҷдәӣ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з”ұдәҺзјәд№ҸзҺ°иұЎж„ҸиҜҶпјҢж— жі•жӢҘжңүе…·жңүвҖңз§ҒдәәжҖ§вҖқзҡ„дё»и§Ӯж„ҹеҸ—пјҢдҫӢеҰӮзңӢи§ҒзәўиүІжҲ–ж„ҹеҲ°з–јз—ӣж—¶зҡ„йӮЈз§ҚвҖңеғҸжҳҜеҰӮжӯӨиҝҷиҲ¬вҖқпјҲвҖңwhat it is like to beвҖқпјүзҡ„з»ҸйӘҢпјҢеҚі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пјҲвҖҳqualiaвҖҷпјүгҖӮз”ұдәҺж„ҸиҜҶе…·жңүзҡ„дёҚеҸҜиҝҳеҺҹзҡ„зҺ°иұЎжҖ§иҙЁпјҢж— жі•йҖҡиҝҮе…¶еӣ жһңеҠҹиғҪиҝӣиЎҢиў«е®Ңе…Ёи§ЈйҮҠпјҢд№ҹдёҚеҸҜд»Ҙиў«иҝҳеҺҹдёәзү©зҗҶеӯҰзҡ„гҖҒз”ҹзү©еӯҰзҡ„жҲ–жҳҜи®ӨзҹҘзҘһз»Ҹ科еӯҰвҖң第дёүдәәз§°зҡ„жҸҸиҝ°вҖқгҖӮ
е“ІеӯҰ家们дёҖеәҰеҜ№иғҪеҗҰи®ҫжғіиҝҷж ·дёҖз§ҚеӯҳеңЁиҖ…пјҲжҲ–иҖ…еғөе°ёпјүеӯҳеңЁдәүи®әпјҢжҜ•з«ҹдёҖдёӘеңЁзү©зҗҶдёҠе’ҢжҲ‘们дёҖжЁЎдёҖж ·пјҢеҚҙе”ҜзӢ¬зјәд№ҸзҺ°иұЎж„ҸиҜҶзҡ„еӯҳеңЁиҖ…пјҢдјјд№ҺиЎЁжҳҺж„ҸиҜҶжҳҜдёҖз§Қйқһзү©зҗҶзҡ„еұһжҖ§жҲ–е®һдҪ“пјҢиҝӣиҖҢеҜ№пјҲдёҖе…ғпјүвҖңзү©зҗҶдё»д№үвҖқзҗҶи®әйҖ жҲҗдәҶеЁҒиғҒ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йҡҸзқҖдәәе·ҘжҷәиғҪзҡ„еҸ‘еұ•пјҢиҝҷз§ҚдёҚдҪҶжҳҜеҸҜи®ҫжғізҡ„пјҢз”ҡиҮіжӯЈйҖҗжёҗеҸҳдёәзҺ°е®һгҖӮзӣ®еүҚзҡ„дәәе·ҘжҷәиғҪе·Із»ҸиғҪиЎЁзҺ°еҮәдёҖдәӣвҖңж„ҸиҜҶиЎҢдёәвҖқпјҢеҰӮдјҠиҺұеҹәе§ҶпјҲEliakimпјүз»„з»ҮејҖеҸ‘зҡ„иҮӘдё»иқҷиқ жңәеҷЁRobatпјҢе…·жңүдёӨдёӘиҖіжңөе’ҢдёҖдёӘеҸ‘е°„еҷЁ, е°ұеҸҜд»ҘеҲ©з”ЁеӣһеЈ°е®ҡдҪҚжһ„е»әеңәжҷҜең°еӣҫжЁЎеһӢпјӣ [2]жқЁпјҲYangпјүз ”еҲ¶зҡ„з”ЁдәҺ家еәӯжҠӨзҗҶзҡ„вҖңжғ…ж„ҹж„ҸиҜҶжңәеҷЁдәәвҖқпјҢеҸҜд»ҘеҫҲеҘҪең°иҜҶеҲ«дёҺиЎЁиҫҫжғ…ж„ҹгҖӮ [3]дҪҶжҳҜпјҢзӣ®еүҚзҡ„дәәе·ҘжҷәиғҪзҡ„иЎҢдёәпјҢеҹәдәҺдәәзұ»йў„е…Ҳзј–еҘҪзҡ„з®—жі•е’Ңжө·йҮҸзҡ„ж•°жҚ®еҲҶжһҗи®ӯз»ғ, иҝҷж„Ҹе‘ізқҖе®ғ们е’Ң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дёҖж ·е№¶дёҚвҖңзҗҶи§ЈвҖқиҮӘе·ұжүҖжү§иЎҢзҡ„еҶ…е®№, жӣҙдёҚз”ЁиҜҙеҶ…зңҒиғҪеҠӣе’Ңз§ҒдәәжҖ§зҡ„ж„ҹи§үз»ҸйӘҢгҖӮеӣ жӯӨпјҢзӣ®еүҚзҡ„дәәе·ҘжҷәиғҪдјјд№ҺйҖҗжёҗжҲҗдёәдәҶи®ҫжғідёӯ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зҡ„зҺ°е®һзүҲгҖӮ
дёҺе“ІеӯҰ家们еҜ№ж„ҸиҜҶзҡ„вҖңжҳ“й—®йўҳвҖқдёҺвҖңйҡҫй—®йўҳвҖқеҢәеҲҶзұ»дјјпјҢйңҚе…°пјҲHollandпјү е°Ҷдәәе·Ҙж„ҸиҜҶеҲҶдёәејұдәәе·Ҙж„ҸиҜҶе’Ңејәдәәе·Ҙж„ҸиҜҶ, еҜ№еә”дәҺдәәе·ҘжҷәиғҪж„ҸиҜҶзҡ„вҖңжҳ“й—®йўҳвҖқдёҺвҖңйҡҫй—®йўҳвҖқпјҢеүҚиҖ…ж„Ҹе‘ізқҖвҖңеҰӮдҪ•дҪҝжңәеҷЁе…·еӨҮж„ҹзҹҘиғҪеҠӣгҖҒжҺЁзҗҶиғҪеҠӣпјҢиҜҶеҲ«е№¶иЎЁиҫҫдёҖе®ҡзҡ„жғ…ж„ҹеҶ…е®№вҖқзҡ„й—®йўҳпјӣиҖҢеҗҺиҖ…ж„Ҹе‘ізқҖвҖңеҰӮдҪ•дҪҝжңәеҷЁе…·еӨҮиҮӘжҲ‘ж„ҸиҜҶгҖҒзҺ°иұЎж„ҸиҜҶпјҲж„ҹеҸ—иҙЁпјүгҖӮвҖқ [4]зӣ®еүҚзҡ„дәәе·ҘжҷәиғҪз ”з©¶еӨҡеҒңз•ҷеңЁеҜ№вҖңжҳ“й—®йўҳвҖқзҡ„и§ЈеҶідёҠпјҢиҖҢеӨҡж•°и®Ўз®—жңә科еӯҰ家и®Өдёәи§ЈеҶівҖңйҡҫй—®йўҳвҖқпјҢе°Өе…¶жҳҜ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й—®йўҳзҡ„и§ЈеҶіпјҢжҳҜдә§з”ҹвҖңзұ»дәәж„ҸиҜҶжңәеҷЁвҖқзҡ„еҝ…иҰҒжқЎд»¶гҖӮ [5]
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дҪңдёәдәәзұ»ж„ҸиҜҶз ”з©¶дёӯжңҖеӣ°йҡҫзҡ„йўҶеҹҹд№ӢдёҖ, дәәе·ҘжҷәиғҪйўҶеҹҹзҡ„еӯҰиҖ…еҜ№дәҺжңәеҷЁжҳҜеҗҰгҖҒд»ҘеҸҠеҰӮдҪ•жӢҘжңү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и§ӮзӮ№дј—иҜҙзә·зәӯгҖҒзҗҶи®әдј—еӨҡпјҢиҝҷд№ҹеҜјиҮҙиҮід»ҠжІЎжңүе®һйҷ…еҸҜж“ҚдҪңзҡ„жңәеҷЁзі»з»ҹиў«з ”еҸ‘еҮәжқҘ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Ҳ‘еңЁиҝҷзҜҮж–Үз« дёӯ并дёҚжү“з®—вҖңеҚ·е…ҘвҖқиҝҷдәӣйҖҗжёҗвҖңзҗҗзўҺвҖқзҡ„и®Ёи®әдёӯпјҢиҖҢжҳҜиҜ•еӣҫз»“еҗҲеҝғзҒөе“ІеӯҰе’Ңи®ӨзҹҘеҝғзҗҶеӯҰзҡ„з ”з©¶пјҢеҜ№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иҝҷдёҖжҰӮеҝөзҡ„вҖңз§ҒдәәжҖ§вҖқзү№еҫҒиҝӣиЎҢеҲҶжһҗпјҢ并表жҳҺжӯЈжҳҜиҜҜи®ӨдёәиҜҘзү№еҫҒе…·жңүе®һеңЁжҖ§пјҢиҮҙдҪҝеӯҰиҖ…们еҜ№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 ”з©¶и·Ҝеҫ„дә§з”ҹдәүи®әгҖӮжҺҘдёӢжқҘзҡ„и®әиҝ°е°ҶеҲҶдёәеӣӣдёӘйғЁеҲҶпјҡйҰ–е…ҲпјҢжҺўз©¶дё№е°јзү№пјҲDennettпјүеҜ№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еҗҰе®ҡи®әиҜҒзӯ–з•Ҙпјӣе…¶ж¬ЎпјҢеҜ№еҪ»еә•еҗҰе®ҡжҖқи·Ҝзҡ„еӣһеә”пјӣйҡҸеҗҺпјҢи®әиҜҒ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дёҚе…·еӨҮвҖңз§ҒдәәжҖ§вҖқзү№еҫҒпјӣжңҖеҗҺпјҢеҜ№ж–Үз« еҶ…е®№иҝӣиЎҢжҖ»з»“пјҢ并еұ•жңӣи§ЈеҶі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й—®йўҳзҡ„еҸҜиғҪж–№жЎҲгҖӮ
дәҢпјҺ еҪ»еә•еҗҰе®ҡ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пјҡжҲ‘们е°ұжҳҜ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
дё№е°јзү№жҳҜ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еқҡе®ҡеҸҚеҜ№иҖ…пјҢд»–и®Өдёә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е’ҢвҖңжҙ»еҠӣи®әвҖқдёҖж ·е®Ңе…ЁжҳҜдёҖз§Қдәәдёәжһ„йҖ зҡ„е№»иұЎгҖӮжҙ»еҠӣи®әиҖ…еЈ°з§°з”ҹе‘ҪдҪ“еҶ…жңүдёҖз§Қзү№ж®Ҡзҡ„зү©иҙЁпјҢеҚівҖңжҙ»еҠӣвҖқпјҢиҝҷз§Қзү№ж®Ҡзҡ„йқһзү©иҙЁзҡ„еӣ зҙ ж”Ҝй…ҚзқҖз”ҹзү©дҪ“зҡ„жҙ»еҠЁпјҢ并дҪҝеҫ—з”ҹе‘ҪдҪ“еҢәеҲ«дәҺйқһз”ҹе‘ҪдҪ“гҖӮ [6]дҪҶиҝҷз§Қи§ӮзӮ№еңЁдәҢеҚҒдёҖдё–зәӘ被科еӯҰ家еҗҰе®ҡпјҡз”ҹзү©дҪ“еҶ…дёҚеӯҳеңЁвҖңжҙ»еҠӣвҖқиҝҷдёҖзү©иҙЁпјҢдёҚиҝҮжҳҜдёҖз§Қе№»иұЎгҖӮдё№е°јзү№еҖҹзұ»жҜ”иЎЁжҳҺ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д№ҹжҳҜз§Қе№»иұЎгҖӮ [7] д»–и®ӨдёәеҜ№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вҖң第дёҖдәәз§°дё»и§ӮжҖ§вҖқзҡ„йў„и®ҫеә”иҜҘиў«еҗҰе®ҡпјҢвҖңиҝңз«ҜеҲәжҝҖиҫ“е…Ҙ-зҘһз»Ҹе…ғж”ҫз”ө-з”ҹзү©еҸҚеә”вҖқйғҪжҳҜвҖң第дёүдәәз§°вҖқзҺ°иұЎпјҢеӣ иҖҢеҸҜд»Ҙ被科еӯҰзҡ„ж–№жі•иҝӣиЎҢз ”з©¶гҖӮеӨ§и„‘е°ұеҰӮеҗҢдёҖеҸ°еҠҹиғҪејәеӨ§зҡ„и®Ўз®—жңәеҷЁпјҢж„ҸиҜҶеҲҷжҳҜжңәеҷЁдёӯзҡ„дёҖдёӘиҷҡжӢҹе…ғзҙ иҖҢжІЎжңүе®һеңЁжҖ§гҖӮ
еҰӮжһңе°Ҷж„ҹеҸ—иҙЁи§Ҷдёәиў«зҘһз»Ҹзі»з»ҹдёӯжҹҗдәӣжҙ»еҠЁжүҖдҫӢзӨәеҢ–пјҲиҖҢйқһиў«иЎЁеҫҒпјүзҡ„еҶ…еңЁеұһжҖ§пјҢйӮЈд№Ҳе®ғеңЁи®ӨзҹҘзі»з»ҹдёӯе°ұжІЎжңүдҪҚзҪ®гҖӮвҖңжҲ‘们зҡ„еҜ№иҺ·еҫ—зҡ„ж„ҹеҸ—иҙЁеҶ…зңҒжҳҜжңүж„Ҹд№үзҡ„пјҢеӣ жӯӨж„ҹеҸ—иҙЁеҝ…然еӯҳеңЁвҖқпјҢжҚўиЁҖд№ӢпјҢжҲ‘们йҖҡиҝҮд»ҺеҝғжҷәеҶ…е®№пјҲmental contentпјүдёӯжҠҪиұЎеҮәдёҖдәӣзү№еҫҒпјҢеҚіе°ҶеҶ…йғЁиЎЁеҫҒзҡ„еҜ№иұЎжҰӮеҝөеҢ–пјҢ并е°Ҷд№ӢеҪ’иөӢдёәжҹҗз§ҚзІҫзҘһжҲ–й¬јйӯӮзҡ„зү©иҙЁгҖӮжҜ”еҰӮйўңиүІи§Ҷи§үжҳҜз”ұдёҖдёӘеӨҚжқӮзҡ„дҝЎжҒҜеӨ„зҗҶзі»з»ҹе®ҢжҲҗпјҢ并е®Ңе…ЁжҳҜеңЁж”ҫз”өеәҸеҲ—дёӯиҝӣиЎҢзҡ„пјҢиүІеҪ©з”ұж”ҫз”өеәҸеҲ—дёӯзҡ„зү©зҗҶжЁЎејҸзҡ„е·®ејӮвҖңиЎЁеҫҒвҖқпјҢеӣ иҖҢиҝҷдәӣе·®ејӮжң¬иә«е№¶йқһиүІеҪ©зҡ„е·®ејӮгҖӮ [8]еӣ жӯӨпјҢжҲ‘д»¬ж №жң¬ж— жі•д»ҘеҜ№иұЎеҢ–зҡ„ж–№ејҸдҪ“йӘҢеҲ°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пјҢиҖҢеҸӘдёҚиҝҮжҳҜеңЁеӨ–йғЁдё–з•ҢдёӯеҜ»жүҫзҡ„вҖңзұ»жҜ”вҖқгҖӮ
ж №жҚ®дё№е°јзү№зҡ„ж„ҸиҜҶзҗҶи®әпјҢж„ҸиҜҶдёҚиҝҮжҳҜдәәзҡ„вҖңзҘһз»Ҹеӣһи·Ҝдёӯзҡ„еҖҫеҗ‘вҖқз»„еҗҲд№ӢеҗҺзҡ„дә§зү©пјҢд»–е°Ҷдәәзұ»йҒҮеҲ°еҚұйҷ©ж—¶зҡ„вҖңжҒҗж…Ңж„ҹвҖқ [9]и§Ҷдёәж №жӨҚдәҺжҲ‘们зҘһз»Ҹзі»з»ҹдёӯзҡ„вҖңйҒҝйҷ©еҖҫеҗ‘вҖқпјҢиҝҷз§ҚеҖҫеҗ‘еӨ„дәҺиҝӣеҢ–зҡ„йңҖиҰҒиў«дҝқз•ҷеңЁжҲ‘们зҡ„еҹәеӣ д№ӢдёӯгҖӮжҜ”еҰӮеңЁеҠЁзү©еӣӯдёӯзңӢи§ҒеҮ¶зҢӣзҡ„еҠЁзү©ж—¶пјҢеҚідҪҝзҹҘйҒ“е®ғ们дёҚе…үиў«е…үеңЁйҖҡз”өзҡ„й“Ғз¬јеӯҗйҮҢпјҢз¬јеӯҗеӨ–иҝҳжңүеҫҲй•ҝзҡ„йёҝжІҹпјҢеӣ иҖҢе®Ңе…ЁжІЎжңүдјӨдәәзҡ„еҸҜиғҪпјҢдәә们иҝҳжҳҜдјҡж„ҹеҲ°вҖңжҒҗж…ҢвҖқпјҢиҝҷйғҪжҳҜеӣ дёәвҖңжҒҗж…Ңж„ҹвҖқжҳҜзҘһз»Ҹзі»з»ҹдёӯзҡ„вҖңеҖҫеҗ‘вҖқпјҢжңүеҲ©дәҺйҮҠж”ҫиӮҫдёҠи…әзҙ её®еҠ©жҲ‘们иҝӣиЎҢеҸҚеҮ»жҲ–йҖғи·‘пјҢиҖҢ并йқһеҸӘжҳҜдёҖз§ҚжҠҪиұЎзҡ„дё»и§ӮдҪ“йӘҢ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Ҷ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и§ҶдёәдёҖз§Қе®һеңЁзҡ„ж„ҸиҜҶеұһжҖ§дёҚиҝҮжҳҜдёҖз§ҚзҗҶи®әй”ҷи§үпјҢеҫ—дёҚеҲ°зҘһз»Ҹ科еӯҰдёҠзҡ„ж”ҜжҢҒгҖӮ
жІҝзқҖвҖңеҗҰе®ҡж„ҹеҸ—жҖ§зҡ„е®һеңЁжҖ§вҖқзҡ„жҖқи·ҜпјҢдё№е°јзү№и®Өдёә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зҡ„е®Ңе…Ёж— ж— йңҖи®ҫпјҢз”ұдәҺ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и®ҫжғідёҚиҝҮжҳҜз§ҚзҗҶи®әе№»иұЎпјҢжҲ‘们дёҺйӮЈдәӣзјәе°‘з–јз—ӣгҖҒйҘҘйҘҝе’ҢжҒҗж…Ңиҝҷдәӣ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еғөе°ёд№Ӣй—ҙжІЎжңүеҢәеҲ«пјҢеӣ иҖҢжҲ‘们е°ұжҳҜжҹҘе°”иҺ«ж–Ҝи®ҫжғізҡ„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гҖӮдё№е°јзү№е’ҢжҹҘе°”иҺ«ж–Ҝзҡ„еҲҶжӯ§еҫҲеӨ§зЁӢеәҰдёҠжқҘиҮӘдёӨдҪҚе“ІеӯҰ家жүҖж”ҜжҢҒзҡ„е“ІеӯҰз«ӢеңәдёҚеҗҢпјҢеүҚиҖ…жҳҜе…ёеһӢзҡ„зү©зҗҶжіЁж„ҸиҖ…пјҢеҗҺиҖ…еҲҷжҳҜиҮӘ然主д№үзҡ„дәҢе…ғи®әпјҲжҲ–жіӣеҝғи®әпјүиҖ…гҖӮдҪҶжҲ‘еңЁиҝҷйҮҢдёҚжү“з®—ж·ұе…ҘжҺўз©¶еҲҶжӯ§дә§з”ҹзҡ„еҺҹеӣ пјҢиҖҢеҸӘе…іжіЁдё№е°јзү№з”ЁдәҺеҗҰе®ҡ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зҡ„и®әиҜҒгҖӮ
и®ҫжғідёҖз§ҚвҖңй«ҳзә§еғөе°ёвҖқпјҢе®ғеңЁеӨ–жҳҫиЎҢдёәдёҠдёҺжҷ®йҖҡзҡ„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дёҖж‘ёдёҖж · [10]пјҢдҪҶеҚҙиғҪвҖңиһәж—ӢиҲ¬ж— йҷҗеҗ‘дёҠеҸҚиә«вҖқпјҲindefinite upward spiral of reflexivityпјүең°зӣ‘жҺ§иҮӘе·ұзҡ„жҙ»еҠЁпјҢеҢ…жӢ¬иҮӘе·ұвҖңеҝғзҒөвҖқзҡ„еҶ…еңЁжҙ»еҠЁгҖӮйҖҡиҝҮиҮӘжҲ‘зӣ‘жҺ§пјҢе®ғпјҲж— ж„ҸиҜҶең°пјүжӢҘжңүе…ідәҺе®ғзҡ„вҖңдҪҺйҳ¶зҠ¶жҖҒвҖқзҡ„еҶ…еңЁдәҺвҖңеҝғзҒөвҖқзҡ„вҖңй«ҳйҳ¶зҠ¶жҖҒвҖқгҖӮ [11]з”ұдәҺвҖңй«ҳйҳ¶еғөе°ёвҖқе…·жңүдёҖдёӘе…Ғи®ёж— йҷҗйҖ’еҪ’зҡ„вҖңиҮӘжҲ‘иЎЁеҫҒвҖқпјҲself-representationпјүзі»з»ҹпјҢе®ғиғҪе…·жңүжҜ”вҖңжҷ®йҖҡеғөе°ёвҖқжӣҙдёәеӨҚжқӮзҡ„иЎҢдёәпјҢеҰӮжҠҘе‘ҠиҮӘе·ұзҡ„еҶ…еңЁзҠ¶жҖҒгҖӮ [12]еңЁдё№е°јзү№зңӢжқҘпјҢи®ҫжғідёӯвҖңй«ҳйҳ¶еғөе°ёвҖқеҮӯеҖҹжһҒе…¶еӨҚжқӮзҡ„и®ӨзҹҘз»“жһ„дёҚд»…е…·жңүеҶ…зңҒиғҪеҠӣпјҢиҖҢдё”иғҪеӨҹвҖңеҮҶзЎ®ең°вҖқжҠҘе‘ҠеҶ…еңЁеҝғзҗҶзҠ¶жҖҒпјҢеӣ дёәе®ғ们иғҪеҜ№иҝҷдәӣзҠ¶жҖҒиҝӣиЎҢзӢ¬з«Ӣең°еҸҚжҖқгҖӮжӯӨж—¶зҡ„вҖңй«ҳйҳ¶еғөе°ёвҖқе’ҢжҲ‘们已з»ҸжІЎжңүеҢәеҲ«дәҶгҖӮи®ҫжғіиҝҷж ·дёҖз§Қжғ…еҶөпјҢе°ҸжҳҺдёәдәҶжЈҖжөӢд»–зҡ„жңӢеҸӢжҳҜдёҚжҳҜеғөе°ёпјҢиҰҒжұӮе®ғеңЁи„‘жө·дёӯи§ЈеҶідёҖдёӘй—®йўҳпјҢ并且解йҮҠе®ғеҰӮдҪ•еҒҡеҲ°зҡ„гҖӮ [13]вҖңеҘ№вҖқжҖқйҮҸзүҮеҲ»еҗҺеӣһзӯ”дәҶй—®йўҳпјҢ并表зӨәиҮӘе·ұеҲҡеҲҡеңЁвҖңеҝғйҮҢвҖқи§ЈеҶідәҶй—®йўҳпјҢ并且вҖңзҹҘйҒ“вҖқиҝҷжҳҜе®ғжғіиҜҙзҡ„гҖӮдҪҶжҳҜеҰӮжһңе®ғиҝӣдёҖжӯҘеҸҚжҖқпјҢе°ұеҸҜиғҪдјҡвҖңзҹҘйҒ“вҖқиҮӘе·ұдёҚзҹҘйҒ“дёәд»Җд№Ҳеӣһзӯ”жҳҜиҝҷж ·дёҖдёӘ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еҸҰдёҖдёӘпјҢеӣ дёәдәӢе®һдёҠе®ғ并дёҚе…·еӨҮзҡ„еҜ№еҶ…еңЁзҠ¶жҖҒзҡ„вҖңи§үзҹҘвҖқиғҪеҠӣгҖӮдёҚиҝҮдҪ и¶ҠжҳҜй—®е®ғзҹҘйҒ“е’ҢдёҚзҹҘйҒ“иҮӘе·ұеңЁиҜҙд»Җд№ҲпјҢе®ғе°ұдјҡи¶ҠжҳҜйҖҡиҝҮпјҲж„ҸиҜҶзҡ„пјүй«ҳйҳ¶еҸҚжҖқжқҘиҝӣиЎҢеӣһзӯ”гҖӮиҝҷж ·зңӢжқҘпјҢе°ҸжҳҺзҡ„жңӢеҸӢжҳҜдёҖдёӘж— ж„ҸиҜҶзҡ„пјҢеҚҙжңүзқҖй«ҳйҳ¶жҖқз»ҙе’Ңдё»и§Ӯж„ҸиҜҶз»ҸйӘҢзҡ„вҖңй«ҳйҳ¶еғөе°ёвҖқпјҢе®ғз”ҡиҮідјҡи§үеҫ—иҮӘе·ұжҳҜжңүж„ҸиҜҶзҡ„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ҸжҳҺзҡ„вҖңеғөе°ёвҖқжңӢеҸӢдёҺжҲ‘们没жңүд»Җд№ҲеҢәеҲ«пјҢжҲ‘们е°ұжҳҜй«ҳйҳ¶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гҖӮ
дёүпјҺеӣһеә”дё№е°јзү№пјҡжҲ‘们жҜ”вҖңеғөе°ёвҖқеӨҡеҮәзҡ„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
дҪңдёәвҖңж„ҸиҜҶеӣ°йҡҫвҖқй—®йўҳзҡ„дё»иҰҒж”ҜжҢҒиҖ…пјҢжҹҘе°”иҺ«ж–ҜеҜ№дё№е°јзү№еҸ–ж¶Ҳ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еҒҡжі•иҝӣиЎҢдәҶеӣһеә”гҖӮд»–и®ӨдёәзҘһз»Ҹзі»з»ҹзҡ„еҠҹиғҪе®һзҺ°иҷҪ然已з»ҸиҜҙжҳҺдәҶеҫҲеӨҡй—®йўҳпјҢдҪҶж— жі•еӣһзӯ”еңЁеҠҹиғҪзҡ„е®һзҺ°иҝҮзЁӢдёӯдёәд»Җд№ҲдјҡеёҰжңүвҖңзҺ°иұЎз»ҸйӘҢвҖқиҝҷдёҖзү№ж®Ҡзҡ„з»ҸйӘҢзҠ¶жҖҒгҖӮ并且пјҢз”Ёз”ҹзҗҶеҠҹиғҪзҡ„е®һзҺ°дјҙйҡҸзқҖвҖңз”ҹе‘ҪвҖқиҜҙжҳҺвҖңжҙ»еҠӣи®әвҖқдёҚеӯҳеңЁзҡ„ж–№жі•пјҢдёҺзҘһз»Ҹзі»з»ҹеҠҹиғҪзҡ„е®һзҺ°иҝӣиЎҢзұ»жҜ”пјҢдёҚиғҪиҜҙжҳҺ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дёҚеӯҳеңЁгҖӮеӣ дёәжҺ’йҷӨвҖңжҙ»еҠӣи®әвҖқзҡ„и®әиҜҒйңҖиҰҒи§ЈйҮҠзҡ„жҳҜпјҢеҰӮдҪ•еңЁдёҚеј•е…ҘвҖңжҙ»еҠӣвҖқзҡ„жғ…еҶөдёӢпјҢеҜ№з”ҹзү©зҡ„ж–°йҷҲд»Ји°ўзӯүй—®йўҳиҝӣиЎҢи§ЈйҮҠпјҢиҝҷдәӣи§ЈйҮҠжң¬иә«е°ұеёҰжңүвҖңеҠҹиғҪжҖ§вҖқзҡ„еұһжҖ§пјҢ并且йғҪеӨ„дәҺзү©зҗҶеұӮйқўиҝҷдёҖжң¬дҪ“и®әйўҶеҹҹгҖӮдҪҶжҳҜеҜ№ж„ҸиҜҶзҡ„й—®йўҳзҡ„еҲҶжһҗе°ұдёҚжҳҜз®ҖеҚ•зҡ„еҠҹиғҪжҖ§й—®йўҳпјҢзү©зҗҶеӯҰзҡ„и§ЈйҮҠж— жі•д»ЈжӣҝжҲ‘们еҜ№дәҺзәўиүІзҺ«з‘°иҠұзҡ„еҺҹе§Ӣз»ҸйӘҢпјҢзҗҶи§ЈзәўиүІеңЁи§ҶзҪ‘иҶңдёҠзҡ„е‘ҲзҺ°еҺҹзҗҶе’ҢдәІзңјзңӢи§ҒзәўиүІд№ҹдёҚжҳҜеҗҢдёҖз§Қз»ҸйӘҢгҖӮеҗҢж—¶пјҢвҖңж„ҹеҸ—иҙЁ-зҘһз»Ҹзі»з»ҹвҖқжҳҜеҗҰеӨ„дәҺеҗҢдёҖжң¬дҪ“и®әдёӯйңҖиҰҒеҫ—еҲ°и®әиҜҒзҡ„пјҢиҖҢдёҚиғҪдҪңдёәеүҚжҸҗгҖӮдё№е°јзү№еқҡжҢҒеңЁвҖңжҙ»еҠӣ-з”ҹзҗҶеҠҹиғҪвҖқдёҺвҖңж„ҹеҸ—иҙЁ-зҘһз»Ҹзі»з»ҹвҖқд№Ӣй—ҙзҡ„зұ»жҜ”пјҢ并没жңүз»ҷеҮәиҜҙжҳҺиҝҷз§Қзұ»жҜ”зҡ„еҗҲзҗҶжҖ§зҡ„иҝӣдёҖжӯҘзҡ„и®әиҜҒ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ҹҘе°”иҺ«ж–Ҝи®Өдёәдё№е°јзү№еңЁеҪўејҸдёҠдҝқз•ҷ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еҒҡжі•жҳҜдёҚзҺ°е®һзҡ„пјҢвҖңпјҲзҺ°иұЎпјүз»ҸйӘҢдёҚеҸҜиғҪеҰӮеҗҢвҖҳжҙ»еҠӣи®әвҖҷдёҖиҲ¬пјҢиғҪиў«ж–°еҮәзҺ°зҡ„зҗҶи®әжүҖжӣҝд»ЈвҖқгҖӮ [14]
дё№е°јзү№и®Өдёә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еҸӘжҳҜйӮЈдәӣзҘһз»Ҹзі»з»ҹдёӯзҡ„еӨҚжқӮеҖҫеҗ‘пјҢж„ҹеҸ—иҙЁжҳҜвҖңвҖҰдҪ еҝғзӣ®дёӯдёҖдёӘз§ҒеҜҶзҡ„гҖҒдёҚеҸҜиЁҖиҜҙзҡ„дёңиҘҝжҲ–е…¶д»–дёңиҘҝпјҢеҰӮдёҖдёӘз§ҒеҜҶзҡ„зІүзәўиүІзҡ„йҳҙеҪұвҖқпјҢдҪҶжҳҜвҖңеҸӘжҳҜдҪ зңӢжқҘзҡ„ж ·еӯҗ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дәӢе®һзҡ„ж ·еӯҗвҖқгҖӮдёҳеҘҮе…°еҫ·пјҲChurchlandпјүд№ҹи®ӨеҗҢ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зҡ„вҖңеҸҜжғіиұЎжҖ§вҖқе®һиҙЁдёҠжҳҜдёҖз§ҚеҹәдәҺвҖңеёёиҜҶеҝғзҗҶеӯҰвҖқзҡ„иҜҜи§ЈпјҢжҳҜз”ұдәҺдәә们еҜ№зҘһз»Ҹ科еӯҰзҡ„е…·дҪ“жңәеҲ¶зҡ„дёҚдәҶи§ЈиҖҢдә§з”ҹзҡ„й”ҷиҜҜзҡ„зӣҙи§үгҖӮйҡҸзқҖ科еӯҰзҡ„иҝӣеұ•пјҢжҲ‘们иғҪеӨҹе®һзҺ°еҜ№дәәи„‘дёӯзҡ„еӨҚжқӮжңәеҲ¶зҡ„е……еҲҶиҜҙжҳҺпјҢиҖҢиҝҷз§ҚвҖңеҸҜжғіиұЎжҖ§вҖқд№ҹе°ұдёҚеӨҚеӯҳеңЁдәҶгҖӮ [15]дҪҶжҳҜпјҢ他们еҜ№дәҺ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з«ӢеңәпјҢйғҪжқҘиҮӘдәҺз ”з©¶дёӯжүҖйҮҮ用第дёүдәәз§°зҡ„е®ўи§Ӯи§Ҷи§’пјҢеҚіз§‘еӯҰз ”з©¶зҡ„ж–№жі•гҖӮд»ҘиҝҷдёҖж–№жі•еҫ—еҮә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дёҚжҳҜеҸҜеҶ…зңҒзҡ„зҺ°е®һпјҢеҰӮжһңе®ғеӯҳеңЁзҡ„иҜқпјҢд№ҹжҳҜйҖҡиҝҮвҖң第дёүдәәз§°вҖқ科еӯҰиҖҢдёҚжҳҜвҖң第дёҖдәәз§°вҖқи§ӮеҜҹеҸ‘зҺ°зҡ„з»“и®ә并дёҚи®©дәәж„ҹеҲ°ж„ҸеӨ–гҖӮиҷҪ然зӣ®еүҚжІЎжңүзҗҶз”ұиЎЁжҳҺпјҢз”Ёе®ўи§Ӯзҡ„科еӯҰз ”з©¶ж–№жі•з ”з©¶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ӯүеёҰжңүејәзғҲдё»и§ӮиүІеҪ©зҡ„ж„ҹеҸ—жҳҜдёҚеҸҜиЎҢзҡ„пјҲжңүеӨ§йҮҸ科еӯҰ家еңЁе°қиҜ•иҝҷйЎ№е·ҘдҪңпјүпјҢдҪҶдёҚиЎЁжҳҺ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жҳҜеҸҜд»Ҙж— е…ізҙ§иҰҒзҡ„пјҢеӣ иҖҢеҸҜд»Ҙиў«еҸ–ж¶ҲгҖӮжӯӨеӨ–пјҢз”Ёе®ўи§Ӯзҡ„ж–№жі•з ”з©¶з ”з©¶дё»и§ӮжҖ§й—®йўҳпјҢе’Ңй—®йўҳжң¬иә«жҳҜдё»и§Ӯзҡ„并дёҚеҶІзӘҒгҖӮеҜ№зҘһз»Ҹзі»з»ҹеҠҹиғҪзҡ„и§ЈйҮҠж—ўдёҚиғҪз©·е°Ҫж„ҹеҸ—з»ҸйӘҢзҡ„зҺ°иұЎзү№еҫҒпјҢд№ҹж— жі•дҪ“зҺ°дё»дҪ“еҜ№дәҺ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дҪ“йӘҢгҖӮеӣ жӯӨеңЁзӣҙи§үдёҠпјҢ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еҸ–ж¶ҲжҳҜдёҚиғҪиў«жҺҘеҸ—зҡ„гҖӮ
еңЁжҸҗеҮәвҖңжҲ‘们е°ұжҳҜвҖҳ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ҷвҖқиҝҷдёҖи®әж–ӯж—¶пјҢдё№е°јзү№е®Ңе…ЁжҳҜд»Һж„ҸиҜҶзҡ„еҠҹиғҪи§’еәҰеҜ№иҝӣиЎҢиҖғиҷ‘пјҢиҖҢжІЎжңүжіЁж„ҸеҲ°иҝҷдёҖжҖқжғіе®һйӘҢеңЁвҖңзҺ°иұЎеұӮйқўвҖқзҡ„е“ІеӯҰж„Ҹд№үгҖӮжҳҫ然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е°ҶдҪҝеҠҹиғҪдё»д№үйҷ·е…Ҙеӣ°еўғпјҢеӣ дёәеҜ№дәәеңЁеҠҹиғҪдёҠзҡ„жЁЎд»ҝеҫҲе®№жҳ“иў«е®һзҺ°пјҢз”ҡиҮіиғҪиў«е®һзҺ°зҡ„жӣҙеҘҪпјҢеңЁзғӯж°ҙеҷЁгҖҒеҶ°з®ұе’Ңи®Ўз®—еҷЁйғҪиғҪеңЁзјәд№Ҹ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жғ…еҶөдёӢеҫҲеҘҪең°е®ҢжҲҗе®ғ们зҡ„еҠҹиғҪгҖӮдҪҶжҳҜ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жҖқжғіе®һйӘҢзҡ„е®һиҙЁжҳҜиЎЁжҳҺж„ҸиҜҶйҡҸйҷ„дәҺзү©зҗҶзҠ¶жҖҒпјҢеҚҙдёҚиғҪиў«иҝҳеҺҹдёәзү©зҗҶиҝҮзЁӢгҖӮеӣ дёәдёҖдёӘеҸӘжңүвҖңеғөе°ёвҖқзҡ„дё–з•ҢдёҚдҪҶжҳҜеҸҜжғіиұЎзҡ„пјҢз”ҡиҮіиҝҗиҪ¬зҡ„еҫҲеҘҪпјҢдҪҶеңЁжң¬иҙЁдёҠдёҺжҲ‘们жүҖеӨ„зҡ„дё–з•ҢдёҚеҗҢгҖӮж„ҸиҜҶзҡ„вҖңдёҚеҸҜиҝҳеҺҹжҖ§вҖқиЎЁжҳҺжғіиұЎж„ҸиҜҶдёҚе®Ңе…ЁжҳҜзү©зҗҶиҝҮзЁӢпјҢеҚідҪҝиҝҷж ·еҸҜиғҪдҪҝеҫ—ж„ҸиҜҶиў«и§ҶдёәдёҖз§ҚвҖңеүҜзҺ°иұЎвҖқпјҢдҪҶиҝҷд№ҹж„Ҹе‘ізқҖжҲ‘们дёәд»Җд№Ҳжңү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жҲҗдёәдәҶдёҖдёӘвҖңйҡҫй—®йўҳвҖқгҖӮеӣ жӯӨпјҢиҮіе°‘еңЁзҺ°иұЎеұӮйқўдёҠпјҢжҲ‘们жҜ”еғөе°ёеӨҡеҮәдәҶ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пјҢеҰӮжһңдё№е°јзү№еқҡжҢҒеҗҰи®ӨиҝҷдёҖзӮ№пјҢд»–йңҖиҰҒжӯЈи§ҶвҖңе“ІеӯҰеғөе°ёвҖқеёҰжқҘзҡ„зҺ°иұЎеұӮйқўзҡ„й—®йўҳпјҢ并дёәд№ӢжҸҗдҫӣйҖӮеҪ“зҡ„и§ЈеҶіж–№жЎҲгҖӮ
еӣӣпјҺдёҚе…·еӨҮвҖңз§ҒдәәжҖ§вҖқзҡ„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и®әиҜҒ
дё№е°јзү№зҡ„еҲҶжһҗжһҒе…·жҙһи§ҒпјҢдҪҶд»–еңЁи®әиҜҒдёӯиҝҗз”ЁеӨ§йҮҸйҡҗе–»е’Ңзұ»жҜ”дҪңзҡ„еҶҷдҪңйЈҺж јпјҢдҪҝе…¶ж–Үз« еңЁеҜҢжңүеҗҜеҸ‘жҖ§зҡ„еҗҢж—¶пјҢзјәд№ҸеҜ№и®әиҜҒдёӯз»ҶиҠӮзҡ„вҖңжү“зЈЁвҖқпјҢиҝҷд№ҹдҪҝд»–зҡ„з«Ӣеңәж—¶еёёеҸ—еҲ°дәүи®®гҖӮжҲ‘们д»Һдё№е°јзү№зҡ„е·ҘдҪңдёӯеҫ—еҲ°дәҶдёҖдәӣжңүзӣҠзҡ„ж•ҷиҜІпјҢе…¶дёӯд№ӢдёҖе°ұжҳҜзӣҙжҺҘе…ЁйқўеҗҰе®ҡ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пјҢиҮіе°‘еңЁзӣ®еүҚзңӢжқҘжҳҜдёҚеҸҜиғҪе®ҢжҲҗзҡ„д»»еҠЎ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ңЁиҝҷдёҖиҠӮдёӯпјҢжҲ‘е°Ҷд»…еҜ№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е…¶дёӯ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зү№еҫҒвҖ”вҖ”вҖңз§ҒдәәжҖ§вҖқиҝӣиЎҢжҺўз©¶гҖӮеңЁжҲ‘зңӢжқҘпјҢиҜҘзү№еҫҒжҸӯзӨәдәҶ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й—®йўҳжҲҗдёәвҖңйҡҫй—®йўҳвҖқзҡ„еҺҹеӣ пјҡиҝҷдёҖзҺ°иұЎз»ҸйӘҢжҳҜеұһдәҺз§Ғдәәзҡ„гҖҒж— жі•д»Ҙе…¬е…ұзҡ„жүӢж®өиў«жЈҖжөӢжҲ–ж„ҹзҹҘзҡ„гҖӮжҜ”еҰӮжҲ‘еҗ¬и§ҒдёҖж®өвҖңжҠ–йҹізҘһжӣІвҖқпјҢжҲ‘жҲ–и®ёдјҡзҡұиө·зңүеӨҙжҲ–иҖ…жҚӮдҪҸиҖіжңөпјҢжӯӨж—¶з”ЁfMRIеҜ№жҲ‘зҡ„и„‘еҢәиҝӣиЎҢжү«жҸҸж—¶пјҢд№ҹеҸҜиғҪдјҡеҸ‘зҺ°иҙҹйқўжғ…ж„ҹзҡ„и„‘еҢәејӮеёёжҙ»и·ғпјҢдҪҶжҲ‘дҪ“йӘҢеҲ°зҡ„йӮЈз§ҚвҖңеҺҢжҒ¶зҡ„вҖқж„ҹеҸ—зҠ¶жҖҒпјҢеҚҙжІЎжі•иў«д»»дҪ•жүӢж®өжЈҖжөӢеҲ°гҖӮеӣ жӯӨпјҢ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иў«и®Өдёәе…·жңүвҖңз§ҒдәәжҖ§вҖқзү№еҫҒгҖӮеҰӮжһңиғҪеӨҹи®әиҜҒиҝҷдёҖи§ӮзӮ№жҳҜй”ҷиҜҜзҡ„пјҢйӮЈд№ҲеҜ№дәҺ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вҖңйҡҫй—®йўҳвҖқдјјд№ҺзҗҶи®әдёҠиғҪиў«иҪ¬еҢ–жҲҗиғҪ被科еӯҰжҠҖжңҜи§ЈеҶізҡ„йӮЈдёҖзұ»й—®йўҳгҖӮиҝҷж ·дёҖжқҘпјҢеӣ°жү°зқҖдәәе·ҘжҷәиғҪж„ҸиҜҶзҡ„вҖңйҡҫй—®йўҳвҖқз”ұдәҺ被被科жҠҖи§ЈеҶіиҖҢеҸҳжҲҗвҖңз®Җзӯ”й—®йўҳвҖқгҖӮжҺҘдёӢжқҘпјҢжҲ‘е°ҶеҖҹеҠ©еҝғзҒөе“ІеӯҰдёҺи®ӨзҹҘеҝғзҗҶеӯҰзҡ„з ”з©¶пјҢеҜ№дёҠиҝ°и§ӮзӮ№иҝӣиЎҢжҺўз©¶гҖӮ
йҖҡеёёжқҘиҜҙпјҢдёҖдёӘеёҰжңү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зҡ„ж„ҸиҜҶжҙ»еҠЁеҫҖеҫҖз”ұеӣӣдёӘйғЁеҲҶз»„жҲҗпјҡ第дёҖпјҢдёҖдёӘж„ҸиҜҶжҙ»еҠЁдёӯзҡ„и®ӨзҹҘиҖ…Sпјӣ第дәҢпјҢзү№е®ҡзҡ„ж„ҸиҜҶжҙ»еҠЁIпјӣ第дёүпјҢж„ҸиҜҶжҙ»еҠЁжүҖжҢҮеҗ‘зҡ„еҜ№иұЎOпјӣ第еӣӣпјҢж„ҸиҜҶжҙ»еҠЁдёӯзҡ„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QгҖӮз”ЁдёҖдёӘз»Ҹе…ёзҡ„дҫӢеӯҗеҸҜд»ҘжӣҙеҘҪзҡ„иҜҙжҳҺдёүиҖ…зҡ„е…ізі»пјҡ
жҲ‘пјҲSпјүжӯЈзңӢзқҖпјҲIпјүдёҖзүҮз»ҝиүІзҡ„(Q)ж ‘еҸ¶(O)
SгҖҒIгҖҒQе’ҢOд№Ӣй—ҙе…ізі»жһ„жҲҗдәҶдёҚеҗҢзҡ„ж„ҸиҜҶжҙ»еҠЁгҖӮйҰ–е…ҲпјҢSеңЁеҜ№Iзҡ„жіЁж„ҸдёӯвҖңеҮёжҳҫвҖқиҮӘиә«гҖӮвҖңжіЁж„ҸвҖқпјҲвҖңattentionвҖқпјүжҳҜж„ҸиҜҶзҡ„йҖүжӢ©жҙ»еҠЁпјҢж„ҸиҜҶйҖүжӢ©жҹҗдёҖдәӢзү©жҲ–дәӢ件е°ұж„Ҹе‘ізқҖвҖңжіЁж„ҸеҲ°вҖқпјҲattend toпјүдёҚеҗҢзҡ„еҜ№иұЎгҖӮ [16] вҖңеҮёжҳҫвҖқж„Ҹе‘ізқҖиҝҷдёҖдәӢзү©жҲ–дәӢ件被ж„ҸиҜҶжҙ»еҠЁдёӯзҡ„и®ӨзҹҘиҖ…жӯЈеңЁи§үзҹҘеҲ°пјҲaware ofпјүиҮӘе·ұзҡ„жҹҗз§Қж„ҸиҜҶз»ҸйӘҢгҖӮ [17]д№ҹе°ұжҳҜиҜҙпјҢж„ҸиҜҶIе’Ңи§үзҹҘеҲ°ж„ҸиҜҶIжҳҜдёӨз§ҚдёҚеҗҢеұӮж¬Ўзҡ„ж„ҸиҜҶжҙ»еҠЁпјҢеүҚиҖ…еҸӘиҰҒжұӮе…ідәҺвҖңзңӢ(I)вҖқзҡ„ж„ҸиҜҶжҙ»еҠЁпјҢеҗҺиҖ…еҲҷиҰҒжұӮи®ӨзҹҘиҖ…Sи§үзҹҘеҲ°вҖңзңӢвҖқиҝҷдёҖж„ҸиҜҶжҙ»еҠЁпјҢд№ҹеҚіеҜ№дёҖз§Қж„ҸиҜҶжҙ»еҠЁзҡ„жіЁж„ҸгҖӮеңЁиҝҷдёҖвҖңеҜ№жҹҗдёҖж„ҸиҜҶжҙ»еҠЁзҡ„жіЁж„ҸвҖқпјҲз®Җз§°вҖңA-T-XвҖқпјҢе…¶дёӯXдёәжіЁж„Ҹзҡ„еҜ№иұЎпјүдёӯпјҢи®ӨзҹҘиҖ…Sиў«вҖңеҮёжҳҫвҖқдёҺж„ҸиҜҶжҙ»еҠЁдёӯ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ёҖдёӘеҢәеҲ«дәҺIзҡ„ж„ҸиҜҶжҙ»еҠЁI*пјҢз»ҸиҝҮA-T-0еҪўжҲҗдәҶгҖӮI*иЎЁжҳҺеӯҳеңЁдёҖдёӘж„ҸиҜҶжҙ»еҠЁзҡ„и®ӨзҹҘиҖ…пјҢеҚіжӯЈеңЁвҖңзңӢвҖқзҡ„SгҖӮе…¶ж¬ЎпјҢйЎәзқҖиҝҷдёҖжҖқи·ҜпјҢеҜ№Iзҡ„е…іжіЁд№ҹе°ҶеҮёжҳҫOгҖӮжҚўиЁҖд№ӢпјҢOйҖҡиҝҮSеҜ№Iзҡ„жіЁж„ҸпјҢеҚіA-T-0иҖҢеҪўжҲҗж–°зҡ„ж„ҸиҜҶжҙ»еҠЁI#вҖ”вҖ”SжіЁж„ҸеҲ°вҖңзңӢвҖқзҡ„еҜ№иұЎжҳҜвҖңж ‘еҸ¶вҖқгҖӮзӣ®еүҚдёәжӯўпјҢжҲ‘们已з»ҸеҲҶжһҗеҮәдёүз§ҚдёҚеҗҢзҡ„ж„ҸиҜҶжҙ»еҠЁпјҢеҲҶеҲ«жҳҜвҖңзңӢвҖқпјҲIпјүгҖҒвҖңи§үзҹҘеҲ°и®ӨзҹҘдё»дҪ“SвҖқпјҲI*пјүд»ҘеҸҠвҖңи§үзҹҘеҲ°зңӢзҡ„еҜ№иұЎOвҖқпјҲI#пјү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жҲ‘们д»Қ然зјәд№ҸеҜ№вҖңз»ҝиүІзҡ„вҖқиҝҷдёҖ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Qзҡ„и§ЈйҮҠгҖӮ
дёҖдёӘеҸҜиЎҢзҡ„и§ЈйҮҠжҳҜQеңЁI#дёӯиў«жіЁж„ҸеҲ°пјҢеӣ дёәпјҲеңЁи®ӨзҹҘиғҪеҠӣжӯЈеёёзҡ„жғ…еҶөдёӢпјүеҸӘжңүеҜ№дәҺзү№е®ҡеҜ№иұЎзҡ„жіЁж„ҸпјҢжүҚиғҪдә§з”ҹзұ»дјјвҖңз»ҝиүІзҡ„вҖқиҝҷж ·зҡ„ж„ҹеҸ—з»ҸйӘҢгҖӮеҗҢж—¶пјҢIеҜ№Qд№ҹжҳҜеҝ…дёҚеҸҜе°‘пјҢжҲ‘д»¬ж— жі•жғіеғҸеҰӮжһңдёҚйҖҡиҝҮвҖңзңӢпјҲIпјүвҖқпјҢвҖңз»ҝиүІпјҲQпјүвҖқзҡ„иҺ·еҫ—жҳҜеҰӮдҪ•еҸҜиғҪзҡ„гҖӮдҪҶжҳҜпјҢI*пјҲеҚіи§үзҹҘеҲ°и®ӨзҹҘдё»дҪ“SпјүеҜ№дәҺQдјјд№Һж— е…ізҙ§иҰҒпјҢеӣ дёәдәә们时常вҖңеҝҳжҲ‘вҖқең°еҒҡжҹҗдәӣдәӢжғ…пјҢжҜ”еҰӮеңЁзңӢдёҖеңәжғҠеҝғеҠЁйӯ„зҡ„еҠЁдҪңз”өеҪұж—¶пјҢи§Ӯдј—ж—¶еёёе®Ңе…ЁжҠ•е…ҘеңәжҷҜд№ӢдёӯпјҢиҖҢеҝҳи®°дәҶйӮЈдәӣеңәжҷҜдёҚиҝҮжҳҜиҮӘе·ұжӯЈеңЁзңӢзҡ„з”өеҪұжғ…иҠӮпјҢжӯӨж—¶жӢҘжңүвҖңжғҠеҝғеҠЁйӯ„вҖқзҡ„ж„ҹеҸ—Qе®Ңе…Ёж— йңҖжӢҘжңүжіЁж„ҸеҲ°дё»дҪ“пјҲA-T-Sпјүзҡ„ж„ҸиҜҶжҙ»еҠЁI*гҖӮ [18]еӣ жӯӨпјҢжҲ‘们еҸҜд»Ҙеҫ—еҮәиҝҷж ·дёҖдёӘз»“и®әпјҡQеңЁI#дёӯиў«жіЁж„ҸеҲ°пјҢеӣ иҖҢеұһдәҺI#зҡ„дёҖйғЁеҲҶгҖӮ
SжӢҘжңү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Qж„Ҹе‘ізқҖиў«Qж— жі•иў«Sд»ҘеӨ–зҡ„дёӘдҪ“жүҖж„ҹзҹҘзҡ„вҖңз§ҒдәәжҖ§вҖқпјҢдё”зјәд№ҸеҸҜиў«е…¬е…ұжЈҖйӘҢзҡ„йҖ”еҫ„гҖӮдҪҶж №жҚ®дёҠйқўзҡ„жҸҸиҝ°пјҢQеұһдәҺI#зҡ„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иҝҷжҳҜеҗҰж„Ҹе‘ізқҖSжӢҘжңүI#е°ұзӯүеҗҢдәҺжӢҘжңүQе‘ўпјҹеҰӮжһңдәӢе®һеҰӮжӯӨпјҢQдҫҝдјҡз”ұдәҺI#еҸҜиў«е…¬е…ұжЈҖйӘҢпјҢд»ҺиҖҢд№ҹе…·еӨҮеҸҜжЈҖйӘҢзҡ„жқЎд»¶гҖӮеӣ дёәI#жҳҜвҖңи§үзҹҘеҲ°еҜ№иұЎвҖқиҝҷдёҖж„ҸиҜҶжҙ»еҠЁпјҢиҖҢдәә们жҳҫ然еҸҜд»Ҙе…·еӨҮжЈҖжөӢдёҖдёӘи®ӨзҹҘиҖ…жҳҜеҗҰиғҪвҖңи§үзҹҘеҲ°жҹҗдёҖеҜ№иұЎзҡ„ж ҮеҮҶвҖқпјҢжҜ”еҰӮеңЁжЈҖжөӢи§ҶеҠӣж—¶пјҢеҢ»з”ҹдјҡиҰҒжұӮз—…дәәз”ЁжүӢеҠҝжҢҮзӨәеҮәи§ҶеҠӣиЎЁдёҠеӨ§е°ҸдёҚеҗҢзҡ„вҖңз¬ҰеҸ·EвҖқзҡ„жңқеҗ‘гҖӮеңЁиҝҷдёҖ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еҢ»з”ҹеҸҜд»Ҙж №жҚ®з—…дәәзҡ„жүӢеҠҝжҳҜеҗҰзңҹзҡ„и§үзҹҘеҲ°вҖңEвҖқзҡ„ж–№еҗ‘пјҢиҖҢеёҰжңүвҖңEвҖқзҡ„и§ҶеҠӣиЎЁе°ұжҳҜдёҖз§ҚI#зҡ„е…¬е…ұжЈҖйӘҢйҖ”еҫ„гҖӮжҚўиЁҖд№ӢпјҢQж— жі•иў«е…¬е…ұжЈҖйӘҢзҡ„иҰҒжұӮдәҺI#зҡ„е…¬е…ұеҸҜжЈҖйӘҢжҖ§зҡ„дәӢе®һеӯҳеңЁеј еҠӣпјҢйҷӨйқһSдёҺQиғҪеҮәзҺ°еңЁеҢәеҲ«дәҺI#зҡ„еҸҰдёҖдёӘж„ҸиҜҶжҙ»еҠЁI!дёӯпјҢдҪҝеҫ—QеҸӘиғҪйӮЈдёӘиў«Sж„ҹзҹҘеӣ иҖҢдёҚиғҪеңЁIпјҒдёӯеҸ—еҲ°жЈҖйӘҢпјҢеҗҰеҲҷвҖңж„ҹеҸ—иҙЁвҖқQе°ұ并дёҚе®һеңЁдәҺж„ҸиҜҶжҙ»еҠЁдёӯпјҢиҖҢдёҚиҝҮжҳҜдёҖз§Қе“ІеӯҰзҡ„вҖңе№»жғівҖқгҖӮиҝҷж ·дёҖжқҘпјҢжҲ‘们讨и®әзҡ„е…ій”®е°ұеҸҳжҲҗдәҶIпјҒиҝҷдёҖSеҜ№Qзҡ„вҖң第дёҖдәәз§°жқғеЁҒвҖқејҸзҡ„вҖңжӢҘжңүвҖқжҳҜеҗҰеҸҜиғҪпјҹжҺўз©¶йңҖиҰҒеӣһеҲ°Qзјәд№ҸеҸҜиў«е…¬е…ұжЈҖйӘҢзҡ„йҖ”еҫ„иҝҷдёҖжҖ§иҙЁ, еҚіQж— жі•иў«Sд№ӢеӨ–зҡ„и®ӨзҹҘиҖ…пјҲS1гҖҒS2вҖҰSnпјүжүҖжӢҘжңүгҖӮжүҖд»ҘпјҢI!еӯҳеңЁпјҢеҪ“дё”д»…еҪ“SжҳҜе”ҜдёҖеҸҜиғҪжӢҘжңүQзҡ„и®ӨзҹҘиҖ…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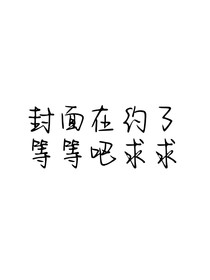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зјӘж–Ҝд№җеӣӯ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ҷ¶иҖ…зўҺж–ҮеҪ•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јӮе…Ҫ笔记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д№…жҹүзҘһиҜҶиҝ°дё–й—ҙзҷҫжҖ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зҝ”йң–пјҡж—§зҲұжӢҫиө·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