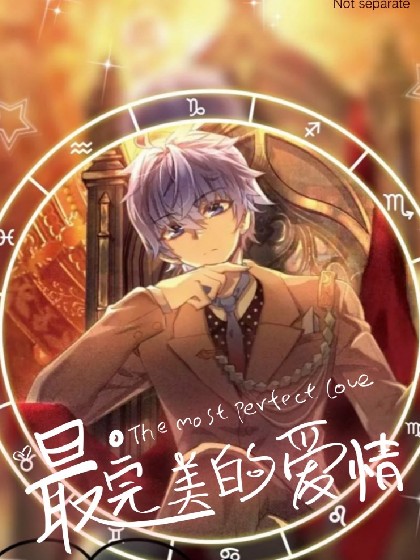国人暴动
周懿王辞世之后,其叔父姬辟方登基称王,史称孝王。孝王离世,懿王之嫡长子姬燮在众诸侯的鼎力支持下,终于重返王座,号为夷王。这一系列非传统的王位更迭,昭示着上层统治者间对于至高无上权力的明争暗斗已然白热化。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原本严谨有序的礼仪制度遭受严重冲击,天子对臣属的滥权行为层出不穷。例如,密康公因未能将三位绝色佳人进献给周王,竟在一载之内国破家亡。夷王之所以能重登大宝,全赖诸侯之力,然而此举却令其权威受损,地位岌岌可危。至此,周朝内部的政治纷争已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周夷王驾崩之后,其子姬胡即位,是为周厉王。为了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周厉王任命荣夷公为卿士,推行所谓的“专利”政策,将原本属于民众的山林湖泽收归天子所有,严禁百姓进入这些资源丰富的地区谋生。此举迅速引发了镐京城内国人的强烈不满,怨声四起,民愤难平。面对如此局面,忠心耿耿的大臣召穆公,亦称召公虎或邵公,忧心忡忡地上书谏言:“大王,百姓已不堪重负,街头巷尾尽是哀叹之声。”然而,周厉王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派遣卫巫严密监视民间言论,凡有敢于议论国事者,一律严惩不贷,甚至处以极刑。在这样的高压之下,镐京城内的气氛愈发凝重,人们即便相遇于街巷之间,也不敢轻易交谈,只能以眼神互相致意,随后便匆匆离去,此情此景,便是后世所说的“道路以目”。周厉王得知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反省,反而沾沾自喜地对召穆公说道:“我已成功遏制了那些非议之声,如今再无人敢妄加评论。”召穆公听罢,再次恳切进谏:“大王此举无异于用强权封堵百姓之口,犹如堵塞河流,一旦堤坝崩溃,必将引发滔天巨浪,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治理国家,应当如治水一般,采取疏导而非堵塞的方法,让民众能够自由发表意见,才是长治久安之道。”遗憾的是,周厉王对此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公元前841年,面对周厉王愈发残暴的统治,镐京的“国人”终于忍无可忍,纷纷拿起手中的棍棒与农具,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直逼王宫,誓要铲除这肆虐的暴君。周厉王闻讯大惊,急忙下令调集军队镇压。然而,臣子们面露难色,无奈地回禀道:“我朝向来以民为兵,国人即军士,军士亦为国人。如今国人已群起反抗,又何从调兵?”周厉王顿感孤立无援,只得携几名心腹匆匆逃离京城,沿着渭水河畔一路奔逃,直至抵达偏远之地彘城。在此后的十四年间,这位曾经威震四方的君主,终日生活在惶恐与病痛之中,直至公元前828年,带着无尽的悔恨与不甘,于彘城悄然离世。
国人攻入王宫,却未能寻得周厉王的踪迹,转而将目标锁定在了太子姬静身上。召穆公深知太子的重要性,果断将其藏匿于安全之地。愤怒的国人包围了召穆公府邸,要求交出太子。面对如此危局,召穆公毅然决定用自己的儿子替换了太子。《竹书纪年》中有记载:“国人捉拿召穆公之子并处死。”这一举动虽暂时平息了民众的怒火,在周定公与召穆公的极力劝说下,国人逐渐散去。然而,宗周却因此陷入了无主之境。为了稳定局势,周公与召公依据众贵族的提议,共同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重大决策由六卿集体商议决定。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历史上称为“共和”(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由共国国君共伯和代理天子之职,但这与《史记·周本纪》记载存在分歧)。关于“周召共和”与“共和行政”两种说法,学术界普遍倾向于后者。
国人暴动之后,周厉王被迫流亡异乡,再也无法重返那曾经辉煌的镐京。而太子静,这位年轻的储君,也因时局动荡未能即刻登基为王。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里,召穆公与周定公挺身而出,共同承担起国家的重担,代行王政。为了稳定民心,他们宣布更改年号为“共和”,这一时期被后世史家称为“周召共和”。
周朝,一个从原始部落向文明社会过渡而来的初生国度,其根基尚显脆弱。那些曾是部落成员的“国人”,成为了支撑周朝政权稳定的核心力量。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国人暴动”如同裂痕般撕开了贵族与平民之间原本脆弱的纽带,使得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遭受重创。这次暴动不仅动摇了王权的根基,更令周王室日渐式微,国家呈现出分崩离析之态。尽管周宣王曾试图力挽狂澜,短暂地振兴了周朝,但好景不长。周幽王继位后,其荒唐行径——烽火戏诸侯,最终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来了犬戎入侵,西周至此走向了终结。
关于国人暴动的性质,历史学家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将其视为平民的起义,有的则认为是工商业者的抗争,众说纷纭。然而,“平民”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当时特指自由民中的非特权阶层。在中国的先秦文献中,并未出现“平民”一词,而“国人”则频繁出现。《周礼·泉府》记载:“国人郊人其有司。”贾公彦对此解释道:“所谓‘国人’,是指居住在国都之内,即六乡之民。”由此可见,“国人”实际上指的是国都里的居民,而非泛指广大的民众。因此,这场暴动也可以被理解为国都内的民众对暴政的反抗行动。
中国通史广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水默之你是我的王妃
- 简介:新战士来袭,王默被陷害,成为了水王子的王妃,也恢复了记忆,她是和水王子有婚约的人!!
- 5.3万字5年前
- 斗罗大陆二之魔帝的爱情
- 简介:一样的剧情更加牛逼的技能不一样的人物,更加曲折的故事
- 2.5万字6年前
- 看似简单的第五游戏日常
- 简介:看似简单,实则……进去看看就吉岛惹!(手动滑稽)(注:只有双休日会更,有杰佣,遗照,黄占等同性cp不腐别看注意避雷!!!)
- 5.0万字6年前
- 徐总爱我就放过我
- 简介:陆艾清是一个小城市的白领由于一次车祸,穿梭于古今两代,因此与徐鑫开始了两段截然不同的恋爱
- 0.2万字5年前
- 丁小孩和小马宝莉的爱情
- 简介:丁程鑫和马嘉祺呀,还有刘耀文和宋亚轩
- 2.4万字5年前
- 繁星夏月的小铺子
- 简介:一个渣渣的封面教程,大佬勿喷。如果有什么不足请在评论区指出来。等我手机回来就去学PS教程。接单:校园,未完待续,头像,素锦,灵异,古风超渣。
- 2.4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