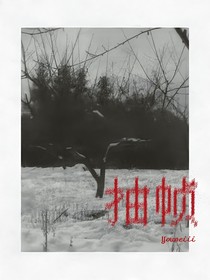无题
小公主折了枝海棠把玩,笑容忽然淡了几分:"二哥如今掌管太医院,成天泡在药庐里。前些日子还研发出什么...咳,说了你也不懂。"她突然把花枝往我发间一插,"倒是你,在北疆十年就光长个子不长心眼?连太子哥哥都认不出!"
"凌月..."我拽着小公主的杏色披帛,眼珠一转,"你太子哥哥如今...可有意中人?"话尾不自觉扬起,活像偷了腥的猫。
谢凌月正往嘴里塞玫瑰酥,闻言差点噎着。她拍着胸口猛灌了口茶,瞪圆了那双狐狸眼:"你莫不是..."突然噗嗤笑出声,"我太子哥哥啊,如今在宫外赁了宅子查案,连东宫都不回,哪有机会结识小娘子?"
她突然凑近,带着蜜饯的甜香:"前儿个李尚书家的小姐,故意把绣帕往他怀里扔。你猜怎么着?"小公主捏着嗓子学谢今朝冷峻的声调:"'姑娘,你的帕子掉了。女子当谨守闺训,岂可随意...'"话未说完,我们已笑作一团。
"他当真不明白人家心意?"我抹着笑出的泪花问。
"榆木脑袋!"谢凌月撇嘴,忽然神秘兮兮压低声音,"不过这次案子倒是稀奇,听说是醉仙楼的头牌清倌人..."她挠挠头,"好像是情杀?又说是暗杀?哎呀记不清了!"
我正想追问,她突然拽住我衣袖:"明日戌时我来寻你,带你看场好戏!"眼珠滴溜溜转,"对了,你有男装吗?"
"有倒是有..."我一脸茫然。
"成!"她击掌一笑,金镶玉镯子撞得清脆作响,"记得备两套!"
回到赏花宴时,忽见海棠树下立着个青衣公子。那人闻声回首,桃花眼里落满碎金,只是面色苍白得近乎透明。谢凌月欢呼一声"哥哥!",拽着我就跑,险些让我栽进花丛。
"惊春,好久不见。"他嗓音温润如春溪,正是二皇子谢知舟。十年光阴将他从病弱稚童雕琢成清雅公子,唯有眼角那颗泪痣依旧。
"听凌月说,你如今在太医院..."我话未说完,他已轻笑摇头。
"不过闲来捣鼓些草药。"他广袖间散着清苦药香,指节分明的手递来一方素帕,"你鬓边落了海棠。"
宴会散时,父亲亲自来接。回府路上,他对着铜镜捋须自照:"阿潼,爹爹可还如当年俊朗?"
"是是是,潘安见了都要掩面而走。"我憋着笑敷衍,余光瞥见父亲偷偷调整玉冠的角度。
晚膳后踱步消食,忽闻假山后传来细弱呜咽。拔开枯草,只见一只杂毛奶狗蜷缩着,湿漉漉的鼻头翕动,肚皮微弱起伏。我解下披风将它裹住,这小东西竟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手腕。
我心尖软得一塌糊涂,将这小东西裹在披风里抱回屋。它轻得可怜,蜷缩在我掌心时,能清晰感受到那微弱的心跳,像片落叶般簌簌发抖。因着月份尚小,不敢轻易给它沐浴,只得命人备了温水,用我最柔软的绢帕浸湿了,一点一点擦拭它脏污的绒毛。
"小姐仔细手。"丫鬟春桃捧着鎏金暖炉,将屋子烘得暖融融的。我跪坐在波斯绒毯上,指尖抚过它瘦骨嶙峋的背脊,能摸到根根分明的肋骨。温水换了三盆,才见它原本的毛色——竟是极漂亮的黄白相间,肚皮雪团似的白,背脊金黄如秋日的麦浪。
同相守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九重紫:再嫁英国公
- 酸涩拉扯,甜中小虐的前夫文学鹤发将军宋砚堂X当世名医明玉兰前世,宋墨与明玉兰是父母之命的寻常夫妻,宋墨伊始对满眼都是他的妻子只有相敬如宾之谊......
- 1.3万字5个月前
- 沐灵烨心
- 为了改变被魔神毁灭的世界,沐灵宗弟子安林可,在宗主爹爹和各位师兄师姐们的保护下,利用沐灵心的力量回到过去,回到过去的安林可,决心刻苦修炼,改......
- 2.8万字4个月前
- 穿成炮灰后直接摆烂
- 雄竞“万花丛中过,看中哪朵摘哪朵~”
- 2.4万字2个月前
- 幽魂引
- 在偏远的槐树村,流传着一个令人胆寒的传说:每逢月圆之夜,村口的老槐树下会出现一个穿着红衣的女子,她总是背对着路人,低声哭泣。这个传说吸引了年......
- 0.9万字2个月前
- 流光明玉
- 孤女阿梨家遭大火,持婚书投奔未婚夫。相处中误会频生,游船落水后她心灰意冷远走。三年后重逢,爱与救赎的故事重新上演。甜美清醒女主V不懂得爱人冰......
- 1.7万字2个月前
- 抽帧
- 夏夜晴朗的晚上♬吕彦良。
- 2.4万字15小时前